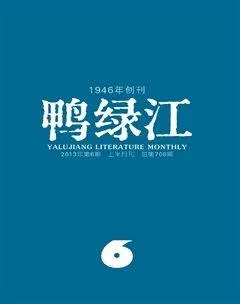橫涇河邊
林 宕,本名徐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上海文學》《小說界》《花城》等刊發表詩歌及小說,小說曾被《作品與爭鳴》《小說月報》轉載,后停止創作十多年。2007年起重新開始小說創作,作品多次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并于2010年榮獲第九屆上海文學獎。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上海某報社。
一
許紅弟說:“我現在是白天沒鳥事,晚上鳥沒事。”
一旁的胖子發出了幾聲嘎嘎嘎的笑,雄鵝樣的。
“找點鳥事還不容易?”胖子收住笑,說。他還把目光移到正靜坐在他身體左側的楊木初的臉上,好像要楊木初作出肯定的回答。
楊木初就慌慌地點頭。其實,楊木初是一直盼望著這個不知名的胖子早點從許紅弟這里離開的,因為他在,許紅弟已經把楊木初冷在一邊好長時間了。許紅弟是曉得楊木初來他辦公室里的意圖的,冷楊木初或許也無關胖子,是許紅弟必然要表示出的一種姿態。楊木初曉得自己不應該久坐這里,可真要叫他離開,輕易放棄要許紅弟辦的事,他也心有不甘——這就好比在他家的竹園里,明明往上跳一跳,是可以摘到藏在竹葉里的一窩鳥蛋的,可由于沒有往上用力一跳,最后就失去了那窩鳥蛋。楊木初今天是想跳一跳的,所以,他就僵硬著上身,一直在沙發上等待著,等待著胖子的離去。
胖子又讓目光落在許紅弟臉上:“兄弟在今天晚上就給你安排點鳥事吧?”
這下輪到許紅弟笑了,他的笑也像鵝的叫聲,看來,笑聲一般是會相互感染的,一般是要鵝一樣相互追逐的。
“要安排,老早有人給我安排了,輪得到你?”
許紅弟說著瞥一眼楊木初,似乎是楊木初的在場,讓他有些話不便說出口。就像剛才胖子的那道目光,許紅弟的這一瞥,又一次讓楊木初感覺到了自己在這里的價值,也堅定了他要繼續坐下去的決心。可這時候,許紅弟卻揮揮手,說:“不談這個,談別的吧。”
胖子說,怎么能不談?男人不談這個,還能談什么?我看就今天晚上,我和你一道到“花中花”夜總會去白相相。許紅弟搖頭,我一向不去那種地方的。胖子的臉上露著神秘兮兮的笑意,一向不去,今晚破例,大哥,我看定了,就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帶你出去白相。許紅弟還是搖頭,還是說,我從不去那種地方。胖子的眼睛里就露出狐疑的神色,你不去那種地方,賺那么多錢做啥?
胖子和許紅弟的這一番對話竟然讓楊木初上身的僵硬感消失了,一旦感到自己的筋絡活絡了,楊木初也挺想插上一兩句話。
片刻后,楊木初捉住了一個機會,終于插上了一句: “晚上就到我竹園里白相吧,來白相幾把。”
胖子不太懂楊木初的話,許紅弟卻曉得楊木初是要他們到他的竹園里去賭上幾把。許紅弟就笑了。
“老楊,你不曉得我是不賭的?”
對上話了,楊木初很高興,并覺得自己要許紅弟辦的事情今天或許真能辦成。
“不嫖不賭的,我看你的工廠還是關掉算了。”胖子說,“我看是你讓自己‘白天沒鳥事,晚上鳥沒事’的。”
胖子的話讓楊木初想起了村里人一道c4974176e395f1d7858598af74e7b648嚼白話時有人講的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講究養生的中年人問一位老中醫,我平時注意養生,基本做到煙酒不沾、女色不貪,能活到八十歲嗎?老中醫說,你煙酒不沾、女色不貪,要活那么長干什么?
楊木初想笑,卻忍住了,嘴里蹦了一句讓他自己也感到滿意的話:“許總雖然不嫖不賭,可他開廠是為了讓鄉里鄉親的人都有口飯吃啊。”
馬屁是拍對了,許紅弟臉上露出笑。
“老楊把我拔高了,拔高了。”許紅弟謙虛地向楊木初擺擺手,可臉上的笑分明含著對楊木初贊許的意思。楊木初覺得照這么談下去,要許紅弟辦成那事的把握是越來越大了。
許紅弟像是剛剛醒悟過來似的,給胖子介紹楊木初:“老楊是編結專業戶,也是我這里的竹藝品供應戶。”
許紅弟的廠是一家編織廠,用水洼地里長出的藺草和竹園里產的蔑片編織各種工藝品,都出口。廠里除了常年雇傭著幾十名編織工人外,鄉里鄉外有人編織了工藝品,只要質量合格,許紅弟的廠也通吃,不但通吃,有時遇到日本那里催貨催得緊,他還把活兒發包給鄉里鄉外的那些業余編結手。這些年,楊木初也隔三差五地接到許紅弟發包來的活兒,所以,嚴格地說,許紅弟是他楊木初的半個“衣食父母”。
輪到要介紹那胖子了,許紅弟竟賣了個關子,要楊木初猜猜看胖子是干啥的。看許紅弟臉上的表情,好像胖子從事的是一個什么神奇的職業。楊木初猜不出,望著許紅弟臉上的表情,說:“開火箭的?”
楊木初對自己的回答很滿意,果然,胖子和許紅弟都笑起來,楊木初讓自己也發出了幾聲干笑。當自己的干笑與另外兩股笑聲交織在一起時,楊木初知道自己差不多已和面前的兩個男人平起平坐了,他差不多可以向許紅弟提出自己的要求了,這要求差不多能得到滿意的答復了。
其實,胖子是干什么的,楊木初一點也不上心,他只想著自己的事能不能辦成,他只想著要與許紅弟簽下個長期的供貨協議。他家的竹園被列入了動遷范圍,這一紙長期的供貨協議就是錢。以前,許紅弟要求一些編織專業戶簽約時,楊木初不上心,現在碰到了動遷這檔事,他才悔不當初了。
許紅弟還是繼續介紹胖子的出處,原來這胖子是許紅弟新結識的外鎮人,雖然不是開火箭的,可做著的活計和開火箭一樣讓本地人覺得陌生而神秘:拍電影。可到底是他拍人家還是人家拍他,許紅弟一時沒有說。楊木初怎么看也不覺得胖子像個電影明星,可明星是他楊木初能輕易看出來的嗎?不過,楊木初很快就知道了,胖子其實只是個掮客,在本地的好幾個景點和幾個北方來的影像制片人之間忙活。
許紅弟說:“現在,新行當真是多,也行行出狀元。我們這里竟然也出了個拍電影的。沈開,真有你的。”
胖子叫沈開。楊木初把目光移到了許紅弟的臉上,感覺是時候了,是到他該把自己來這里的目的抖落出來的時候了。
“許總,辰光不早了,”楊木初心里雖然有點急,可還是把話講得很慢,“我們不要開火箭了,也不要拍電影了。”
許紅弟再一次被楊木初的語氣逗樂了,覺得老楊這個平時看上去有點唯唯諾諾的男人,一旦給了他臉,還是蠻有意思的。
“那你說說看,我們要干什么?”
楊木初說:“把我那件摸得著見得著的事辦了吧。”
許紅弟臉上的笑收起了,他想,看來真不能給老楊臉。許紅弟說,不是已經跟你講過了嗎?許紅弟的意思是,既然楊木初家的竹園已經被列入了動遷的規劃區,那么,他許紅弟再與楊木初簽訂供貨協議就是違規行為了,而如果照楊木初的意思,把簽約的具體日期往前挪,挪到動遷消息傳出前,那更是一種欺詐行為了。這樣做的話,許紅弟還想在商場上和社會上混嗎?
然后,他話鋒一轉,回答了楊木初提出的一個疑問:“說最近我與幾個藺草種植戶倒簽協議,是別人在瞎嚼舌頭!”
墻上的掛鐘“當”地響了一下,沈開從靠背椅上跳起來,說吃飯了吃飯了。
楊木初也站起來,說:“我請你們吃飯去。”
見許紅弟和沈開不接嘴,楊木初又說了一遍。他是真心實意地向他們發出邀請的。雖然許紅弟又一次拒絕了他,可他還是想再努力一把,照他的理解,要談成事也就那兩種場合,辦公室里和酒桌上,可辦公室里有了外人,事就難談了,就只能到酒桌上了,而事實上在酒桌上把事情談成的把握也確實比辦公室里更大些。
“讓你請客?想得出。”許紅弟說。
楊木初理解錯了許紅弟的話,有點急切地說:“我們怎么就不能坐在一起喝酒?你不肯幫我辦事,我們就一定是對手了?”
即使真是對手,也可以坐在一道喝酒呀。楊木初告訴許紅弟,鎮動遷辦的喬小剛和上訪戶張桂根真是對手呢,可一方面是對手,一方面卻又常常一道到他那個竹園里來,是客客氣氣的、輸了也不紅眼的賭友呢。
許紅弟看住楊木初:“老楊,你很有意思啊!”
然后,許紅弟又說,今天很不巧,他和沈開有事要馬上到市區,改天一定由他做東,請老楊吃飯。
二
玻璃頂響起雨滴聲時,楊木初開始為離開他十幾米遠的另一個玻璃頂棚子里的人下面條。
液化氣鋼瓶里噴出的火藍瑩瑩的,舔著鍋底。雨是噼里啪啦地落起來了,蓋去了不遠處的洗牌聲和喧鬧聲。已經成慣例了,每到下午三點左右,楊木初就要為那些玩牌九的人弄點心,有時是下餛飩和面條,有時是下本地人做的眉毛餃,也有的時候是弄半鍋子蛋炒飯。本來,這種燒燒炒炒的生活該是女人做的,可楊木初的老婆過世得早,女兒傻娟又夾在這些賭友中不愿出來,楊木初就自己為打牌的人弄點心了。如果夜里還有場子,楊木初仍要在晚上九點左右為客人們弄點心(比起在每個場子結束后贏家留在桌面上的臺費,點心和茶水的開銷是微不足道的)。
面條很快下好了,用一把長柄笊籬把滑溜溜的面條下到好幾只放著蔥油的瓷碗里后,楊木初的目光有點茫然地朝玻璃頂棚子的外面望去,無數白亮亮的雨線穿織在竹林里,青翠的竹葉發出簌簌的聲音,像是相互間的絮語,而一些枯死的竹葉不時地從高高的竹枝上脫離,像一些被打濕了翅膀的蝴蝶,悠悠地墜落到地上。
從楊木初待著的這個棚屋到十幾米外的另一個棚屋,是一條傾斜的青磚小道,小道的上方,竹枝竹葉相互纏繞,像是一個天然的廊篷。楊木初就沿著這條青磚小道,用一個木托盤分三次把面條端了過去。
打牌的人都兒女吃上了父母端上的東西似的,臉上露出了心滿意足而又理所當然的神色。眾人稀里嘩啦地把空碗扔到地上的一只篾簍里,又紛紛走到桌子邊。
“老楊,棚頂上的玻璃燈怎么不亮了?”張桂根在桌子邊轉過臉來。
因為下雨,竹林里的能見度就低。那玻璃燈早該開了的,可這燈幾天前就罷工了,幾天來天氣一直晴好,不要開燈的,楊木初也就懶得去管它了。
楊木初要眾人先不忙玩牌,然后站到了桌子上。原來是小問題,燈泡里的鎢絲斷了,他摘下了燈泡,跳下桌子,向眾人揮揮手,示意他們可以重新開始了。只有這個手勢,讓人覺得楊木初不像是這批人的服務員,倒像個將軍了,向他的士兵發出了進攻的號令。
楊木初看一眼站在喬小剛身后的女兒傻娟,想叫她到竹林南面的家里去拿個新燈泡,可一直站在喬小剛身后看牌的女兒一口回絕了他,說不能離開,離開了,喬小剛的手氣就要壞。眾人笑起來,說要不離開就永遠不要離開,跟小剛跟到底。
傻娟已快二十歲了,可村里人一直認為,傻娟和常人比,腦袋瓜是不靈光的。對村里人的一些不恰當言論,楊木初是憤怒的,可沒有一個人當著他的面說,他的憤怒就不好發作。他一直認為傻娟是不笨的,只是讀不出書而已。他的兩個女兒都讀不出書,早早從學堂里回了家。既然不能指望她們書包翻身,楊木初只好讓自己多動腦筋、多傷筋骨,為她們的今后多讓自家累些、苦些。
他順著一條鋪著碎石的彎道向老屋走去。當他跨進家門時,十三歲的小女兒珍珍在門角落里躥出,身體貼上了他。村里人都說珍珍比她姐姐傻娟還傻。楊木初卻認為珍珍比她姐姐還要聰明,只要他外出,她就一個人候在門角落里,等,等他回來。其實,傻娟原來也不叫傻娟的,叫秀娟,是村上人覺得她腦子不太靈清,才為她改了名的,也不知是哪一個先開始叫出“傻娟”這個稱謂的,反正村里人后來都這么叫了,叫得楊木初也默認了秀娟就是傻娟這個事實。
楊木初用粗糲的手掌摸摸珍珍的頭頂,就往自己的房間里走,珍珍像一條小狗一樣緊緊跟過來。楊木初家是一幢七路頭瓦屋,中間一個客堂,東西是兩個次間,一間是兩個女兒的房間,一間是他的房間。此外,瓦屋的兩端還各有一個廂房,一間堆放雜物,一間是楊木初編織竹藝品的作坊。
在房間里拿了一只新燈泡,返身跨出家門時,楊木初擺擺手,珍珍就很聽話地縮回到了門角落里。
屋外,雨已經停了。楊木初重新走進了竹園里,竹園里布滿著竹葉的清香和泥腥氣,這清香和泥腥氣是楊木初聞慣了的,也是他喜歡的。有一陣子,他身上也散發著這種氣味,帶著這種氣味,他去找“新蓮盛”編織品有限公司的總經理許紅弟,許紅弟好幾次遠遠聞到了這種氣味,就從自己的辦公室里躲開了。
還沒有走近竹園里那個眾人聚賭的場子,楊木初就察覺到了異樣,那場子里的人在喧嘩、在起哄。他們碰到了什么高興事?楊木初緊走了上去。
這群人原來在尋傻娟的開心。“傻娟你還需要跟莊嗎?不要的,你只要在喬小剛的臉上親一口,老子就給你一百元”——河南人張桂根的這句話是由別人轉到楊木初耳朵里的,當手里拿著一只新燈泡的楊木初剛看到傻娟佝僂著腰在親喬小剛的左臉頰時,還有點犯糊涂。他看到喬小剛微微側轉著臉面,臉面上是一副迎合、迷醉的神色。
楊木初急忙撥開身邊的幾個人,去拉傻娟。
旁邊有人開口,說出了河南人張桂根的那句話。這是不能怪張桂根的,在橫涇村,開男女玩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甚至有人會當著你的面開你老婆的玩笑,能這樣開玩笑,只能說明那人與你是心無芥蒂的,關系融洽的。確實如此,當著你的面,那人能與你老婆做什么呢,開開玩笑而已,明人做的不是暗事。而反過來,做暗事的人恰恰是不敢講明話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橫涇村人是喜歡那些能當著你的面開你老婆玩笑的人的,說明這人是一切做在明處的,你對這人盡管放心好了,絕不會背著你做暗事。
既然這樣,楊木初能對河南人張桂根和喬小剛發火嗎?不能,也不會。可楊木初還是對傻娟的賺錢方式表示了反對。他看到傻娟的左手中已經捏上了幾張百元的鈔票,就一下子奪了過來,遞還給張桂根。
眾人起哄,說,老楊,是你自己要還的啊,不是他張桂根要回來的啊。好像楊木初立刻要反悔似的。
“是我還的,”楊木初說,“老楊家不賺這錢。”
張桂根說:“嘖嘖,賺錢還要講究什么,像我,只要來錢,管它什么路數。”他又問坐在對面的喬小剛,“對吧?”
喬小剛點點頭,臉上帶著笑:“你差不多已經涉黑了。”
張桂根也不動氣,只是嘀咕一聲,黑不黑也不是你說了算。張桂根從河南來這里快五年了,先是在本地一家企業里打工,后來開始在河南人之間做“娘舅”,就是只要河南人之間有什么過節,都由他張桂根出面解決。再后來,橫涇村所有外來人員間的糾紛,幾乎都需要張桂根出面來定奪,當然,他也不是光桿司令,他手下也有一批人。直到如今,張桂根已經在幫本地人打理事情了,例如,本地有人在廠里遇工傷了,由他手下的人冒充本地人的家人,躺廠門口,坐廠長室。甚至本地人需要上訪,也會找到他,于是他會帶著一幫外來人員,坐到鎮政府門口。
嘩嘩嘩——有人重新開始洗起牌。
“拿牌吧,待著做啥?阿是也想叫傻娟親一口?”經營著一個廢品收購點的金貴沖他對過的人說。
眾人笑起來,傻娟也笑。傻娟笑的時候,是很好看的。
三
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夜的嵐氣彌漫在了橫涇河的兩岸。空中仿佛有無數只涼爽的手指,在撫摸著在橫涇河兩岸乘涼的人的肌膚。
橫涇河是橫涇村人的母親河,一到夜里,橫涇村人就到河邊的柳叢中、石凳旁嚼白話、趁風涼。整條河彎彎曲曲的,以前村里曾來過一位不明來處的勘探人員,說如果把這條河畫出來,河上的喜雨橋和塘灣橋不是并行的,是相對的,就是喜雨橋的一個橋堍與塘灣橋的另一個橋堍是對應的,可以用一根直線連起來。可想而知,橫涇河彎曲得是那么厲害。可是,為什么這河在橫涇人的印象中始終是東西向的呢?橫涇人弄不清這是為什么,就像弄不清河南人張桂根和鎮動遷辦的喬小剛第一天還在為動遷的事鬧,第二天卻相約著去打牌;就像弄不清楚“新蓮盛”編織品有限公司的總經理許紅弟為什么平時那么扣克工人的工鈿,卻又時時會提著鈔票到區民政局去捐款,到廟里燒香。
橫涇河上其實不止喜雨橋和塘灣橋這兩座橋,還有大概四五座橋,其中最大的橫涇橋是一座三孔石拱橋。橋的兩個橋堍那里還各建有一個毛竹搭的涼亭。每到夏天,毛竹涼亭里、橫涇橋的三個橋孔里躺著或坐著乘涼的人最多,有的人甚至整夜躺在那里。其實,橫涇村已經有不少人家裝了空調,即使不裝,也幾乎家家有電扇了,可橫涇村人還是喜歡在夜里拿一條草席出來,睡到河邊柳樹下或橋孔里。這從很早以前沿襲下來的習慣,橫涇村人為什么一直沒有丟掉呢?這同樣是一個叫人弄不明白的問題。
現在,沈開跟著楊木初穿行在橫涇河的河邊,臉上一層新奇、興奮的表情被薄薄的月光照亮著,橫涇河散發出的一股水汽撲鼻而來,水汽里帶著一股清淡的東洋草的香氣。沈開翕動著鼻翼說:“橫涇河很好聞。”
在他們幾步路開外,一個有著孕婦一樣大肚子的壯漢在一條麻石板上翻了個身,一把由棕葉做成的蒲扇從他裸露著的大肚子上落下來。楊木初記得那麻石板曾是一塊野田里的無名墓碑,一般人不太愿意睡。壯漢不但睡了,而且身下還沒有鋪草席。以前,橫經村人睡石板、石條不鋪草席,睡久了,好多人就得了僵直性風濕病,走路直不起腰了。起先,得僵直性風濕病的人還以為是長期的農活造成的,橫涇村的好幾任赤腳醫生也不曾識出病因,終于有一位赤腳醫生識出了,這樣,村民們睡石板條時開始鋪草席、竹席了。當然,也有人不信那醫生話的,就依舊直接往石頭上躺了,就像眼前的這壯漢。
壯漢躺在了一棵青楓樹下,樹根處的一蓬草叢里傳出了紡織娘的叫聲,這纖細的叫聲和漢子粗重的呼嚕聲交織在一起。楊木初想上前一步認認這胖子是誰,發覺沈開已經鉆進了前面的柳樹叢里,連忙跟了上去。
快到橫涇橋時,楊木初在一棵老柳樹下看到了一個影影綽綽的景象,一個人躺在一條石凳上,就在這人的左下側還有一條低一些的石凳,同樣躺著一個人,下面的人把一條裸露著的胳膊擱在了上面那人的胸脯上,上面那人的左腿則垂下來,搭在了下面那人的大腿上。一男一女。面對這種景象,楊木初已經見怪不怪了。在橫涇河邊趁風涼的人中,這樣的情況還少嗎?兩個原本離得很開的男女,會越來越近,到后半夜甚至會睡到一張草席上,當然,他們往往不是夫妻。
“快點。”沈開在前面催楊木初,他快到橫涇橋南橋堍邊的那個毛竹涼亭邊了。
沈開是在給楊木初打電話時,才萌發了要到橫涇河邊來看看的想法。他是在許紅弟辦公室打來的,打到了楊木初隔壁的耿老四家。許老板要請你吃夜飯啊,上次講過的。沈開在電話里大聲嚷嚷。沈開還說,許老板還有別的事找他。楊木初就說,我夜飯吃了啊,我下晝四點鐘就吃了,只有你們有錢人,夜飯吃得晚,越有錢越晚。可楊木初很快醒悟過來,心撲撲撲地跳起來,許老板還有事找他?莫非他愿意跟我簽約了?我來我來,楊木初忙說,我正想到橫涇河邊去呢,現在不去了。沈開問,聽人講橫涇村的男人們都喜歡夜里睡到橫涇河邊去,是不是因為半夜里有美人魚要爬上岸來?說著,沈開哈哈大笑起來。可是,夜飯還是沒有吃成,許紅弟突然有事了,說夜飯就改天。沈開就重新打來電話,他讓老楊今天夜里仍舊到橫涇河邊去,還說,他也想來,來看看,說不定這河邊的景致能成為很好的外景,用不著花錢布置的外景。
繞過一根爬滿了蔦蘿的石柱,楊木初跟上沈開。
“下禮拜就叫人來拍。”沈開有點興奮,“說不準在河邊真能拍到原生態的男女野合圖呢。”
一幅河邊鄉景圖繼續在沈開和楊木初的面前展開,在他們身體左前側的涼棚里,有人影影影綽綽的,鬧猛的聲音卻清晰地傳出來。平常里,楊木初也常會進去軋軋鬧猛的,也曉得,到了半夜,這團在一道的作人鳥獸散時,總會有一兩個人悄悄地尾隨著離去,沿著橫涇河走,看著哪個橋孔里沒有人,就先后鉆進去。當然,他們是一男一女。就在這時候,楊木初突然心里撲撲跳起來。他驚醒過來,剛才那老柳樹下躺著的女子怪不得看上去眼熟,原來是傻娟。那么,躺在她高一級石條上的是喬小剛了。對,是喬小剛。
楊木初停止了前進的腳步,沈開卻在說:“我們上橋去。”
涼棚上方的橫涇橋上也站著一些人,他們依在橋欄上,手中煙頭一閃一閃的。楊木初記得如果從兩里遠的龐涇橋上望過來,這些煙頭就仿佛是星星落到了橫涇橋上。
“你先上吧,我往回走走。”楊木初說。
沈開攥住了楊木初的手,臉上露著笑:“看到什么了?”
“那就上橋吧。”楊木初只得說。
在橋階上,楊木初絆了一下,摜倒了。可他很快站起來。
“操那娘。”楊木初講了一句臟話,他是仰著臉對著繁星閃爍的夜空說的,可他看到的是喬小剛那張有點尖削的面孔。
沈開在橋頂上站住,看著從他的身下一直朝東延伸開去的黑黝黝的橫涇河面,說:“明天晚上吧,許老板要與你談談那事呢。”
楊木初屏息等著沈開往下說,可沈開閉上了嘴。楊木初終于問,許老板要與我談啥事?沈開回答他,明天一起吃晚飯時他自然會曉得的。
沈開重新邁開了步子,向河的北岸逐級下橋。見楊木初緊緊跟著他,就轉臉說:“你回吧,我也要回了。”
沈開沿著河的北岸朝西走。只要朝西走上兩百米開外的樣子,就是大馬路,沈開的那輛破舊的桑塔納車子就停在大馬路上。
楊木初立刻轉身,幾乎是跳下了橋。他很快來到了老柳樹下,可看到的是空空的一高一低兩條石凳。
操那娘,看到我后溜了。楊木初表情怔怔的,摸一把臉上的汗。他有點頹喪地往家里走。可真要再一次碰上傻娟和喬小剛,他又能怎么樣呢?他早就察覺到傻娟的心思了,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看著她像一只小斑鳩,朝竹園里張在竹梢上的網兜里鉆。看來,村里人講得其實沒有錯,她傻,她是傻斑鳩,要朝竹園里張在竹梢上的網兜里鉆。
踏進家門,楊木初見東面的次間里有暈黃的光線投射到客堂里,他迅速地走了進去。傻娟依靠在木床的床頭,在看一本已經被她翻爛了的瓊瑤書。身旁,放在梨木梳妝臺面上的電扇吹出的風,不時掀起傻娟額頭的一縷頭發。
“你怎么從河邊回來了?”楊木初問得有點氣急。
“我怎么在河邊了?”傻娟臉上露出的迷惑神色和一個聰明人是一模一樣的,其實,傻娟在某些方面就是個聰明人,比如,她用蔑片編竹籃、竹簍以及竹塔、竹豬、竹馬等竹器工藝品時,好多同年齡的女孩是不能跟她比的,可她還是被村里人說是腦子里缺一根筋。幾年前,她告訴別人,說隔壁耿老四的女人鉆到她父親的被窩里了。被楊木初打了一巴掌后,她立刻曉得這是不能說的,所以,楊木初覺得傻娟是聰明的。
“你不是躺在河邊的石條上?喬小剛也在一邊?”
傻娟扔掉了手中的書,身子騰地從床上直起來。
“他在河邊?”
楊木初連忙按住了傻娟的肩頭,“他已經回家了。”看來,是他認錯人了。楊木初搖搖頭,覺得自己的眼神是越來越不行了,可眼神不行,他的腦袋瓜還行。
“你不能再與喬小剛交往了,”楊木初說,“喬小剛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傻娟臉上露出使勁想的神態,“我們都是橫涇人。”
“對,可是橫涇人跟橫涇人是不同的。”楊木初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要講不同,就是他是男的,我是女的。”
這真是一句聰明話,楊木初凝神看著傻娟,臉上露出贊許的神色,不過一瞬后,他還是嘆口氣,又開口:“男人之間區別更大了,喬小剛家有銅鈿,他人又是那么花。家里有銅鈿,人又老實的,有這樣好的運道能讓你碰上嗎?”
傻娟認真聽著,她又想從床上起來,楊木初再一次按住了他。
“是該給你說個相配的人了,托托人看。”
“不,我要讓喬小剛討我做娘子。”傻娟尖叫起來。
四
二樓的喬小剛把腦袋探出玻璃窗,朝樓下喊:“張桂根,今朝你打算坐幾個鐘頭?”
看來,這一陣喬小剛也是閑著。香花橋鎮動遷辦是與市政所合在一幢樓里辦公的。底樓正中央進門處的不銹鋼大門緊緊關著,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人進出了。這道大門近階段整天關著,樓里辦公的人都有一張磁卡,往門把處的一個金屬片上一貼,這門就開了。這么做,顯然是為了防止那些鬧事的人進樓妨礙公務。可張桂根對人說,真要進去,這兩層小樓,架一把梯子就攻進來了,這鋼門頂個鳥用?張桂根還說,他們的鬧事其實也是文明的鬧事,是擺理講譜的鬧事,不是瞎胡鬧。
樓房前的場地上,張桂根帶領的一幫外地人坐在一棵白果樹下。和以前去坐鎮政府門口一樣,張桂根不會與那幫外地人一樣,自始自終地坐在場地上的,他往往會在半中走開。也與去坐鎮政府門口一樣,那幫外地人中混雜著幾個本地人,碰到要進樓談判了,那幾個主事的本地人就進去談。而碰到突發事件,如樓里的人叫了鎮聯防隊或鎮派出所的人來了,那幾個本地人會悄悄地退到白果樹的后面,甚至會順著白果樹后面的一條煤屑路匆匆地打道回府,留下那些外地人繼續在樓房前做著對抗政府和公家人的樣子。
喬小剛也是橫涇村人,可他憑著他父親是鎮動遷辦主任的身份,竟然也到動遷辦替公家辦事了。這一次,幾乎小半條村子的地皮要被兩家港資企業征用,照說,動遷辦里有兩個人是橫涇村的,何況連動遷辦主任都是橫涇人,好多橫涇人就認為在動遷上肯定會得到格外的照顧,其實不然,幾戶連老屋也要被動遷掉的人家,置換給他們的房子還沒有落實,只發了點要他們到外面租房用的過渡費,就要拆他們的房子了。他們當然不情愿,去動遷辦、鎮里吵了、鬧了,都沒有用。后來,村民們感到這事恐怕要打個持久戰,就干脆找了張桂根,談定了價鈿,由他組織了一支也算龐大的外地人隊伍,時不時地到動遷辦和鎮政府門口去靜坐和站上一陣。今天,就是聽說區里有一位領導要來鎮動遷辦來檢查工作,那支外地人隊伍又被再次指派著過來的。
張桂根從地上站起來,蹬踏了一下已經麻木了的腿腳,又從人叢中走了出來,走到了耀眼的陽光下,揚臉朝樓上喊:“區領導到底什么時候來呢?”
“不知道,講好下晝兩點來的,可現在已經是三點了,還沒有來。”喬小剛的腦袋擱在窗框的外面。
“領導應該是很守時的呀,怎么拉了一個小時。”
“領導常常會被別的事拖住。”這一點,吃公家飯的人往往有發言權。
現在,有兩位村民夾在外地人中,村上人是輪著參與到這種事當中的。專門負責人員調配的小學退休教師朱炳根今天上午也是叫了楊木初的,楊木初說先要去區中心城辦事,辦好事后再來。可是,他顯然把自家搞得與區領導一樣了,到現在還沒有到。兩位小名分別叫木根與瓜頭的村民就對楊木初有了意見,在外地人中間罵楊木初赤佬,說今天散了后就去找他,讓他“出點血”。“出點血”的意思并不是真要傷他身體,是要他請客吃喝。
想不到楊木初后來到了,“吭哧吭哧”地喘著粗氣,樣子很急。他跨進了坐在白果樹周圍的人堆里,想到木根和瓜頭身邊來。由于步子邁得快,不小心踩到了一個人的腳背上。那天真不巧,因為要到區中心城去,楊木初把腳上的那雙布鞋換了,換上了風涼皮鞋。楊木初還有往自己的皮鞋鞋跟上釘鐵片的習慣,就是他右腳皮鞋跟上的鐵片把那個人的腳背踩破了。
那個人從地上站了起來,一把揪住了楊木初的衣領。其實,到這時候,楊木初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踩到別人了,他認為那人剛才口中喚出的一記痛楚的叫喚聲是跟自己無關的,所以,他臉上露出茫然的神色。
“你眼睛長天上了?”那人叫一聲,楊木初襯衣上的幾粒紐扣掉落下來,也終于明白是自己踩著別人了。
楊木初想道歉,可突然感到嘴里的舌頭又麻又大,轉不過彎來。年輕人已經拽著楊木初的胳膊了,要把楊木初往人堆外拖。這時候,有幾個人從地上站起來,沉悶已久的臉上露出了活泛的表情。
“干一架。”有人嚷起來。
楊木初覺得年輕人的面孔還是有點熟悉的,卻想不起來他到底是誰,在哪里做的。他舔舔自己的嘴唇,想問,旁邊又有人開口了:“李子,把這老頭摜地上。”
哦,原來他是村東頭那家廢品收購站的李子,楊木初見過的。楊木初記得有一次去賣過銅皮,李子還差點兒按鐵皮的價格付給楊木初鈔票。
李子右手的虎口叉住了楊木初的喉嚨。楊木初的喉嚨口呻喚一聲,兩人就扭成了一團。這時候,坐地上的人大部分已經站起來。木根和瓜頭撥開人叢,沖過來。
“操那娘,還沒有和樓里的人干起來,自家人倒干起來了!”木根說。
其實,以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支上訪的隊伍還沒有走近鎮政府門口,由于口角,兩位外地人從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指責發展到了拳腳相向。
“李子,你狗娘養的看我不把你趕出橫涇村。”瓜頭也嚷了一聲。
外地人看到本地人在幫本地人,也開始起哄起來,他們仗著人多勢眾,圍住了木根和瓜頭。其實,木根和瓜頭也只是想動動嘴唇皮,唬退了那李子。現在,看到外地人都逼近了,就立刻噤了聲。他們突然想起自己原來對楊木初的遲到也是有意見的,現在干嗎要為了他而給自己惹什么麻煩呢?
這時候,李子也停止了所有動作,因為楊木初已經真的被他摜在了地上。李子雖然停止了動作,有一個人卻要他再一次做出動作,是張桂根,張桂根對李子說:“把他攙起來。聽到沒有?”
張桂根的話雖然很輕,可場地上的人都聽見了,就連他們面前那幢兩層樓里的好多人也聽見了。那些人為了看好笑,都把腦袋探出了窗口。
“聽到沒有?”張桂根又對李子這么說了一聲。
“不要攙的。”楊木初快速地就從地上站起來,拍拍自己屁股上的灰塵,“我的筋骨好著呢,能一下子摜得壞?”
樓上,有一個人發話了:“不識抬舉的東西,木初叔是讓著你呢。”
他站在高處,目光遠遠地投射在李子身上。別人在說李子了,張桂根就反過來幫李子了,他把臉轉向樓上:
“關你什么事呢?你少說幾句吧。”
張桂根的語氣雖是不溫不火的,樓上那人卻不吱聲了,他的臉也隱去了,這時候,喬小剛的腦袋卻在樓上露了出來了。張桂根立刻向他揚了揚手。
“嘴干了,扔幾瓶礦泉水下來吧。”張桂根往上說。
喬小剛往樓下扔下了幾瓶礦泉水,張桂根傴僂下腰撿,剛重新直起腰,喬小剛又在樓上發話了:“剛接電話,區領導不來了呢。”
木根和瓜頭的目光里露出狐疑的神色,張桂根側著臉望著他們:
“要不今天就先撤了吧?”
“撤吧!”見木根和瓜頭點頭,張桂根轉身朝人群揮了揮手。
五
在依著老環城河的一家飯店里,許紅弟先坐了,沈開和楊木初就跟著在臨窗的一只方桌邊坐下。楊木初轉臉,看看窗外在微微漾動的碧綠河水,說:“你們請我吃飯,我老楊檔次上去了啊。”
飯店前面是一條窄窄的青石鋪設的小街。昨天,楊木初在滾燙的青石小街上走過時,曾向這家飯店的門楣上掛著的木匾額看了一眼,終于沒有走進匾額上寫著“漕溪人家”店名的這家飯店,只是到一個點心攤上買了三個剛出籠的饅頭吃。小街兩邊除了一些飯店和小吃店外,磚木結構的民房里還遺留著一些隱性職業者。楊木初昨天就是去小街東首找一名瞎子算命先生,讓他給傻娟掐算婚姻。掐算的結果,傻娟最好是在年內讓人做媒,嫁出去。
飯店里客人不多,服務小姐把菜譜遞上,許紅弟朝沈開努努嘴,沈開就接了菜譜點起菜來。
窗外,有櫓聲傳來,船上一位小女孩的手臂也伸進窗里,她手舉著一束粉白色的花。
“阿要買花?”
許紅弟朝她擺擺手。
櫓聲遠去,一串水百哥的叫聲又逼進窗里。
許紅弟請楊木初到飯店來,真有事了,不過不是楊木初盼著的那件好事,簽那份長期的供貨協議。當他用商量的口吻向楊木初說出這次請他吃飯的目的后,楊木初感到很吃驚。
原來,許紅弟有個快三十歲了還沒有成家的親阿弟,是個癱子,常年躺床上的,聽說腦子也不大靈光。許紅弟想給他說個娘子,問楊木初能不能爭取把傻娟說給他?
一口酒像火一樣停在楊木初的喉嚨口,一瞬后,這酒又像火一樣滾進了他的肚子里。
“你怎么啦,老楊?”沈開說,“鯁魚骨頭了?”
“老楊哪是鯁魚骨頭了,他是不同意這親事呢。”許紅弟說。
“噯!你不要搞錯。”沈開覺得有必要提醒楊木初,“徐家是什么人家,嫁過去,就好比老鼠跌在白米囤里。”
哪有這么巧的,他昨天剛剛問過瞎子算命先生,今天真有人來給傻娟提親說媒了,可要把傻娟說給怎樣一個男人啊。楊木初覺得自己的肚內依舊在燙。他囁嚅道:“這不是讓我家傻娟去做保姆嗎?”
許紅弟把筷子往桌上一擱,哈哈笑起來。
“我家里常年有保姆的,一個還是專門伺候我阿弟的呢。”他把臉湊近楊木初,并放低了聲音,“我告訴你,他雖然癱了,可還能做那種事呢。”
可你卻不能做,你到現在還沒有小人,你們許家怕斷后,所以你想到了要給你弟弟娶老婆——對許紅弟的事,楊木初多少還是曉得一點的。那天,沈開在許紅弟辦公室里提議要給許紅弟安排“鳥事”時,楊木初真想給沈開抖落一下許紅弟的事,可他終于還是不敢。
楊木初覺得喉嚨口癢癢的,有一種想吐的感覺,他強壓下了這感覺。他想站起來。反正已經吃不進什么了,還坐在這里干什么呢?可他想是這么想,卻一時還是沒有站起來,畢竟,許紅弟也算是他的衣食父母,許紅弟再怎么樣,他表面上還是要忍一忍的。
“我阿弟真還能做那種事的。”許紅弟又湊近了說。
“傻娟已經在處對象了呢。”楊木初囁嚅道,“在和喬小剛處。”
許紅弟像是一下子沒有聽懂楊木初的話,凝神片刻,才用突然醒悟過來的口吻說:“為你的竹園,你是想盡了一切辦法。”他沉吟了一下,又用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說,“不過,我也是一個為達到目的想盡一切辦法的人。”
許紅弟哈哈笑起來。楊木初的目光從許紅弟臉上躲閃開去,他凝神片刻,終于站起來,說:“我要回了。”
“走好吧,老楊。祝你的竹園賣個好價鈿。”許紅弟說。
楊木初走到家門口時,珍珍從門角落里跳出來。楊木初撫摸一下她的腦袋,然后指指屋內,示意她回去。珍珍很懂事地退回到了門檻內。
楊木初沒有進家門,拐了個彎,順著家門口西側那條滑膩膩的磚道,來到了他家那片大竹林里。一股夾帶著竹葉青澀氣息的涼氣彌漫在了整個竹園里,有餛飩鳥的叫聲在楊木初的頭頂上不時響起,楊木初抬臉,在竹枝間看到了一對在追逐、跳躍的餛飩鳥,它們的翅膀拍打在了青翠的竹葉上,激起了一片愛情的聲音。
楊木初跨進了正在發出一片嘈雜聲的玻璃棚子里,在玩著牌九的人群中拽出傻娟。
“跟我走。”他說。
傻娟卻犟著,身體往喬小剛那里蹭。楊木初擰了傻娟一下,傻娟叫喚了一聲。
“怎么啦怎么啦?”有人沖楊木初嚷。楊木初認出是村東頭廢品收購站的老板金福。只有金福這么問楊木初,其余的人仍專注于牌九,甚至是喬小剛。看到喬小剛,楊木初就知道今天是雙休日。上班辰光,喬小剛這種吃公家飯的人是不來這里的,只有休息了,他才來。他休息了,這里的人也就不把他當公家人看待。
楊木初拽著傻娟的胳膊往竹林外走。到了村道上后,傻娟已經乖乖地跟在他后面了。
“去哪兒呢?”傻娟朝楊木初的后背嘀咕了這么一句,楊木初沒有吱聲。邁進了媒婆黃琴家的門檻,傻娟還不曉得她阿爸帶她來做啥。
“也用不著把閨女也帶來啊。”黃琴說。
“我也只是把她從竹園里拉開。”楊木初看一眼立在他左側的傻娟,“啥人曉得她一直跟在我后面。”
楊木初在一只高背椅子上坐下,說:“成了,十八只蹄子總歸給的,放心。”
黃琴轉著眼珠,像是在大腦里為傻娟搜羅著適合的人選。
“給我說小剛。”傻娟已經明白他們來這里的目的。黃琴的眼珠停止了轉動,看住傻娟,“撲哧”一聲笑了:“傻娟不傻嘛。要你家的竹園值價鈿,是要攀這樣的親。”
黃琴收住了笑,“可這事就像動遷辦的人來動這里的房子和竹園一樣難,難是難,不過動遷辦要辦的事最后有辦不成的嗎?”黃琴又笑起來,“我要辦的事最終也能成的!這蹄子我是吃定了!”
“你聽她的話!”楊木初急了,“你做媒總也要看個門當戶對吧?”
黃琴又“撲哧”一聲笑了:“你爺倆到底要我聽誰的?”
“我已經是小剛的人了。”傻娟說。
楊木初粗糲的大手可笑地要去封傻娟的嘴,在接近傻娟的嘴巴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這個徒勞而可笑的舉動,手就順勢而下抓住了傻娟的胳膊。
“走。”楊木初說。
父女倆跨出了媒婆黃琴家的門口。
六
珍珍雙手把著木門的邊沿,不斷轉動門軸,“吱吱扭扭”的聲音持續不斷地響著,像是在為楊木初翻飛著的雙手作著伴奏。楊木初抬頭看一眼珍珍,記起有一年珍珍到她姑姑家住了半年,門臼里竟然長出了青苔。
幾根糾纏在一起的篾條在楊木初的雙手間舞蹈,這篾條散發著一股帶著苦艾氣息的清香。若干年后,當楊木初家和橫涇村里大部分村民一道被動遷到一個農民新村后,他只要遠遠看到由篾條編織而成的殯品,鼻腔里就會襲上一股清香氣息,這氣息讓他有一種被抽斷了根脈、懸浮在半空的感覺。
現在,在楊木初的雙手之間,這股氣息浮動著、彌漫著,他的雙手也像鼻子一樣呼吸著這氣息,這氣息讓他的雙手有著使不完的力道。那些舞蹈著的篾條在相互糾纏中終于永遠聯結在了一起,要么變成一只只變形的竹金剛,要么變成一只只胖豬狀的儲蓄罐,他把這些篾條編成的什物放在了身邊的一只橢圓形的竹匾里。
他的身后,粉皮斑駁的后墻上掛著三幅裝著細木框的黑白照片,是楊木初的父親、母親和老婆的遺像。三張遺像竟然都是全身照,大概他們臨死前都沒有來得及去拍攝半身照吧。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冬天的裝束,父親頭上戴著一頂黑線帽,和此刻的楊木初一樣,腰里束著一條褶子作裙,這種褶子作裙某種程度上就是篾匠的標志;母親頭上戴著月藍布作底的青蓮包頭,身上束著繡著春桃圖案的腰兜;老婆頭上沒戴什么,聳著一個饅頭發髻,身上短衫薄褲。
楊木初的父親也是篾匠,不過他一生編織的是飯篾籮、籃子、竹匾等日常用品,所以,遺像上的他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楊木初,看著楊木初編織著一些他不理解的竹藝品。
“珍珍。”楊木初的手停止了動作。
珍珍不再搖門,走到了楊木初的身邊,像一只乖巧的小貓一樣依在了楊木初的腿邊,臉上的神氣也是小貓式的,有一種柔順,也有一份期待。
“要快點把你姐姐嫁出去。”
和小貓一樣,珍珍沒有聽懂這句話的含義,這句話顯然要比剛才喚她的那聲“珍珍”復雜多了。可即便聽不懂,珍珍臉上的那份柔順和期待依舊沒有消去。
“哪能再讓她待在家里。”楊木初還想說什么,卻發覺幾個人站在了他家的門檻前。是鎮動遷辦的人,以前也來過,楊木初記得為首的中年人叫黃玉龍,說是動遷辦的一個副主任,年齡介于喬小剛與他阿爸之間。
楊木初從凳上站起來,拍拍褶子作裙上的屑物,要來人坐。黃玉龍在墻邊的一條柏木長凳上坐下,說:“老楊,我們要你確認一下你家竹園里的竹子棵數。”
一位短發女子把一張有著格子紋的紙頭遞到楊木初的面前。
“你的竹園里總共有385棵竹子,簽一下字吧。”短發女子看上去有三十多歲,白皮膚圓面孔,講話時00f2cbe0ca0ae0d488405c691a0793b62594ae040e6ff9ca5bf7f6bf8998c76b聲音細細的,這種類型的女子常常會出現在一種對抗性場面中的,某種程度上發揮著軟化矛盾的作用。
楊木初起先真想把紙頭撕了的,就是這女子,讓楊木初最后還是打消了念頭。與此同時,他在心里嘀咕:上次你們就來竹園數了,就要我在紙頭上確認了,上次你們告訴我的竹子數目是355棵,過了幾天怎么多了30棵?就算多給我竹子,我也不會在這張紙頭上落字。
一直靜靜站在一邊的珍珍突然用手指著短發女子衣裳上的花,說:“好看。”
短發女人的眼里涌上了一種異樣的神色,她把目光從珍珍身上移到楊木初的臉上:“簽了吧,你何苦呢。”似還有隱言要講,停了片刻,果然又講:“傻娟再怎樣,每根竹子的價鈿也是不能變了的,上面早定了的。”
楊木初突然低吼一聲:“傻娟嫁給誰,你們管不著。這竹園里的竹子,你們一根也不能動。”
連楊木初自己也感到奇怪,他的這聲低吼卻不是對著短發女子,而是對著黃玉龍發出的。
“我是不會在這紙頭上落字的,你們走吧。”楊木初從地上撿起篾條,重新編織起來。
珍珍扯住短發女子的衣角,說:“不要走不要走,我不讓你們走。”
可是,黃玉龍的屁股還是從柏木長凳上浮了起來,臉上也終于露出笑意:“老楊,到最后,簽與不簽其實是一樣的。”
跨出門檻時,黃玉龍還向楊木初友好地揮了揮手,短發女子則撫了撫珍珍的頭頂,又摸了摸珍珍的臉頰。
珍珍依著門框,看著一行人在場角上的一棵白果樹邊轉了個彎,然后走進了由兩垛灰墻組成的一條夾弄里。一只灰貓從夾弄里竄出,在弄口猛地駐足,一瞬后,又迅速竄上南面的那垛灰色墻頭。
傻娟回家時已是傍晚時分。
“你下晝在哪里?”楊木初問她,語氣是輕柔的。
“我在找小剛。”
楊木初朝屋門外瞥一眼,見珍珍一人在夾弄口玩耍,就跟著傻娟進了她的房間。他反手把房間的木門關上了。
“你真是小剛的人了?”楊木初問。
“真是他的人了。”傻娟說。
楊木初就要傻娟在床上躺下,傻娟瞪著一雙迷茫的眼睛,不明白她父親要她躺床上干什么,不過片刻后,她還是聽話地躺到了床上,像一個等待醫生檢查的病人一樣。
楊木初在床沿邊佝僂下來,手探到傻娟腰際,撩起傻娟的粉紅色薄衫。當楊木初瘦骨嶙峋的右手挨上傻娟涼滑的肚皮時,傻娟格格格地笑起來。
“做啥?”被弄癢了的傻娟舉起雙手,開始推擋楊木初的右手。
“不要動。”楊木初低喝一聲。
楊木初的手在傻娟肚皮上摸了一圈,感覺到她的肚皮癟癟的,像是盛著半袋水的一只熱水袋,里面的水已經涼了,所以,楊木初的手感覺到的是一片涼意。當這只熱水袋里發出一串“咕嚕咕嚕”的氣泡似的聲響時,楊木初的手像是受了驚嚇,往回一縮,撤離了傻娟的肚皮。
楊木初沒法判斷里面到底有沒有孩子。同時醒悟到,如果這孩子現在還只有彈子這么大時,他是沒法摸出的。他有點沮喪,感覺像是盼著傻娟肚子里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并且這孩子已經大得足以隔肚摸出。
雖然楊木初的手已經撤離了傻娟的肚皮,可傻娟仍舊攤手攤腳地躺著,仿佛等著楊木初再次觸摸他。他看著傻娟有點無恥的樣子,心里的沮喪轉為了惱火。
“起來起來。”他喝道。
傻娟要直起腰來時,楊木初突然又按住了她的肩頭,輕聲問:“小剛是什么時候與你做那事的?”
傻娟臉上露出茫然的神情,黑黑的眼珠子轉動一下。
“他家的貓死了。”她說。
楊木初偏起右腿,讓半個身子擱到傻娟的身上,他的另外半個身體在往傻娟身上移的同時,開口:“像這樣,喬小剛壓過你的身體嗎?像這樣地壓?”
傻娟在下面點頭,又很快搖頭。楊木初望望傻娟的臉,覺得還是不放心,用手撥拉傻娟褲子的松緊帶,往下撥拉。
“還這樣,把你的褲子往下剝掉嗎?”楊木初說。
傻娟搖頭,又很快點頭。楊木初突然覺得自己的血在涌動,他的身體差點兒整個地癱軟到傻娟的身上,可他猛地一用力,差不多從傻娟的身上跌落到了床前的踏板上。
七
沈開說有一個影視組要拍竹園里的一場戲。租用一下楊木初家的竹園,給500元,問楊木初干不干。
竹園里的牌九場子散去時,贏家只留下100元的場子費,現在卻給500元,這筆賬傻子也會算。楊木初答應了。
沈開說,是拍一場男女戲,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在竹園里相互追逐,女的追啊追啊,最后卻不見了那男的,就在女的失望之時,鏡頭切到了當天的一輪圓月上。沈開告訴楊木初,順利的話,半天工夫不到就可以搞定的,竹園里的牌九場子可以接著開。
楊木初問:“演戲的人要不要?”
“演員早定了的,你演那個男主角的爸也不合適。”
“我哪能演,我是想讓傻娟演那女的。”
沈開露出了愛莫能助的表情。他雖是專程為這事趕到楊木初家的,可他還沒有見到傻娟,見到的話,說不準也會動讓傻娟演戲的念頭的,說不準會去極力勸說導演更換女主角的。
下午就開演了。開演前,還下了一場大雨,雨后,竹園里有無數的蜻蜓在飛,蜻蜓們時而繞著竹竿飛,時而貼著竹園濕漉漉的地面飛。楊木初聽見了蜻蜓振翅的聲音,甚至還聽見了好多蜻蜓在空中交尾時發出的聲音。開演前,楊木初還不解地問沈開:“天上的月亮呢?不是最后要拍天上月亮的嗎?”
沈開擺擺手:“主要是拍女的追那男的。那月亮會到電腦里整出來。”
一幫人鬧哄哄的,扛著攝影機的男人扎著個辮子,而一個面清目秀的姑娘卻剪著個小平頭,就在開拍前,一個胖子卻拿上一個秀發飄飄的假發套給小平頭姑娘套上。這姑娘原來就是女主角,要在竹園里追一個男的。
橫涇村的人幾乎都想來看熱鬧,大部分人被攝制組雇來的幾個壯漢擋在竹園外,只有來得早的少數幾個像漏網的魚一樣尾隨著攝制組的人在竹園里竄動。沈開想讓人把這幾個人也給清出竹園,可留著一部恩格斯一樣胡須的導演卻擺擺手,說就讓他們跟著吧。
正式開拍后,一對熱戀中的男女在竹園里追逐,步子輕盈得就像蜻蜓。男的還沒有跑出女的視野,傻娟闖進了鏡頭。傻娟原來也是一條漏網的魚。她既像是誤闖進了鏡頭,也像是要追那男的,像是要與假發女子展開同臺競爭。
導演向攝影師揮手:“停!停!”
楊木初一下子沖到傻娟身邊,他揚起了手,想給她一個耳刮子,可想想為了500元錢,給她一個耳刮子也不值的,就只是把她往回拽。
“你以為那男的是小剛?”楊木初說。
想不到這句話比耳刮子還厲害,這句話剛從楊木初的嘴中跑出,就像是撞痛傻娟了,傻娟一下子坐到地上,先是茫然四顧一下,然后哭起來。
從身后幾個村民的竊竊私語中,導演知道老楊家這個長得不比假發女演員差的女兒腦子是有問題的,所以他最終把罵人的話咽進了肚子里,要老楊把傻娟領回家去,也終于對那些漏網之魚一樣尾隨在后的村民下了逐客令。
楊木初從地上拽起了傻娟,轉身時,他的額頭撞上了一根粗大的毛竹竿,他心里就有點毒,抓著傻娟手臂的右手用上了力,本來已經停止哭泣的傻娟又發出了哭聲。
楊木初把哭哭啼啼的傻娟牽回了家。
夜里,楊木初在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月光從沒有拉上窗簾的木格子窗子里投進來,像一層霜似的敷在床板和光著膀子的楊木初身上。
其實,沈開應該帶著攝制組再來一次,來拍竹園上空的真月亮。楊木初想象著此刻的月亮該像一張圓圓的發亮的大餅,這大餅樣的月亮總比從電腦里整出的月亮好吧。說實在的,他也想不明白怎么從電腦里搗鼓出月亮。既然能搗鼓,他們不來就不來吧,好像他老楊拿了沈開500元錢后,貪心不足,想再拿一次似的。
北面墻角落里的蟲鳴聲斷了,可一陣嘈雜聲卻從外面傳來。楊木初凝神,嘈雜聲像是從瓦屋北面的竹園里傳來的。差不多半夜了,牌九的夜場也散了,會有什么聲音呢?楊木初正嘀咕,有人影在木格子窗前晃動,繼而有人“砰砰砰”地敲響了他家的木門。
“楊木初楊木初,你家的竹園著火啦。”
楊木初從床板上驚跳起來,竄到了客堂,見客堂的門已經開了,村上的幾個人已經站在了客堂里。他們怎么進來了?門閂難道沒有閂上?顧不得這些了,楊木初往屋外沖,進了屋的幾個人也跟出來,有人說:“不要急不要急,已經被撲滅了。你去看看。”
楊木初放慢了腳步。
“你去看看到底怎么起的火。”有人又說,口氣里還有一層沒有說透的內容。
楊木初心里犯起疑惑,邊琢磨著那人話里沒有說透的那層意思,邊繞到了自己家的屋后。空氣中飄來了一股焦臭味,楊木初翕動一下鼻子,帶緊了步子。
在竹園東南角的一片叢生竹邊圍著一幫人,焦臭味顯然就是從那里傳出的。楊木初家的竹園里就東南角上種植著五六片叢生竹,竹園里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株一株的散生竹。雖然散生竹不容易點燃,可一旦竹園里隨便哪一處起火,由于散生竹的頂部基本是連在一起的,整個竹園就有滅頂之災。
那幫人看到了楊木初后,散開了一條縫隙。那幫人中有不少是婦女,一名因參加過撲火而使自己的頭發散亂開來了的婦女拉住楊木初的衣角:“你女兒又發癡了呢。”
在一叢一半已經被燒黑了的竹子下,傻娟坐著,叢竹的陰影籠罩在了她的臉上,使她的臉看上去也像一小塊燒黑了的東西。
“拉她也不肯起來。”又有一名婦女說。
“走。”楊木初一拉就把傻娟從地上拉了起來。
八
“你們誰敢動這里的一根竹子,我這老命就不要了。”楊木初朝卡車上跳下來的人喊,他的手里拿著一把鎬,樣子很嚇人,那幫人停住了腳步。
楊木初家的竹園只有南面的一個進口,別的地方都扎緊著荊樹籬笆。其實,只要用一把砍刀就可以在籬笆上砍出一個豁口的,可既然有了一個進口,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往那個進口處走了。
動遷辦副主任黃玉龍帶著這幫前來砍竹的人,他說,雖然他們這是文明動遷、人性化動遷,可不管楊木初接受不接受動遷辦給出的竹子賠償價,他們都會先把竹園里的竹子砍下來,讓許紅弟的工藝品廠收購去,而這收購費是給楊木初的,是楊木初在得到動遷辦給出的竹子賠償款后額外得到的。
可楊木初不認這話,我不要你們動遷辦給的賠款,也不要許紅弟那個工藝品廠的收購費,可以吧?他還看到從兩輛卡車上跳下來的人竟然大部分是河南人張桂根手下的,心頭的火更大了。一會兒替村里人去鬧事,一會兒又反過來找村里人麻煩,兩頭吃啊。他定定神,在人群里沒有發現張桂根,卻發現了跟他鬧過不高興的廢品收購站的李子。
“你們都給我滾。”楊木初大聲說。
楊木初現在底氣很足,因為本村的一些男女老少也來到了他的身邊。他沒有招呼,他們卻來了,可見,一旦發生啥事,村上人還是能抱成團的。村里人認為,動遷辦開始動楊木初家的竹園了,那么離動別人家竹園的日子也不遠了。
對峙的局面一旦形成,時間仿佛如凝固的膠水一樣,化不開,流不起來了。后來,大家都在心里等,等中午的時候快到來,中午的時候一到,大家就可以回去吃飯,就可以與動遷辦支使來的人一道離開這里了。
陽光通過竹園入口處那棵苦楝樹的枝葉,斑斑駁駁地灑落到地面上。卡車上下來的大部分人都站在了樹下,陽光的斑點也像蝴蝶一樣在他們的身上跳動。有幾個人想在樹底下坐下來,可是被黃玉龍制止住了。
“又不是要你們在鎮政府門口靜坐。”黃玉龍說。
這批人是黃玉龍叫來的,黃玉龍找到張桂根時,張桂根起先有點犯難,說這些人一直是幫村里人干事的,現在怎么能去挖村里人的墻腳呢?黃玉龍說,怎么是挖墻腳呢?是幫楊木初家砍竹子,砍下的竹子仍是楊木初的,賣給許紅弟的工藝品廠后,錢是給楊木初的,而弟兄們砍竹子當天的人工鈿卻由動遷辦來支付,這不是在幫楊木初又是什么?
叫外地人去砍竹,動遷辦主任喬建中起先也是不同意的。他認為這些外地人有奶便是娘的,怎么能叫他們砍竹?黃玉龍反駁,正因為他們有奶便是娘,所以,只要給他們奶喝,他們就會干得更賣力。何況要在附近找一批愿意砍竹的人,一時也是難找的。黃玉龍嘴皮子的一陣翻動,終于讓喬建中和張桂根打消了疑慮。
干等在樹下,時間真的凝滯的膠水似的,流不起來了,苦楝樹上突然響起的一聲蟬鳴也顯得十分悠長。樹下的一個人像是猛地被這聲蟬鳴從昏睡中弄醒了似的,問黃玉龍:“到底讓我們砍不砍了?不砍的話,一上午的工鈿會付我們嗎?”
黃玉龍看一眼站在竹園入口處的村民,喉骨“咕嚕”轉動了一下,說:“沒有砍竹子,怎么能算你們工鈿?我們也要按株給你們結算工鈿的。”
廢品收購站的李子當下就叫起來:“操哪,當我們什么啊?”
剛才問黃玉龍的那個人也高聲嚷:“走走走,我們撤。”
有人不愿意撤:“那我們剛才耗在這里算是白耗了?我們走的話,不是被人當猴耍了?”
大家都覺得這句話講得對,如果現在就走的話,真是把他們當猴子耍了。可不走,萬一這黃玉龍最后真是一毛不拔,那不是又要在這里多耗一段辰光嗎?一位年紀稍大一點的胖子看上去是個好脾氣的人,他朝離他大約有六七步遠的楊木初開口:“老阿哥,我真不明白,有一大筆賠款,賣了竹子的錢又歸你,還要那個爛竹園干啥?”
“是啊,還要這爛竹園干什么?”有人附和,“里面的牌九場子也不會讓你設長的,老派就要來沖的。”他們叫派出所的人為老派,不知是為了表示敬畏還是為了表示輕視。
怎么是那幫外來人員開始做楊木初的思想工作了呢?黃玉龍覺得好笑,也覺得自己是失職了,他清清嗓子,示意別人不要開口了。
“老楊啊,”黃玉龍擠著一對小眼睛,像是在思考著要說些什么,“他們講得對。再講,聽說許紅弟想把自己的廠賣掉了,真賣掉了,這廠還收不收竹制工藝品還是個疑問呢。”
黃玉龍講得很溫和的,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這句比所有外來人員講得要溫和得多的話,倒像是一下子惹惱了楊木初,大家聽到楊木初的喉頭發出一記怪異的叫聲,朝苦楝樹下沖過來,手臂掄圓了手中的鎬,嘴里那怪異的叫聲像是沖鋒號角似地繼續響著。
對于被叫來砍竹的那些外來人員來說,最讓他們難受的其實是沒有事情可做,而一場沖突往往正是他們在內心所期盼的。他們千里迢迢地從偏遠省份趕到這里來不是為了享受清閑的,他們是來找事的,這事可以說是能掙錢的各種生活,也可以是能點燃他們熱血的一場沖突。現在,他們在苦楝樹下左騰右突地躲閃著楊木初手中的長鎬,個個顯得那么生龍活虎。一個人的大腿像是被楊木初的長鎬終于擊上了,他發出一記既像是痛楚又像是興奮的叫聲,緊隨著這叫聲,楊木初握著鎬柄的雙手也終于被人捏住了,那把長鎬迅速變成了外來人員的戰利品,楊木初本人也被摁到了地上。就在這個時候,剛才一直站立在竹園入口處的本村的男女老少沖了過來,他們的喉嚨口也發出了楊木初沖到樹下時發出的那種嘯叫。
看到事態擴大了,黃玉龍吼叫起來:“都給我站住!”
他覺得這時候手中如果有一把槍的話,他肯定會朝著樹底下開的,而絕不會像電影里放的那樣往天上開。
“都給我住手!”黃玉龍覺得自己的身體像要騰空而起,結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么到人群中央的,他在人群中央邊揮舞著手臂邊繼續吼叫著,“你們這群豬玀,都尋死啊。”
黃玉龍的臉上和胸膛各挨了一拳后,沖突的雙方也終于住手了。外來人員中響起了一個粗聲粗氣的聲音:“走吧,算我們倒霉。”
橫涇村的那幫人則依舊衣冠不整地站在樹下,他們的腳像是和身邊的那棵樹一樣,在地上生根了。臉上掛了彩的黃玉龍彎下腰,想把躺在地上的楊木初攙起來,想不到楊木初甩開了黃玉龍的手,女人似的說:“別碰我!”
他躺地上的身體也像是生了根。不過,當苦楝樹上已經停了好一陣的蟬鳴又突然響起時,楊木初被喚醒了似的從地上爬起來。他旁若無人地拍拍自己身上的塵土,然后朝自己家的竹園走去。
村上人的腳也在地上動起來,當他們往前邁動幾步后,楊木初猛然轉身,再一次女人似的說:“別跟我。”
黃玉龍這時發覺老楊臉上的神態和他的兩個女兒,特別是小女兒珍珍像極了。他想,楊木初腦子壞了。村上人幫他趕走了那幫外地人,他卻一點也不感激,倒像是村上人也得罪了他。
村上人站住了。他們是為了他才與外來人員發生沖突的,現在楊木初既然一點也沒有感激的意思,反而好像對他們有意見了,他們就覺得很無趣。
很快,苦楝樹下就空蕩蕩了。
不多會兒后,楊木初家竹園的上空有幾縷濃煙升起。有幾個剛才從苦楝樹下撤離的村民看到了那裊娜著升起的煙塵,心里“咯噔”一下:難道傻娟又去了她家竹園東南角的那片叢生竹下了?他們想立刻跑去看看,可很快耳邊再一次響起了楊木初那聲“別跟我”的話。
他們覺得要不是楊木初傻了,就是他們自己傻了,自己在苦楝樹下被人傻瓜似的耍了一回。現在如果再往楊家竹園那里跑,他們就是想當第二回傻瓜。
這一天真是奇怪,即使沒有到過苦楝樹下的村民,竟然也沒有一個再到楊家竹園那里去。而那天夜里,雖然夜已經很深,卻居然還有好多村民跑到了楊家竹園去,把一叢竹子上的火給撲了。
九
許紅弟把楊木初接到北大街上的“漕溪人家”飯店里,兩人居然又坐在了上趟坐過的那只臨窗方桌旁,只是這一次沒有沈開在場。
“老楊,你沒有變傻。”許紅弟邊招呼服務員邊說。
“可橫涇村一半以上的人說我傻了呢,把自己家的竹園都燒了。”
“真傻了倒是樁好事,”許紅弟俯過臉來,“我也想傻啊。前天夜里,我想把我的廠一把火燒了。”
楊木初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不過,這神色很快消去,他把臉轉到窗外,漕港河清澈的河水在微風中輕輕漾動,有水鳥在水面上閃電般地掠過。
當許紅弟問他要喝什么酒時,他才把臉從窗外轉回來。
“紹興特加飯有沒有?”楊木初問。
服務員回答說沒有,楊木初就要服務員隨便拿一瓶什么黃酒來,又開口:“怎么又想到要請我吃飯了?我皮厚,怎么跟來了,其實是承受不起的。”
“哪里話。”
“到底做啥又要請我吃飯?”
“做啥?我也不曉得。”想了想,許紅弟又開口,“就是有一次,突然想把你請過來,讓你也把我的廠燒了,因為你傻了嘛。有些事只能叫傻子辦。”
“你講這話,你才真傻了呢。”楊木初瞪大了眼睛。
“我沒有傻,傻的話,自己燒了。”
“你日子這么好過,卻要燒掉自己的廠,你不是傻子,誰是傻子?你是被錢撐傻了。”
許紅弟哈哈笑起來。這時候,酒和冷菜都來了。兩人就吃喝起來。
“就為那次突然想把你請來放火這個念頭,今天才接你來喝酒的。”許紅弟說。
“許總,那你還要不要我放火了?”楊木初問得很認真,臉上那種認真的神色差不多又要讓許紅弟覺得他是真傻了。
許紅弟又與楊木初碰了一杯,說:“都說你傻了,我看不像。”
沉思一下,再一次開口:“其實做傻子也蠻好。”說罷,就獨自猛灌了幾口。
聽說最近許紅弟的工廠碰到一些麻煩,到底是什么麻煩,楊木初也不愿去打聽。見許紅弟那么灌自己,就勸他少喝。
“老楊,我、我不能做那事的,你知道嗎?”許紅弟有點醉意了,講話時舌頭顯得僵硬。
“知道,你說過,你白天沒有鳥事,晚上鳥沒事。”
許紅弟剛想講什么,想不到楊木初又開口了:“我沒兒沒女的,整那么大一個廠干什么?”
許紅弟打了個酒嗝,盯住了楊木初:“老楊,你其實不會傻的,你家不會出第三個傻子的。”
窗外,有櫓聲傳來,兩人都動了動頭頸,看到船上小女孩的玉臂伸進窗里,她手中是粉白色的花束。
“阿要買花?”
許紅弟拿過身邊空座位上的皮包,拉開拉鏈。
“拿去。”許紅弟說。
小女孩看著許紅弟手上好幾張鈔票,眼睛里露出不相信眼前景象的神色,手伸了一下,又縮回去。
“拿去!”許紅弟直起了身子,把鈔票扔進了鴨頭小船的艙里。
粉白色的花束也沒有給,鴨頭小船就慌忙地調轉了頭,偷了什么東西似的快速往西劃去。
楊木初伸頸,看到小船的后面形成了一條蛇一樣的水波,向西逶迤而去。
楊木初囁嚅著說:“你的廠再有麻煩,你也比楊家有更多鈔票。”
“對,所以,你家不需要有啥鈔票,你還守著那個竹園做啥呢?”許紅弟歇口氣,手往空中一劈,“不需要!傻娟以后一定會過上最好的生活!”
楊木初又一次往船窗外望去,小船剛剛留下的蛇一樣的波紋已經不見了,整個河面平滑如鏡,反射著晃眼的光亮。
責任編輯 曉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