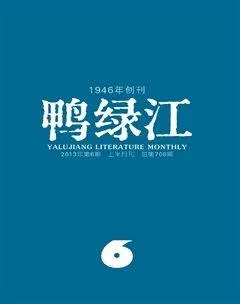兩個(gè)人的戰(zhàn)爭(zhēng)
楊逍,本名楊來(lái)江,1982年生于甘肅張家川。2008年出版詩(shī)集《二十八季》。2009年開(kāi)始在《文學(xué)界》《飛天》《延河》等刊物發(fā)表小說(shuō)。多篇小說(shuō)被報(bào)刊轉(zhuǎn)載。
正如大家之前見(jiàn)到的和能想象的一樣,這場(chǎng)戰(zhàn)斗仍然存在著不可理喻和幽默的雙重游戲特性。觀眾以老幼婦女居多,男人似乎對(duì)這樣毫無(wú)刺激的戰(zhàn)斗不感興趣。這對(duì)高莊的人來(lái)說(shuō)都已經(jīng)司空見(jiàn)慣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只見(jiàn)兩個(gè)衣衫襤褸的漢子,渾身沾滿泥漿,一些柴草和破敗的爛菜葉嵌進(jìn)他們的頭發(fā)和臉上,甚至還有血跡,其中一個(gè)矮胖子的鞋子不知什么時(shí)候丟掉了,另一只腳則被泥漿包裹起來(lái),像是鍍上金粉的羅漢的手臂,他光著的腳板正好踩在一塊棱角不太分明的碎石上,可他依舊狠著勁,死死地抓住瘦高個(gè)的領(lǐng)口,那塊石頭反而成了他的倚靠,他口齒含糊,發(fā)音并不清晰敞亮,眼睛混沌無(wú)光,絲毫沒(méi)有精明強(qiáng)干的人所特有的炯炯有神。那個(gè)瘦高個(gè)的情況似乎要好一些,他僅僅是左側(cè)的褲腿撕開(kāi)了一條縫,也許是早些日子不小心劃破的,他的神色比矮胖子好多了,因而他的聲音高亢而尖細(xì),吐字較為清晰,他不斷地環(huán)視人群,沖其中某個(gè)人嘿嘿一笑,牙齒竟然潔白。明顯能看出他的力量并不比矮胖子好,但他用勁巧,能笨拙地躲開(kāi)對(duì)方的幾次強(qiáng)勢(shì)進(jìn)攻,他的得意溢于言表,他不停地叫著,狗日的,敢和我斗。他每說(shuō)完一次,都要咧嘴一笑,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善良。矮胖子說(shuō)話不大連貫,且發(fā)音不準(zhǔn),鼻音很重,還帶有結(jié)巴和淺舌子的缺陷,把方言說(shuō)得像西班牙語(yǔ),但大家都能基本聽(tīng)懂,無(wú)非是和瘦高個(gè)對(duì)罵的一些臟話。他們多數(shù)時(shí)間就像兩只對(duì)峙的螳螂,互相抓著頭發(fā)和領(lǐng)口,過(guò)上一陣子換個(gè)姿勢(shì),偶爾在腳底下來(lái)幾次磕碰,也不兇猛。他們的對(duì)罵是最有趣的,引得眾人大笑不止,倘若夾雜上古怪的表情,便能使一些失笑過(guò)多的女人俯身揉著肚子,笑作一團(tuán)。他們的對(duì)峙往往要持續(xù)上好幾個(gè)小時(shí),直至彼此累了才肯罷手回家,由此,觀眾也不穩(wěn)定,來(lái)來(lái)回回?fù)Q了好幾撥。
這樣堂堂正正決斗的兩個(gè)人是郭義和常河,在方圓幾里享有盛名。大家之所以關(guān)注他們,是因?yàn)樗麄兒驼H瞬⒉灰粯樱兄傋踊蛘呱底拥南右伞N伊?xí)慣于稱他們是兩個(gè)瘋子,因?yàn)樵谖铱磥?lái),瘋子大約帶有一些調(diào)侃或是親切的成分,就像熟識(shí)的老朋友見(jiàn)面一樣,而傻子則多少有些生硬,或者含有貶意,包含了弱智的根本元素。我寧愿相信他們和正常人一樣,甚至比正常人更有值得贊揚(yáng)的地方,至于他人的說(shuō)法,我則不去理會(huì),盡管有人抱有怨恨,鄙視甚至偶爾毆打他們,我倒也覺(jué)得不十分過(guò)分,因?yàn)樗麄冊(cè)揪秃驼H瞬惶粯印?/p>
矮胖子郭義也許要比瘦高個(gè)常河的智力更差一些。準(zhǔn)確地說(shuō)常河犯病的機(jī)會(huì)比郭義要少很多,程度也輕。至于郭義犯病時(shí)的可怕情形,但凡和哥哥一樣年齡的人,時(shí)至今日都心有余悸。郭義通常像野蠻人,喜歡住在幽深潮濕的山洞里。哥哥說(shuō)那時(shí)候的高莊廢棄的窯洞隨處可見(jiàn),據(jù)說(shuō)是舊時(shí)牧羊人的棲身之所。因而郭義的行蹤就很難被人掌握,當(dāng)他的家人在西山的梁上尋找他時(shí),他也許正在東山的某個(gè)洞里睡得正好,有時(shí)并沒(méi)有睡著,卻不答應(yīng),好像此起彼伏的喊聲與他無(wú)關(guān)。
尋找郭義最多的是他的母親,那個(gè)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年輕的時(shí)候落下了風(fēng)濕病,腿腳不大靈便,而所有的苦難卻似乎都降臨在了她的身上,三十多歲的時(shí)候死了丈夫,她本想用自己的堅(jiān)強(qiáng)來(lái)和命運(yùn)的不公平相抗?fàn)帲涩F(xiàn)實(shí)卻并沒(méi)有按照她所期望的到來(lái)。她辛苦地抓養(yǎng)著兩個(gè)孩子,大兒子在八歲那年,從三米高的槐樹(shù)上跌落下來(lái),摔斷了腿。衛(wèi)生院老眼昏花的趙老大夫一手經(jīng)營(yíng)著蕭條破敗的診所,在面對(duì)女人的焦灼和孩子的疼痛時(shí)微微一笑,他裝了一鍋旱煙,閉上眼,雙手在孩子的腿上游走了一陣,然后一咬牙,一用勁,只聽(tīng)骨頭斷裂的聲響和孩子絕望的痛叫糾纏在一起后,他就拍拍孩子的肩膀說(shuō)沒(méi)事了,回去吧。就這樣,她就把孩子帶回了家,根據(jù)趙老大夫不必吃藥的理論,她僅僅付了他一元八角的手術(shù)費(fèi)。可怕的后果是幾年后孩子漸漸長(zhǎng)大了卻跛得厲害,起初離不開(kāi)拐杖的依托,她也去找過(guò)大夫,可那趙大夫卻羅列了一堆狗屁醫(yī)術(shù)上的條條框框讀給她聽(tīng),在她似懂非懂的時(shí)候,就被怒發(fā)沖冠的他指著鼻子罵了出來(lái),爾后她就安心下來(lái),她相信趙大夫的高明。可孩子長(zhǎng)到二十歲的時(shí)候也不見(jiàn)好,等她如夢(mèng)初醒的時(shí)候,趙老大夫卻早已退休不知去向,她除了看著孩子的腿哭泣和自責(zé)還能做什么呢。
所以,她就把全部的心血放在郭義身上,她發(fā)誓說(shuō)一定要讓他健康快樂(lè),而郭義長(zhǎng)至五六歲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和同齡的孩子有了差別,連吃喝拉撒都毫無(wú)節(jié)制,反應(yīng)遲鈍和身體羸弱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標(biāo)簽,大家都看出了孩子的不正常,而她卻堅(jiān)持不信,甚至還惡言相向,罵那些建議她給孩子治病的人,說(shuō)他們壞心眼,戳她的短處。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學(xué)了,郭義還不知道饑寒飽暖,她才不得不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shí),她對(duì)此前的七八年做了一番詳細(xì)的回憶,最后得出結(jié)論:郭義可能是在三歲那年高燒不退落下的病。至于她的推斷是否正確都已失去意義,人們除了無(wú)限惋惜以及對(duì)她報(bào)以十分真誠(chéng)的慰問(wèn)還能做什么呢。生活似乎一下?lián)艨辶怂顾诖撕蟮膸啄昀锫淦堑搅钊藚拹旱牡夭健K偸欠耆吮阏f(shuō),郭義生下來(lái)是好的,就是被高燒害了,要不然他也能上學(xué)了。剛開(kāi)始她說(shuō)得多,人們回應(yīng)得也多,到后來(lái)就只變成了一句話:要不然郭義也能上學(xué)。但她得到的卻已經(jīng)不是人們的同情了,而是他們的白眼和不屑,甚至有人還在她的面前故意說(shuō),一個(gè)傻子怎么能上學(xué)呢。她也不氣恨,到下次見(jiàn)了,仍然說(shuō)著那句話。
哥哥說(shuō),那個(gè)可憐的女人以后就一直為郭義奔波著。從此,高莊的人便總能聽(tīng)見(jiàn)她漫山遍野、挨家挨戶呼喚郭義的聲音,時(shí)而尖細(xì),時(shí)而高亢,有時(shí)清晨的露珠還沒(méi)有散去,有時(shí)太陽(yáng)正在當(dāng)空高掛,有時(shí)則是漆黑的暗夜。但她的呼喚似乎總是徒勞的,沒(méi)有人聽(tīng)見(jiàn)過(guò)一次郭義的回應(yīng),她一個(gè)人奔走在大街小巷,田埂地畔,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孤魂野鬼。于是,有人開(kāi)始詛咒她,背地里或是當(dāng)面,言詞毫不顧忌,說(shuō)她是催命的鬼。
她對(duì)郭義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當(dāng)然不是為他討要?jiǎng)e人家剛出鍋的熱饅頭,也不是定下一門親事,而是多次哀求村小的校長(zhǎng),要他收下郭義在學(xué)校里混上幾年,她說(shuō),說(shuō)不定,過(guò)幾年,他就能好起來(lái)。校長(zhǎng)當(dāng)時(shí)為難極了,好話勸她別瞎折騰,說(shuō)即使要上學(xué)也要去外面大城市里的智障學(xué)校,那里有專門的老師教。一聽(tīng)這話,她就跪下了,當(dāng)著眾多的學(xué)生和老師以及一些有頭有臉的村里人,她哽咽著語(yǔ)無(wú)倫次,眼淚順著脖子直往衣服里鉆。校長(zhǎng)無(wú)奈,只好敷衍地答應(yīng)了。其實(shí),校長(zhǎng)也是給自己找了個(gè)臺(tái)階下,他覺(jué)得她只是一時(shí)沖動(dòng)而已,等她清醒了,就不胡鬧了。可誰(shuí)想,第二天,她就把郭義打扮得煥然一新,并親自送到校長(zhǎng)的房子里,直至校長(zhǎng)把郭義領(lǐng)進(jìn)了一年級(jí)的教室,她才滿意地笑了。此后,她逢人便說(shuō):我家郭義也上學(xué)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她心中的無(wú)上自豪。那一年,郭義十歲。
郭義的到來(lái)為一年級(jí)的同學(xué)增添了不少樂(lè)趣,他們像歡迎古代部落的族長(zhǎng)一樣給予了他最大的榮耀。老師們不得已把郭義安置在一個(gè)相對(duì)自由的空間里,在最后一排靠近后門的角落里他有了屬于自己的地盤,那兒任由他吃喝拉撒睡,誰(shuí)都拿他沒(méi)辦法,老師的訓(xùn)斥在他眼中不值一提,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像舊社會(huì)的無(wú)賴地痞,但大家都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倘若他高興起來(lái),就在老師講得正起勁的時(shí)候在教室里走動(dòng),或者主動(dòng)上去幫老師擦黑板,偶爾也會(huì)對(duì)老師的白眼感到害怕。當(dāng)然,也有老師對(duì)他絕不寬容,他們報(bào)著泄憤的心態(tài),把平日里積攢下來(lái)的恩怨找個(gè)機(jī)會(huì)一股腦地拋給郭義,讓睡夢(mèng)顛倒的他在毫無(wú)防范的情況下吃盡苦頭,即使皮開(kāi)肉綻、他哇哇大叫也絕不手軟。而郭義的母親卻在他遭到這樣的毆打之后反而興奮不已,她說(shuō)這是老師教育他呢,是好事。
而更多的時(shí)候,郭義只專注于自己的事。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別人搶奪皮球,以致在爭(zhēng)奪中頭破血流。由于他大過(guò)其他孩子幾歲,因而在身體上占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所以他總是能在斗爭(zhēng)中獲得勝利。也許是他本就不能克制自己的好動(dòng),或者完全是故意為之,不管怎么說(shuō),他后來(lái)都漸漸失去了和別人一起玩耍的機(jī)會(huì),大家都排斥他,像躲瘟疫一樣躲著他。而他在失去同伴的情況下,便常常伺機(jī)而動(dòng),尋釁鬧事,攪得教室烏煙瘴氣,他的母親因而便成了學(xué)校的常客,校長(zhǎng)幾次都要讓她把他帶走,但都被她央求了下來(lái)。
其實(shí),令校長(zhǎng)生氣的還遠(yuǎn)不止這些,而是他的母親在領(lǐng)他上學(xué)時(shí)隱瞞了一件重要的事。郭義有著不太嚴(yán)重的間歇性抽搐。哥哥說(shuō),他一抽搐,就癱軟在地上,眼睛上翻,呼吸急促,有時(shí)還口吐白沫,這是在一節(jié)數(shù)學(xué)課上發(fā)生的事,眼看著他快要不行了,那個(gè)經(jīng)常毆打郭義的數(shù)學(xué)老師派人找了幾根柳條,他把那些柳條擰在一起,朝他的身體大膽地抽打,大約幾分鐘,郭義就慢慢緩了過(guò)來(lái),等完全醒轉(zhuǎn),像是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用十分茫然的眼神看著四周,眼睛里竟然充滿怒氣。事后,大家都聽(tīng)了數(shù)學(xué)老師的話:不要和郭義靠近,否則要吃虧的。而這樣的事后來(lái)竟然很少發(fā)生,即使有一兩次發(fā)生了,大家便請(qǐng)數(shù)學(xué)老師如法炮制,郭義便能得到解救,因而,郭義的母親后來(lái)還專門在學(xué)校拜謝過(guò)數(shù)學(xué)老師,說(shuō)他比衛(wèi)生院的趙大夫強(qiáng)。在和哥哥一般大的人中,他們后來(lái)都堅(jiān)信用柳條抽打身體是有效治療抽搐的方法,當(dāng)然,我也就此翻閱了許多醫(yī)學(xué)書籍,甚至包括《本草綱目》,但翻遍了所有的資料,我都沒(méi)有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這方面的記載。
乃至郭義漸漸長(zhǎng)大,和他一起上學(xué)的孩子都已經(jīng)升到了三年級(jí),而他還在一年級(jí)里渾水摸魚,不得已,他的母親便又央求校長(zhǎng)讓他升級(jí),校長(zhǎng)無(wú)奈,加之郭義的個(gè)頭躥高了很多,只好也讓他升,就這樣,郭義一直升至四年級(jí)才由于抽搐得厲害了,不得不退學(xué)。不久,他的母親撒手人寰,郭義便只好在他跛腿哥哥的監(jiān)督下干活,他已經(jīng)長(zhǎng)成大人了,身體甚至比和他同齡的人更好一些。但以他的本性,誰(shuí)都不能要求他做好什么事,他那跛腿的哥哥也無(wú)能為力,只好聽(tīng)天由命。他不干活時(shí),就任由他在方圓幾個(gè)村子里游蕩,不是遠(yuǎn)遠(yuǎn)地用石頭打了漂亮媳婦的小腿,就是把玩耍的三歲小孩嚇得哭了一個(gè)多月,或是翻墻進(jìn)了誰(shuí)家的院子和一條狗打斗,甚至是抓著牛尾巴和牛較勁,光著身子在巷子里奔走,如此等等,都已屢見(jiàn)不鮮。而常河卻并不怕這些,他大約是當(dāng)時(shí)能制約郭義的不二人選,當(dāng)然別人都不愿意花時(shí)間在郭義身上,并不是因?yàn)榕隆?/p>
哥哥說(shuō),郭義有一個(gè)鐵桶般的模樣,簡(jiǎn)直就像一座有缺損的橋墩,脖子短而粗壯,胸膛寬闊結(jié)實(shí),只是兩條胳膊不大齊整,右臂似乎要短一些,而且右手因?yàn)殚L(zhǎng)年抽搐的緣故明顯伸展不開(kāi),左邊的臉上有一道清晰的傷疤,是在玉米地里逃跑時(shí)絆倒劃傷的,身上的傷疤要更多一些,大多是犯病時(shí)被抽打過(guò)的痕跡,雙腿羅圈且走路時(shí)喜歡右腿拖在地上,因而右腳的鞋子時(shí)常是殘缺的,和他破爛的衣服一樣。他有時(shí)不穿內(nèi)衣,徑自敞開(kāi)藍(lán)布汗衫,肚子的贅肉就隨著他的顛簸一抖一抖的,并不好看。或者,他就光著身子四下里跑,一點(diǎn)也不顧及別人,二十幾歲的大小伙子在人堆里鉆,害得那些小媳婦大姑娘紛紛哇哇大叫著四散逃走,他卻跟在她們身后嘿嘿地笑,不防備時(shí)就有大團(tuán)的口水順著白花花的胸脯淌下來(lái),他也不知道擦。
但是不管他干什么愚蠢的事,他都在右胳膊上挎?zhèn)€糞籃子,左胳膊下夾著一把銹跡斑斑的沒(méi)有刃口的破鐵锨。他的鐵锨和籃子給人印象很深,無(wú)論從哪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他都有理由在村子內(nèi)外自由地游走,從造型上看,他的背影還有些男子漢的氣概,并不是松松垮垮一擊即倒的孱弱。當(dāng)然,這也是他喜歡和常河扭打的原因之一,因?yàn)楹芏鄳Z恿他的人都說(shuō),他比常河結(jié)實(shí),常河不是他的對(duì)手,再說(shuō),他還有武器——鐵锨和籃子,而常河沒(méi)有。
想當(dāng)然,郭義就不斷向常河尋釁鬧事,他堅(jiān)信常河不是他的對(duì)手。但他從沒(méi)有想過(guò)自己的弱點(diǎn),別人也沒(méi)有告訴過(guò)他,那是因?yàn)槌:臃覆〉母怕瘦^小較輕,很多時(shí)候你并不能把他當(dāng)一個(gè)瘋子來(lái)看待。而郭義則平衡感極差,除了力氣大之外再無(wú)特別。
常河變成瘋子是后來(lái)的事,哥哥如是說(shuō)。常河要比郭義年齡大些,有些老成持重的感覺(jué),他原本是個(gè)極厲害的角色,只是長(zhǎng)相有些獨(dú)特,只要見(jiàn)上一面,也許就難以忘記,他的鼻子是最典型的代表,并不像村子里的人那樣規(guī)整,而是尖細(xì)悠長(zhǎng)的那種,和他一起的玩伴都說(shuō)他是烏克蘭人,事實(shí)上,他們也不知道烏克蘭人長(zhǎng)得如何,只是大約聽(tīng)過(guò)烏克蘭種豬才這樣說(shuō)的,他們覺(jué)得烏克蘭這個(gè)名字很好。除了鼻子之外,眼睛長(zhǎng)得太小,嘴唇又太薄,看起來(lái)就像小丑,有人第一次見(jiàn)到了還會(huì)忍不住發(fā)笑。而這些都是表面的,真實(shí)的情況是他在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中出盡了風(fēng)頭。他自小就被人嬌慣。他的母親在他還沒(méi)有上小學(xué)的時(shí)候就得病死了。他有五個(gè)姐姐,而且一個(gè)個(gè)長(zhǎng)得膀大腰圓,和他的高瘦截然相反,她們不但能做完家里全部的家務(wù)和農(nóng)活,還能始終如一地留一人照看常河,常河是姐姐們抱大的。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給他添上了那種白皙和狡詐的舊時(shí)地主少爺所特有的氣派。他像游手好閑的富家公子,盡管家里并不富裕,姐姐們都衣衫襤褸,但他仍然趾高氣揚(yáng)。
常河是村子里擁有玩具最多的人,他家里也是擁有遙控電視的第一家。在所有人依然貧窮的那個(gè)年代,遙控電視帶給人們的好奇遠(yuǎn)比原子彈爆炸來(lái)得真實(shí)而刺激,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涌到常河家里要看個(gè)究竟,而常河則把大家堵在門外,只挑選關(guān)系好的伙伴放進(jìn)去,然后死死地關(guān)上門,任憑其他人在外面呼天喊地。從那以后,常河變成了大家的王,只要有人不遂他意,他便拒絕人家來(lái)看電視,若是稍帶有情緒的,便不讓摸遙控器。哥哥說(shuō),常河和父親是光著屁股坐在炕上看電視到中午十二點(diǎn)的人,而其他孩子卻要干一早上的農(nóng)活。
常河的能耐并不是他家里的遙控電視所能代表的,盡管他學(xué)習(xí)并不好,還經(jīng)常以拉肚子、感冒等小毛病逃學(xué),但這都不能影響他天才般的詩(shī)人氣息恣意蔓延。上小學(xué)時(shí)他就表現(xiàn)得非同一般,他的記憶好像專為詩(shī)歌而有,凡是需要背誦的詩(shī)詞,他都能在第一時(shí)間里記得滾瓜爛熟,而別的課文則總是背上半截兒不了了之。起先,并沒(méi)有人為此驚嘆,直到有一天,他拿著一個(gè)白紙訂做的小本子,上面寫滿了鉛筆書寫的詩(shī)歌,其中有幾句還頗耐人尋味,大家才拿出贊許和羨慕的眼光來(lái),連語(yǔ)文老師都夸他寫得好。哥哥說(shuō),那幾乎都是些順口溜,但讀起來(lái)很好,比如“高莊有個(gè)小常河,光吃飯來(lái)不干活”等等。
應(yīng)該說(shuō)常河成了詩(shī)人以后他才真正受到了別人的尊敬,誰(shuí)都沒(méi)有料到他竟然會(huì)寫詩(shī),還有模有樣,這連語(yǔ)文老師恐怕都辦不到。其實(shí),大家都不知道現(xiàn)代詩(shī)歌究竟是個(gè)什么樣子,老師也沒(méi)有講過(guò),所以就沒(méi)人懷疑常河寫滿了一個(gè)本子的東西究竟是不是詩(shī)歌。而最關(guān)鍵的是他怎么會(huì)想到寫詩(shī)呢,別人為什么不會(huì),就連想也想不到,老師們均以為是奇才,一霎時(shí),常河的名聲便在方圓的村子里傳開(kāi)了。
上了中學(xué),常河的個(gè)頭猛高了許多,而與之相反的是隨著大家認(rèn)識(shí)上的提高,他們漸漸開(kāi)始對(duì)常河的詩(shī)歌不感興趣了,甚至有人還嘲笑他,這讓常河很是尷尬,他似乎一下子還不能適應(yīng)這個(gè)轉(zhuǎn)變給他帶來(lái)的本質(zhì)上的變化。于是,他變得脾氣暴躁起來(lái),加之在家里橫行霸道的秉性,他開(kāi)始和別人打架。那時(shí)候,他的腰里總是藏著一小段鋼管,或是在鎮(zhèn)上買的雙截棍,有時(shí)還會(huì)是一把尖刀。關(guān)于他在學(xué)校里尋釁鬧事的丑聞便時(shí)有發(fā)生,有別的村子的同學(xué),在學(xué)校里組織一個(gè)團(tuán)體,把他圍堵在學(xué)校后面的廁所里向他復(fù)仇。還有人明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duì)手,便買上幾包好煙,請(qǐng)來(lái)社會(huì)上的二流子,闖進(jìn)校園或是等在回家的路上找他的麻煩,而常河的非凡能耐,在此時(shí)就能大顯身手,他很少被強(qiáng)大的勢(shì)力攔劫,也不知是他的同伙向他通風(fēng)報(bào)信,還是他有預(yù)感,總之他一直都能逃之夭夭,而遇上弱小的,他就和他的同伙群起圍攻,直至對(duì)方落荒而逃或是罷手告饒。誰(shuí)都知道常河的能耐,我們也在那時(shí)受到了他的保護(hù),哥哥說(shuō)。
不能否認(rèn),常河之所以大打出手,是與他漸處下風(fēng)的詩(shī)歌有關(guān)的,他希望能通過(guò)這種途徑獲得別人對(duì)他的尊重,以及對(duì)他那個(gè)小本子的重新認(rèn)識(shí),他也許并不是真的想和人打架。但既然他名聲在外,就算是打架的理由如何堂而皇之,都掩蓋不了他暴露在多數(shù)人面前的蠻橫無(wú)理,同學(xué)們都躲著他,生怕和他染上關(guān)系而受到某種牽連,老師也不愿理他,更不用說(shuō)教育了。而要緊的是他真的得罪了不少人。
正當(dāng)常河由于多種原因打算退學(xué)的時(shí)候,那個(gè)深秋的晚上,他遭遇了不測(cè)。事情來(lái)得極為突然,就像電影上演的那樣。隔壁村子里的社戲才剛剛開(kāi)始,常河和他的同伙們站在一個(gè)顯眼的角落里看熱鬧,他們之所以要站在外面的角落里是為了離開(kāi)方便,他們并不喜好臺(tái)上演員的表演,少年時(shí)代的孩子具有那個(gè)年齡慣有的好奇和躁動(dòng),他們喜歡在暗地里捉弄人,把土揚(yáng)向看戲的觀眾才是他們預(yù)謀的。或者渴望能在戲臺(tái)背面的草場(chǎng)里發(fā)現(xiàn)一對(duì)不三不四的男女,甚至還渴望能和那個(gè)心儀已久的女生碰個(gè)照面,最好能說(shuō)上幾句話。但這些都沒(méi)有出現(xiàn)。反而在他正蠢蠢欲動(dòng)的時(shí)候,半塊磚頭就在他毫無(wú)防備的時(shí)候落在了他的后腦上,他當(dāng)時(shí)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血順著他的脖子流開(kāi)了,不多時(shí)便布滿了地面。
大約半年以后,常河才再次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里,他已經(jīng)沒(méi)有了先前的敏銳和霸氣,變得綿軟而憨厚。大家都說(shuō)總算撿了一條命。可常河卻見(jiàn)了人就笑,莫名其妙地笑,你就是罵他,他也不理會(huì),有時(shí)和人聊天則東拉西扯,天上地下沒(méi)有章法,完全不像之前那個(gè)寫詩(shī)的常河。后來(lái),人們才發(fā)現(xiàn)他的腦子出了問(wèn)題,大腦在某一時(shí)刻會(huì)續(xù)不上弦,當(dāng)然,人們能見(jiàn)到的也只是表象,嚴(yán)重的是他的脾氣越來(lái)越大,犯病的時(shí)候竟然力氣很大,瘋狂地?fù)p壞他能觸及的物體,有時(shí)還出手傷人。他的父親,那個(gè)輕度駝背的老人,在萬(wàn)不得已的時(shí)候就把他捆起來(lái),鎖在柴房里,任由他胡作非為。當(dāng)然,這樣慘烈的時(shí)候并不多見(jiàn),在他受傷后的最初的日子里發(fā)作略微頻繁一些,持續(xù)也久一些,直至后來(lái)便不像當(dāng)初那樣無(wú)法控制,但他也似乎被多次的犯病折騰得精神上愈加含糊了,和人交流有了困難。但不管怎樣,他都在里層的上衣口袋里裝著那個(gè)寫滿詩(shī)歌的小本子,逢人就拿出來(lái)念,在人們?cè)絹?lái)越覺(jué)得毫無(wú)新意的時(shí)候,他也不放棄,仍然堅(jiān)持著跟在你的身后,大聲地朗誦著,就像一個(gè)為藝術(shù)獻(xiàn)身的勇士。他最喜歡的地方是小學(xué)校,就是他曾經(jīng)帶著詩(shī)歌輝煌的地方,他總是找到當(dāng)初的語(yǔ)文老師,請(qǐng)他批評(píng),語(yǔ)文老師若是不肯,他就跟在他的后面永不離開(kāi),直到老師答應(yīng)了,并說(shuō)上幾句贊揚(yáng)的好話,他才興高采烈地離開(kāi),千恩萬(wàn)謝。他喜歡在小學(xué)生中朗誦他的作品,而那些孩子也像當(dāng)初哥哥們羨慕他那樣揚(yáng)起小小的腦袋,滿臉驚訝地崇拜他,他們?cè)趺匆膊荒苊靼祝粋€(gè)瘋子怎么能寫出這樣的詩(shī)來(lái)。常河似乎能在那里找到他的快樂(lè)。因而,他總是在學(xué)校里轉(zhuǎn)悠,有時(shí)坐在某個(gè)教室里聽(tīng)課,有時(shí)和孩子們一起做早操,直至他的父親拿著鞭子趕他離開(kāi)為止。之后,他便會(huì)和郭義戰(zhàn)斗。
所謂“一山不容二虎”的說(shuō)法在郭義和常河的身上便得到了驗(yàn)證。最初,郭義一個(gè)人孤單的影子在村子里或者田頭地腦出沒(méi),加之他傷人的能力不大,人們并沒(méi)有多少戒心,而現(xiàn)在多了一個(gè),并且犯起病來(lái)無(wú)所不為,大家才感到了從未有過(guò)的不安。有時(shí),你外出一次幾乎能多次和他們兩個(gè)擦肩而過(guò),那都是要擔(dān)驚受怕的,哥哥說(shuō)。也許是他們?yōu)榱藸?zhēng)奪地盤,也許是受了某個(gè)好事者的挑唆,他們二人之間的戰(zhàn)斗便愈演愈烈。
戰(zhàn)斗不分時(shí)間和地點(diǎn)。有時(shí)是在清晨,他們各自從潛伏的秘密基地里出來(lái),在村子里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上幾個(gè)來(lái)回,然后在人們開(kāi)始上地的時(shí)候,站在某個(gè)人多的地方開(kāi)始咿咿呀呀地對(duì)罵,一個(gè)說(shuō)另一個(gè)是瘋子,另一個(gè)要這一個(gè)回去干活。然后對(duì)峙。他們的戰(zhàn)斗并不激烈,反而有惺惺相惜的佑護(hù),看起來(lái)就像是做游戲,但他們卻樂(lè)在其中,縱使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有時(shí)戰(zhàn)斗發(fā)生在中午,常河總是像個(gè)大人那樣,追趕著要求郭義早些回家,而郭義卻不肯,他也要堅(jiān)持讓常河早些回家,于是扭打在一起。當(dāng)然,晚上也不例外,晚上的戰(zhàn)斗可以肯定是郭義不對(duì),因?yàn)樗矚g黑地里光裸著在村子里奔走,而常河不愿意他這樣,說(shuō)他丟人,就追著郭義要他穿上衣服,郭義不肯,就也要脫常河的衣服,然后兩個(gè)人在某個(gè)巷子口殺聲震天,直至被人趕回家去才罷手。他們戰(zhàn)斗的地方多數(shù)在山神廟前,那兒總是聚集了村里的閑雜人,他們有興趣觀看他們的戰(zhàn)斗,并為他們糊涂地助陣,而他們也為那樣的吶喊興高采烈,戰(zhàn)斗就顯得精彩一些。
幾乎沒(méi)有人想去操他們的心,也不勸解他們的戰(zhàn)斗,除非有一方流血了,不然,他們的戰(zhàn)斗總是像一場(chǎng)場(chǎng)笑話供人娛樂(lè)。而事實(shí)上,他們并沒(méi)有置一方于死地的想法,也沒(méi)有趕走一方的想法,只是那樣對(duì)峙著,以獲取更多人的笑聲。也許他們喜歡這樣,沒(méi)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shí)想法。
后來(lái),常河突然消失了。據(jù)說(shuō)是他的父親在所有的女兒出嫁后為后半輩子著想,花了好大的功夫定下了一房媳婦,他說(shuō)一定要有個(gè)女人來(lái)照顧他和常河。但那個(gè)守了多年寡的山里的女人,卻以常河犯病后打人為由不肯搬來(lái),并堅(jiān)持要常河的父親處理了常河才能做他的女人。常河的父親無(wú)奈,只好帶上他出了一次遠(yuǎn)門,在某個(gè)火車站下車后借故上廁所回來(lái)了。郭義在常河失蹤的日子里,犯了一次病,好轉(zhuǎn)以后就開(kāi)始在村子里狂奔,口里念著:常河,狗日的。沒(méi)有人知道他為何要尋找常河,紛紛為此制造了很多版本的笑話。
而出人意料的是半個(gè)月后常河竟然自己回來(lái)了,除了灰頭土臉和衣衫不整之外并無(wú)大礙,他仍然沖著人笑,別人問(wèn)他這幾天到哪兒去了,他也只是笑,看起來(lái)精神上比以前更加迷糊,不瘋反而傻了,能記住的東西也不多了,只是那個(gè)白紙的小本子還裝在口袋里,手里一直握著半支鉛筆,那個(gè)本子已經(jīng)不成樣子了,邊邊角角都卷起來(lái),一些早年的句子也模糊不清。但郭義照樣還找他打架,只是次數(shù)少了許多。
常河的父親當(dāng)然沒(méi)有娶來(lái)那個(gè)女人為伴。常河也不知道他曾經(jīng)被父親遺棄過(guò)。
幾個(gè)月后,常河又一次失蹤了,但和他的父親無(wú)關(guān)。他是自己出走的,沒(méi)有來(lái)由,下落不明。后來(lái)有人說(shuō)在某個(gè)地方見(jiàn)過(guò)和他相像的人或者背影,但都是猜測(cè),并沒(méi)有足夠的證據(jù)。而郭義在常河沒(méi)有回來(lái)之后,卻日益郁郁寡歡,在那個(gè)冬天的深夜,他光著身子在村子里從南走到北,從東走到西,從天黑走到了天明。當(dāng)早起的人發(fā)現(xiàn)他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在戲臺(tái)的角落里僵硬如冰,他的身邊放著他的糞籃子和那把破鐵锨,安靜極了。
責(zé)任編輯 鐵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