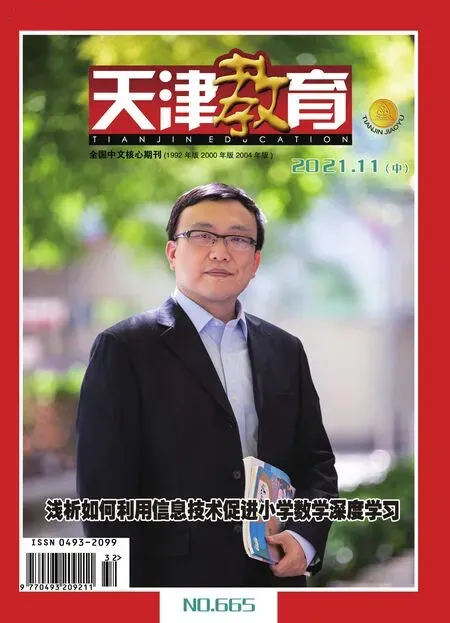關于小學班級文化建設的思考
■江蘇省啟東市合作小學 黃宏華
為培養學生從小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作風,小學班主任必須將班級的文化建設重視起來,為學生培養良好的思想品質打下堅實的基礎。要實行小學班級的文化建設,首先要從良好的文化氛圍入手,然后是豐富的班級文化活動,同時還要重視班級的精神文化建設,引導小學生向正確的人生進程邁進,培養其良好的文化素養。
一、創建班級文化氛圍
班級中良好的文化氛圍能夠培養學生的積極性,幫助學生提高其綜合素養。例如: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以節日點為引導,讓學生感受節日文化的氛圍。在母親節即將到來時,教師可以母親節為引導,在母親節當天讓學生邀請自己的母親來學校參與班級“感恩母親”的活動,在活動前,教師可引導學生給自己的母親寫感恩信。在活動當天,由教師組織相關活動,讓學生和母親一起參與其中,增進親子之間的關系。活動的末尾,讓學生將自己寫好的感恩信念給自己的母親聽,這樣不僅能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還能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因此,創建良好的文化氛圍對于班級文化建設而言至關重要。
二、組織班級文化活動
要進行小學班級文化建設,教師還可以通過開展班級活動的方式實施,并引導學生參與到活動中,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例如,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一些班級活動,如“文明班級建設”,讓學生發揮自己的想象,把班級建設成自己心目中的文明班級。在進行班級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教師可放手讓學生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對班級進行裝置,同時,還可以為班級設置相應的口號,以此展現一個班級的文化風貌,將團隊的精神融入班級活動中,展現班級風采。班級活動還能鍛煉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教師可以將班級里的學生進行分組,實行小組之間的文明活動競爭,如,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可以將不同的學習任務分給每個小組,讓學生通過小組合作完成任務,教師可在此過程中引導并鼓勵學生形成良性競爭,讓小組為著同一個目標去努力。每一次教師在組織班級活動的時候,都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其感受活動為其帶來的文化熏陶,培養學生的文化自信,讓學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圍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實現班級文化的建設。
三、創造班級物質環境
在進行班級的物質環境建設的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其中,提高學生的審美力。例如,在進行班級的文化環境布置時,要先制定一定的主題。教師在上到《少年中國說》一文時,可以此為話題,進行室內的環境設計,收集與此相關的海報、圖片、故事等貼于班級的宣傳欄里,將海報貼于室內的墻上,讓學生感受這樣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熏陶中學習。同樣,教師在開展不同的教學時,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布置班級環境,并要求學生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想法,將主動權交予學生,讓學生主動感受這樣的文化環境。此外,教師還可以利用分小組的方式,讓學生負責班級中不同區域的環境布置,并對自己所布置的環境負責。一部分學生會將自己喜歡的書籍或者有教育意義的圖片帶到班級中,豐富班級的文化角;一部分學生還會將有意義的知識或者常識用黑板報的形式在班級中呈現出來;有的小組還會將自己喜歡的名人名言用來裝飾班級的文化環境。各個小組通過不同的方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不但豐富了班級的物質文化環境,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相應的文化意識。
四、構建班級精神文化
在一個班級中,精神文化的建設是核心內容,也是班級文化建設的關鍵環節。班級的精神文明建設包括了學風、班風、價值觀等。例如,教師在進行教育的過程中,一定要先給學生強調正確的“三觀”,并對其進行引導。教師在課堂中應該給予學生一定的時間討論相關的內容,如,語文教師上到寓言故事時,要讓學生討論寓言故事中所要表達的思想以及價值觀,并發表自己的見解,讓學生內化主人公的優秀品質。同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上到有關助人為樂等相關的內容時,也可抓住此契機教育學生,發展班級精神文化。教師還要利用好時政的作用,引導學生在課余時間學習正能量的時政常識,如國家的科技成果等,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此外,教師在進行教學時也要對小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把小學生的思想觀念等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由此可見,在班級精神文化建設中,教師要注重對學生的引導,并充分利用小學生的優勢開展教學。
五、完善班級管理制度
良好班級文化的建設需建立在完善的班級規章制度基礎上,好的規章制度對小學生有正確的引導,對其行為、學習等有一定的規范作用,這同樣是優秀班級文化所必備的條件。并且,小學生的閱歷、儲備知識等還比較少,因此,其理解能力也較差,更證明了其需要良好的管理制度進行引導。比如,教師可針對本級的整體情況以及小學生的日常表現,制定并完善相應的班規。在建設班級文化墻時,有部分小學生會表現出應付心態,常常不把文化墻建設放在心上,此時,若教師采取批評的方式,小學生可能會產生叛逆心理,為緩解這一現象,教師應采用鼓勵的方式對小學生進行引導,以此端正小學生態度,提升其責任心。如在文化墻創建結束后,教師需對一直積極參與的學生進行褒獎,讓其感受到被重視,提高其學習積極性。班級管理相關制度并不是對學生的約束,教師需根據小學生的天性制定一些對其有激勵作用的制度,以此引導其在班級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于活躍性比較高的小學生,正確的引導非常重要。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需不斷完善班級管理制度,有效增強小學生的責任心,讓其進行自我管理,最終達到創建班級文化的目的。
六、結語
總之,小學班主任在班級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導,讓學生主動參與其中,不能忽視學生的主體作用。教師要把班級文化的建設置于教育的重要位置,通過不同的方法將班級文化建設進行有效落實,最終實現小學生綜合素養的培養,為其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