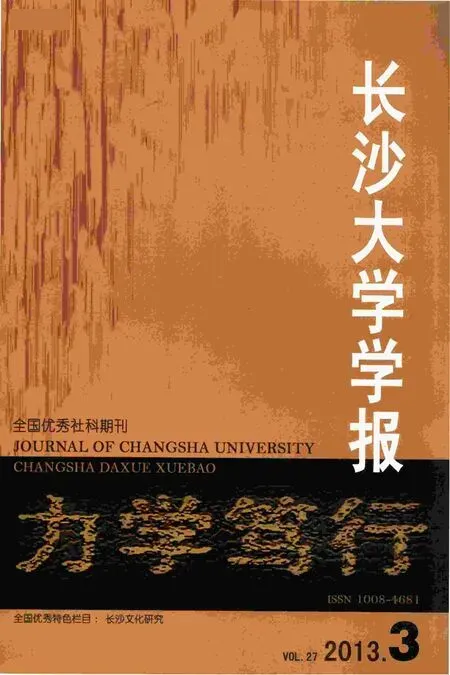歌唱中咬字、吐字的技巧探析及問題對策
朱惠華
(漳州城市職業學院教師教育系,福建漳州363000)
歌唱是一門特殊的音樂藝術,集旋律、人聲、語言為一體,具有音樂與語言相結合的雙重性,是帶有語言的音樂,是其他器樂所不能比擬的。它用準確的語言、美妙的人聲通過優美的旋律把聲樂作品的思想感情更直接地傳遞給觀眾,感染觀眾,產生共鳴。因此,語言是歌唱的基礎。在中國傳統唱論中對歌唱語言發聲有專門的稱謂,即咬字和吐字。古今中外,歷代聲樂理論家對歌唱的咬字、吐字都有精辟的論述:
“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明代魏良輔的《曲律》
“清晰的咬字,絕對不會對聲音有害處,相反會使聲音更完美、更集中、更柔和。”——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魯索
“聲、情、字、味、表、象、養”,其中的“字”,就是指要講究吐字。——聲樂教育家金鐵霖
由此可見,歌唱藝術的特征不僅以聲傳情,還得以字達意。要想達到聲樂藝術的完美境界,就必須正確掌握咬字、吐字技巧問題。
一 咬字、吐字的含義
“字”在民族傳統聲樂理論中,可分為字頭、字腹、字尾。
咬字,是指字頭正確、清晰的發音。清代許大椿的《樂府傳聲》中說:“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于喉為喉音,出于舌為舌音,出于齒為齒音,出于牙為牙音,出于唇為唇音。最深為喉音,稍出為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為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為牙音,再出在唇上位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深淺不一,舌音之深淺不一,余三音皆然。”(轉引自酆子玲《歌唱語音訓練》)[1]其中的“五音”,實際上是現代漢語拼音中的聲母部分,共有21個。即:唇音 b、p、m、f;齒音 zh、ch、sh、r、z、c、s;舌音 d、t、n、l;牙音 j、q、x;喉音g、k、h。聲母就是我們常說的字頭。體現在歌唱時就是要發好聲母,咬準字頭。
吐字,是指字腹到字尾的發音過程。其中字腹、字尾是指漢字的韻母。在我國傳統聲樂訓練中,歷來認為吐字訓練與四呼的口型、“十三轍”歸韻的訓練密切相關。所謂“四呼”,《樂府傳聲》中說:“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不僅反映韻母的口型變化,而且體現了韻母的著力部位。
二 歌唱中咬字、吐字的技巧
如上所述,數百年來,我國戲劇界的前輩在咬字吐字方面已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總結出的“五音”、“四呼”、“歸韻”、“收聲”等都是歌唱中咬字和吐字方法的精華。因此,在歌唱中就應該懂得出字收聲的要點,懂得使用唇、齒、牙、舌、喉等發聲器官,做到十二個字“字頭清晰,字腹準確,字尾快收”。針對這十二個字借用例曲來談談本人多年教學中對咬字、吐字的一些體會。
例曲:《海風陣陣愁殺人》

歌詞 海 風 陣 陣 愁 殺 人 哪聲母h f zh zh ch sh r n韻 母韻頭韻腹 a e e e o e a韻尾i ng n n u n
字頭(聲母):聲母作為一個字音的開始,直接影響到字音的清晰、準確。因此,咬字頭時必須做到三字經“快、準、狠”。“快”是指字頭發出后,要立刻過渡到字腹,時值短促,出字干凈利落;“準”是指字頭的發音部位要正確;“狠”是指咬字的力度。觀上表,“海”字出聲應念“喝(h)”;“風”字出聲應念“佛(f)”;“陣”字出聲應念“之(zh)”;“愁”字出聲應念“吃(ch)”;“殺”字出聲應念“師(sh)”;“人”字出聲應念“日(r)”;“哪”字出聲應念“吶(n)”每一個字的字頭一旦念清楚出聲后就引長其身,過渡到字腹,即韻母部分。
字腹(韻母):字頭的清晰,為韻母作了一個良好的鋪墊。一個字的發音,聲母幾乎是不發音的,字的發聲引長和最響亮的部分直接來源于韻母中的母音,歌聲就是靠它唱響傳遠。一個音節可以沒有字頭、韻頭、韻尾,但不能沒有字腹。所以有人說“歌唱是母音的藝術”。不僅關系到字音的清晰準確、共鳴大小、音色圓潤,更重要是語言的連貫性。觀上表:“海”字應引長唱“愛”;“風”字應引長唱“喔”;“陣、人”字應引長唱“恩”;“愁”字應引長唱“歐”;“殺、哪”字應引長唱“啊”。
字尾(韻尾):字尾是一個字的結束,又是字腹的延伸。它關系到字音的連貫性與完整性。歌唱語言的準確完美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字尾的收聲歸韻。韻尾占的時值一般都很短,不管一個字的時值有多長,它只占最后一拍的后四分之一時值。為了保證字音的完美,應采取十三轍來準確地歸韻收聲。如上表:“海”字要收“衣(i)”;“風”字要收入全鼻腔(ng);“陣”字要收入半鼻腔(n);“殺、哪”字沒有韻尾,要保持“a”口型不變,一韻到底,截氣收聲。
綜上所述,字頭、字腹、字尾三部分,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又各自獨立。在演唱時要把握各自特征,做到出聲有力、引腹響亮、歸韻到位。
三 歌唱中咬字、吐字的規律
咬字和吐字是發音時先后發生而又有著密切聯系的兩個步驟。可以歸納為“咬字在前,吐字在后”八個字。這是一個字發音技巧的規律,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違背,否則字、義會面目全非。咬字和吐字技巧各有特征,又是一整體,兩者既對立又統一。對立一面是咬字與吐字分別有不同的技巧要求,咬字技巧主要注重發音部位的準確及發音部位著力點的適度,吐字技巧則是注重氣息的支持、喉頭的打開與穩定、口腔的開合度。統一一面是兩者互為依存,共處于“字”這個統一體中,是一個整體。這樣,在歌唱中才能做到咬字清晰,吐字自然,達到“字正腔圓”、“以字行腔”、“以聲傳情”、“聲情并茂”的藝術境界。
四 歌唱中咬字、吐字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們有著深厚的傳統聲樂文化基礎,而且標準普通話也走向普及,但是有些觀念和習慣妨礙了咬字、吐字技巧的掌握,在歌唱中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對歌唱語言的重要性不夠重視
有些歌者只顧追求聲音的共鳴,而忽視咬字吐字的訓練,以為歌唱就是發聲技巧的技術問題,演唱時忽視歸韻收音等問題,從而造成咬字吐字不清晰的后果。
(二)美聲唱法的影響
美聲唱法因其發聲體系科學、完善,已越來越被大眾所接受,使得其他唱法都以它為基礎。美聲唱法的歌唱語言是意大利語,母音多,子音與母音的發音流暢,有利于發聲。因此,美聲唱法較注重聲音,在歌唱時極力追求整體共鳴效果。而我國漢字發音復雜,漢字的子音與母音相離較遠,增加了咬字吐字的難度,如果用這種極力追求整體共鳴效果的美聲唱法來演繹我國民族的聲樂作品,會顧此失彼,造成咬字吐字不清等問題。
(三)地域方言差異的影響
在高校里,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說話真是南腔北調。由于各種各樣的方言習慣,給我們的歌唱帶來了不少的困擾,如:鄂西北地方分不清平舌音與翹舌音,常把平舌音(z、c、s)讀成翹舌音(zh、ch、sh),把“私人(si ren)”唱成“詩人(shi ren)”;陜西關中地區分不清舌尖中音n與l,將“帶(dai)”唱成“太(tai)”,“惱人(nao ren)”唱成“老人(lao ren)”等等。
五 解決歌唱中咬字、吐字存在問題的基本對策
咬字、吐字的最基本原則是清晰與準確。在民族語言規律的基礎上,根據聲樂作品的語言風格、語言系統,對字的“五音”、“四呼”、“十三轍”、“四聲”等予以清楚交待,讓欣賞者能清楚地了解歌詞內容。在歌唱中做到咬字準確、吐字清晰,以便欣賞者欣賞到民族聲樂藝術特有的語言、旋律和韻味之美。針對上面存在的三種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幾種對策:
對策一:改變觀念,提高正確咬字、吐字的意識。
要唱好一首歌曲除掌握一定的聲樂技巧外,還需有準確的咬字、吐字能力。歌唱必須建立在語言表達的基礎上。漢斯克爾說:“從歌曲的解釋和聽眾的立場來說,歌唱者的讀字比起歌唱者的聲音更重要。在歌唱中,扎實的讀字是正確發聲的重要基礎。”[2]“凡曲以晴朗為主,欲令人知所唱為何曲,必須字字響亮,然有聲極響亮,而人仍不能知為何語者,何也?乃交待不明。”[3]一定要改變忽視咬字、吐字的觀念,沒有一定的聲音技巧是很難唱好歌的,但光有好的聲音和嫻熟的技巧而不注意正確咬字、吐字也難以感染聽眾,達不到一定的藝術效果。
對策二:恰當借鑒西洋傳統美聲的理論和經驗。
西洋傳統美聲大部分聲樂論著的主要內容都是以論述“發音”為中心的,吐字問題被放在較次要的地位上,西洋唱法認為“正確的發音方法,吐字必定清晰”。因此是發音決定吐字。這也是他們有利于歌唱發音的意大利語言決定的。母音多,字母的位置準確,元音吐發一般在口腔后部或咽腔完成。而中國的語言結構甚為復雜,由一個個單音節組成,而每一個音節又絕大多數是個獨特的音素,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聲調問題,即“四聲”。意大利語言是不存在四聲問題的。因此,在中國民族唱法中,咬字、吐字與發聲一樣,同等重要,同樣存在能力和技巧問題。因此,在借鑒的過程中,不能盲目,而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對策三:尋找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
我們常說習慣成自然,要改變各種各樣的方言習慣是一項不易的事情,但并非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可用兩種辦法來訓練。一是養成良好、正確的說普通話的習慣。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魯索曾提出“運用說話來訓練歌唱”。說話和歌唱都是同一發聲器官發出的聲音,都存在著咬字、吐字兩個動作。說話時的咬字、吐字是保持自然而然的狀態,不用注重著力點和氣息的支持,而歌唱中的咬字、吐字是在說話的基礎上被夸張和強化了。由此可見,說是唱的基礎,只要我們運用氣息的支持來夸張地說話,就可以更容易、更輕松地正確掌握歌唱中的咬字、吐字。二是采用朗誦的練習方法。朗誦是把語言藝術呈現給觀眾,歌唱是把音樂化的語言藝術呈現給觀眾。朗誦對字的要求嚴格,讀準聲母、韻母、聲調,讀出音變,這也是聲樂歌唱中必須強調的“字正腔圓”。在咬字、吐字方面,兩者要求相同:清晰、圓潤、悅耳。在氣息運用方面兩者都追求較深的氣息支持。因此有人這樣說過:“學過朗誦的人學聲樂就是走了一條捷徑。”
在實施這些對策的基礎上,再充分運用前文所說的咬字、吐字技巧,我們相信歌唱中咬字、吐字存在的問題是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的。
總而言之,咬字和吐字是歌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歌唱者必須掌握的基本技巧。只有通過對演唱中咬字和吐字技巧的訓練,才能完美地將語言和聲樂結合起來,既表現聲音的魅力,又表現語言的魅力,達到聲音美與語言美的統一,使聲樂所特有的美感得以發揮,從而征服聽眾。
[1]酆子玲.歌唱語音訓練[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
[2][意]P·M·馬臘費迪奧.卡魯索的發聲方法[M].郎毓秀,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
[3][清]徐大春.樂府傳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