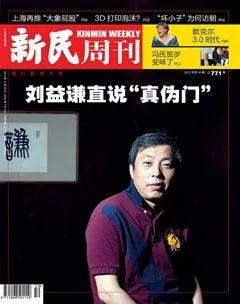無效GDP與改革紅利/世態(tài)萬象
劉洪波
“無效GDP”,是這幾天變得顯著起來的一個說法。
中國社科院學(xué)部委員、副院長李揚(yáng)說,據(jù)《中國國家資產(chǎn)負(fù)債表2013》顯示,國家凈資產(chǎn)增加額持續(xù)小于當(dāng)年GDP,表明并非全部的GDP都會形成財富積累,其中不少是無效GDP。
近幾年,反思GDP崇拜一直在進(jìn)行中,當(dāng)然GDP崇拜也一直在進(jìn)行中。經(jīng)常地,兩者是互為表里而已,但總算比過去表里都崇拜GDP好一點。
反對GDP崇拜,經(jīng)常會說到“GDP不代表什么”,例如它不代表全面發(fā)展,不反映環(huán)境質(zhì)量,不反映經(jīng)濟(jì)福利等等。這是對GDP含義的認(rèn)識,比簡單的“贊歌獻(xiàn)給GDP”好。“無效GDP”,算是對GDP數(shù)字的分辨,數(shù)字中有水分,我們一直知道,數(shù)字中包括無效部分,則是說哪怕真實的數(shù)字,也不是全然可喜。
分析資產(chǎn)負(fù)債表,是個技術(shù)活。資產(chǎn)增加額持續(xù)小于當(dāng)年GDP,表明不是全部的GDP都會形成真正的財富積累,例如過剩產(chǎn)能也在GDP中,這不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應(yīng)該從財富中扣除。我想,過剩產(chǎn)能,可能連“無效GDP”都不是,它是“負(fù)效GDP”。這就像虛胖和浮腫,虛胖可以算無效,浮腫則是疾病。
現(xiàn)在,社會似乎對GDP崇拜的荒謬已深有認(rèn)識,但GDP崇拜其實還是“實操”的寶典。增速降一點,各地都有些吃不住勁。所以拼拆遷、拼外貿(mào)、拼引資優(yōu)惠、拼拔苗助長。簡而言之,GDP本來應(yīng)該是服務(wù)于人類的,但在這里,它有時恰好是以反人類為前提的。別人本來還有個房子住,一拆,GDP有了,房子沒住的了,就是例子。
GDP世界第二,正在望一,風(fēng)光得很。“中美國”、“G2”,概念令人神往。但宋朝的GDP應(yīng)該遠(yuǎn)大于金朝,而且文明形態(tài)更高級,讓金朝一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詩句就想南侵,結(jié)果兩個皇帝都被人擄去,被迫學(xué)習(xí)打馬球。明朝的GDP不會比清朝小,比試結(jié)果則一目了然。從康乾盛世到大清終局,叫做“輝煌的落日”,不是GDP高不高的問題,鴉片戰(zhàn)爭時英國的GDP未必高過清朝,甲午海戰(zhàn)時日本的GDP低得很。
增長不等于發(fā)展,富裕不等于幸福。這在新世紀(jì)之初就已被認(rèn)識到了,現(xiàn)在過了10多年,仍然沒有表現(xiàn)為實踐的拔正。僅僅因為“國際金融危機(jī)”了,增長實在快不起來,才會“反思增長”,但高于還是低于“全國平均增速”,仍是至為敏感的,非得高一點才高興,低了就要著急,就要新動力。
沒有經(jīng)濟(jì)增長,人類自身的發(fā)展固然有限;然而一個擁有200元的奴仆,比不上只擁有100元的公民。根據(jù)百萬富翁與貧兒的財產(chǎn)總和來計算“人均收入”,只是一種滑稽;而現(xiàn)在,我們甚至連平均數(shù)都不想算了,只拿奢侈品消費世界第一、百萬富翁數(shù)量世界第一來顯示富裕程度在增加。霧霾和糧食安全問題,都在顯示“懷珠玉而死”并非神話。
人們是否能夠有尊嚴(yán)的生活,盡管不是大款和官員;是否能夠獲得公正的對待,盡管他是一個民工、一個鄉(xiāng)下人;是否能夠?qū)ι鐣磉_(dá)自己的意見,盡管他不是高級人才、留洋博士;是否能夠包容地球上的人類文明,無論這種文明是非洲土著的、少數(shù)民族的還是歐美諸國的……這些比任何一個數(shù)據(jù)更能表明發(fā)展的水平。所謂幸福,真的是比富裕和GDP遠(yuǎn)為復(fù)雜的事情。
增長不等于發(fā)展,意味著政府的責(zé)任不僅在于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各項權(quán)益的實現(xiàn)。前些時,大家爭談“改革紅利”。改革30多年了,紅利在哪里呢?GDP、國力、富翁、消費、聲色犬馬,都算是體現(xiàn)吧。普通人呢?當(dāng)然也不能說沒有,例如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大為減少了,更多的人在小康,而且就連窮人都有手機(jī)、電腦、銀行卡可用,這都是標(biāo)志。但畢竟,這是30多年,從翻身作主到有瓦房住,有收音機(jī)、縫紉機(jī)用,那也是翻天覆地。其實簡單的物質(zhì)變化,并非等同享有“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