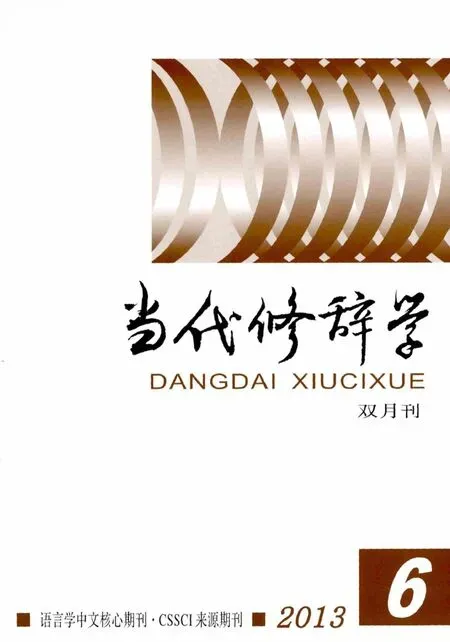語體研究方法回顧與瞻望
——基于CNKI語體研究論文樣本的統計分析
趙雪李平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100024)
提 要 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CNKI)1980-2012年語體研究的論文為樣本,從宏觀與微觀、定性與定量、對比與比較、材料性與非材料性幾個方面對語體研究的方法進行統計和分析,并對今后國內語體研究方法進行了瞻望,針對不足之處也思考了相應的對策。
一、引 言
迄今為止,語體研究方法的探索一直在進行中。如李熙宗(2011)認為應區分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具體科學方法論,將哲學和一般方法論的辨證方法、系統方法貫穿于語體研究的整個過程,以分析、綜合、歸納、比較、統計等具體方法對語體進行微觀研究。丁金國(2004)認為功能域以其域界的穩定性、規則的俗成性和域場的輻射性與語境、語體在關聯中區別開來,它較之語境與語體在應用上更具有可操作性。“現代語體風格論體系的建立,應立足于自己固有的特質,吸取現代新理論、新方法來構建。在理論上,以語義為核心的結構原則必須進入體系之中;在操作方法上,成分的離析和量化微分析應當是重要的實證性手段。”(丁金國2013)袁暉、李熙宗(2005)歸納出了語體研究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系統方法、比較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此外,還有抽樣調查、現場采錄以及歸納綜合等多種方法。
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簡稱CNKI)中1980-2012年間我國語體研究的論文為樣本,對我國語體研究的方法進行統計和分析。這樣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語體研究方法的使用現狀,而且還能夠發現語體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促進語體研究的發展。
我們在CNKI中檢索到最早有關語體研究的論文是1965年羅廷亮發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上的《英語常用詞匯和句型結構的語體區分》,這是一篇以英語語體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同時,CNKI檢索還顯示,在這篇文章問世之后的十幾年間,我國的語體研究一直是空白,直至1980年后才陸續有成果問世。1980至2012年,CNKI中以語體為主題的論文有2492篇。除去書評、簡況簡訊、大事記、紀念性文章、會議紀要等171篇外,有關語體研究的論文共計2321篇。我們以發表時間為序對這些論文進行了統計,如下圖所示:

圖1:1980-2012年語體研究論文數量總體走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自1980年至今,我國語體研究論文的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大約在1999年以后,語體研究論文的數量增長較快。這表明近十余年來語體研究受到了人們的普遍重視,我國的語體研究走上了逐步發展、逐漸深入的道路。
二、樣本的統計與分析
對CNKI中檢索到的語體論文,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所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宏觀與微觀、定性與定量、對比與比較、材料性與非材料性。
1.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
宏觀層面的語體研究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從整體上或方法論的角度來研究語體的論文。這類論文共359篇,如李熙宗的《語體學的研究方法探析》(2011)、王希杰的《語體的定義與性質的反思》(2012)等。第二類是對語體研究進行回顧、評論的論文。這類論文共108篇,如紀永祥的《新時期語體研究評述》(1995)、鄧鸝鳴等的《國內語體研究回顧與思考》(2012)等。
微觀層面的語體研究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就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語體特征進行探討的論文,共221篇,如朱巖的《〈尚書〉的語體風格》(2011)等。第二類是對某種語體進行分析的論文,共775篇,如楊達英的《政論語體的語言特點》(1984)、王燕的《新聞語體研究》(2003)等。第三類是對不同語體的語體特征進行對比的論文,共132篇,如趙瑾的《報道語體內部的分支語體對比研究》(2011)、張煥燕的《文藝語體與公文語體介詞短語差異研究》(2012)。第四類是從語體角度對某種語言現象進行研究的論文,共726篇,如張莉莉的《新興媒體中“紅段子”的語體風格研究》(2012)、蔣艷的《名詞化的語體研究》(2012)等。
從統計數據來看,宏觀層面語體研究的論文共467篇,約占樣本總數的20.12%;微觀層面語體研究的論文共1854篇,約占樣本總數的79.88%。可以看出,在語體研究中,微觀研究論文的數量明顯多于宏觀研究。對它們的歷時變化進行考察,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2: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論文數量歷時變化對比圖
從圖2可以看出,1980至1999年,對語體進行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論文的數量不相上下。大約自1999年起,這兩類研究論文的數量都有了明顯地增長,尤其是微觀研究論文數量的增長更為顯著。在1980至1999年間,微觀研究的論文僅有122篇;而在2000至2012年間,微觀研究論文的數量已達1390篇。僅在2012這一年就有181篇。正是由于微觀研究的這種迅猛增勢,才使得微觀研究論文的數量遠遠多于宏觀研究。
微觀研究論文數量較多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宏觀研究難度較大,或許是因為人們逐漸認識到了微觀研究的重要性。
2.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的哲學基礎是現象學,強調自然觀察,采用歸納分析和綜合性、描述性的方法,其理論方法的核心建立在對系統資料的主觀分析、評價的基礎之上。定量研究的哲學基礎是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實驗觀察,采用演繹法、分析法,其理論方法的核心建立在對有選擇的資料的客觀驗證的基礎之上(桂詩春、寧春巖1997)。
在樣本中,定量研究的論文與定性研究的論文篇數與占比見下表:

表1:1980-2012年語體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論文數量對比表
可以看出,在語體研究中,定性研究論文的數量遠遠多于定量研究。
從樣本來看,有學者已開始利用語料庫來進行語體研究,如朱軍和戴春蕾的《基于語料庫的有標并列短語語體適應性考察》(2012)、李靜和常院玲的《基于語料庫的英語寫作語體特征個案研究》(2012)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計算語言學界的學者對漢語語體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涌現出了劉丙麗和牛雅嫻等的《基于依存句法標注樹庫的漢語語體差異研究》(2012)、張文賢和邱立坤等的《基于語料庫的漢語同義詞語體差異定量分析》(2012)等論文。與純文科背景學者不同的是,他們不僅利用語料庫、樹庫來收集語料,而且采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漢語語體,這是語體研究在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其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上的對比原則,為語體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與單純的定性研究相比,其研究結果更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丁金國2009:249)。但是,這類論文在樣本中僅有42篇,約占樣本總數的1.81%,這表明我們對語料庫、樹庫這些現代技術了解得還很不夠。
概言之,目前我國的語體研究仍以定性研究為主,借助語料庫進行量化研究的方法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也許,這和從事語體研究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是純文科出身有關。
3.對比研究與比較研究
對比研究(contrastive study)指的是將同一種語言中的不同語言現象構成最小差異對,從中找出最小的差異點,然后把這些差異點聯系起來分析,概括抽象成系統性的規則或原理。對比研究是在同一種語言的無限事實中尋找本質特征的可靠方法。
與對比研究相對應的是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這是西方現代理論語言學的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較研究又稱跨語研究(cross-linguistic study),指的是在多種具體語言的現實中尋找普遍的東西,包括事實比較和理論比較(桂詩春、寧春巖1997:64)。
采用對比法研究語體的論文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就不同語體某方面特征進行對比的論文,這類論文共107篇,如曾毅平和李小鳳的《報道語體與文藝語體疑問句的分布差異》(2006)、劉媛媛的《藝術語體與科技語體比喻差異研究》(2011)等。第二類是對同一種語言現象在不同語體中的表現進行對比的論文,這類論文共41篇,如楊穎奇和陳偉偉的《委婉語在不同語體中的使用差異研究》(2006)、杜文霞的《“把”字句在不同語體中的分布、結構、語用差異考察》(2005)等。第三類是對不同語體進行全面對比的論文,這類論文共25篇,如劉恒的《談英語的禮貌語體和熟稔語體》(1998)、王瓊的《淺論公文語體與文藝語體的區別》(2009)等。
采用比較法研究語體的論文主要是比較同一語體在不同語言中的差異,這類論文共34篇,如徐振忠的《試論英漢演說辭的文藝語體特征》(2000)、黃佳麗的《英漢廣告語體中模糊詞語遣用比較》(2005)等。
從統計數據來看,采用對比法的論文共173篇,約占樣本總數的7.45%;采用比較法的論文共34篇,約占樣本總數的1.46%。可以看出,在語體研究中,采用對比法研究語體的論文數量多于比較研究,這也許和學者的外語水平有一定的關系。同時,我們還發現在語體研究中,無論是對比研究,還是比較研究,它們在樣本總數中的比例都很低,這說明我們對這兩種研究方法重視不夠。此外,許多學者對對比研究和比較研究不加區分,對二者的區別不甚了然。
4.材料性研究與非材料性研究
材料性研究又稱實證研究,指研究者親自收集、觀察材料,為提出理論假設或驗證理論假設而展開的研究,以有計劃、系統地采集和分析材料為基礎;非材料性研究則指不以系統采集材料為基礎的研究,包括理論及應用、描述性研究和個人經驗總結。在樣本中,材料性的論文與非材料性研究的論文篇數及占比見下表:

表2:1980-2012年語體材料性研究與非材料性研究論文數量對比表
可以看出,在語體研究中,非材料性研究論文的數量占絕對多數,材料性研究論文的數量則相對較少。
材料性研究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和第二手材料的研究。
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又稱第一手研究(primary research),指深入實地獲取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包括統計性的實驗研究、調查和非統計性的個案研究等。與此相對應的是第二手材料的研究,又稱第二手研究(secondary research),指對間接獲得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的理論性、思辨性或綜述性的研究,主要是對論文資料的綜合、分析、分類比較等。
在樣本中,采用第一手研究方法的論文有78篇,約占材料性研究論文總數的17.93%;第二手研究的論文有357篇,約占材料性研究論文總數的82.07%。可以看出,材料性研究中的大部分論文都是第二手研究。第一手研究還有待加強。
我們對第一手研究的論文進行了分析,發現采用實驗法研究的論文有2篇,分別為吳勇毅的《基于語體的對外漢語中高級聽力教學模式初構》(2005)和韓瑩的《中高級對外漢語綜合課教材中書面語體情況考察與分析》(2008),所占比例為2.56%。采用調查法研究的論文有19篇,所占比例為24.36%;其中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如劉圣心的《高級階段留學生書面語體意識的考察與培養》(2008)等。采用個案研究法的論文有57篇,所占比例為73.08%,如楊欣然的《論非結構銜接與敘事結構的把握——敘事語體寫作個案探討》(2008)等。可以看出,第一手研究的論文以個案研究為主,而實驗研究和調查研究論文的數量較少。也許,這是因為個案研究相對容易一些。
我們又從書面語語料與口語語料的角度,對第一手研究進行了更進一步地分析。我們發現在第一手研究的論文中,以書面語為語料的論文有59篇,約占第一手研究論文總數的75.64%;以口語為語料的論文有19篇,約占第一手研究論文總數的24.36%。可以看出,在為數不多的第一手研究中,還存在著重書面語研究、輕口語研究的現象,這可能與第一手口語語料采集難度較大有關。
三、語體研究方法上的不足與對策
從CNKI中的樣本來看,目前的語體研究以非材料性的微觀定性研究為主;缺少定量研究,尤其缺少借助語料庫進行量化統計的研究;缺少采用對比法和比較法進行的研究;缺少材料性研究,特別是第一手口語語料的實驗和調查的研究。
針對語體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對策:
第一,加強語體的宏觀研究,把握好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系。宏觀研究高屋建瓴,旨在揭示事物的本質和普遍規律,而科學正是一項以普遍性和一致性作為最高目標的事業(朱曉農2008:19)。語體的宏觀研究不僅要為語體的微觀研究提供理論指導,而且也為要其它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例如語法研究中的語體問題、計算語言學中的語體問題,都涉及到了語體的定義、語體的類型等宏觀層面的問題。語體的宏觀研究主要在語體的綜合層面上展開,既包括對不同類型的具體語體的特點體系進行全面描述,指明其語體風格基調;也包括確立某一特定時代的各種語體類型及由這些不同類型共同組合而成的整體的語體系統,在此基礎上確立語體規范(李熙宗2011)。語體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宏觀研究必須建立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之上。陳光磊(1991)形象地將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比作顯微鏡和放大鏡。我們在進行語體研究時,要將這兩種研究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二者不可偏廢。
第二,加強語體的定量研究,把握好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關系,大力提倡利用語料庫、樹庫等現代技術手段進行語體的量化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不僅可以通過各種統計數字客觀地呈現研究對象的真實狀態,揭示語言與其相關變量之間的各種關系,而且還可運用數理統計原理,對研究對象的整體作出具有一定效度和信度的評價,從而達到把握研究對象總體的目的(丁金國2001)。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并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定量與定性這兩種研究方法,就和人的雙腿一樣,少了任何一條腿走路就有困難(桂詩春2007:327)。基于語料庫、樹庫的量化研究為語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研究方法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語言標記的確立和提取。如果不能確定哪些語言標記在語體研究上具有普遍意義,那么再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第三,加強語體的對比研究和比較研究。在語體研究中,對比和比較是兩種重要的研究方法,只有通過對比或比較,才能發現語體內部或不同語體之間的同與異,才能揭示出語體的特征。李熙宗(2011)指出,語體的比較研究既包括語體內部上下層次的,以及某語體內部的處于同一層面的不同分支語體間的特點的比較;又包括不同語體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特點的比較。通過這種比較不但可把握該語體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特點,也可了解在不同時期的矛盾的特殊性。
第四,加強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口語材料的實證研究。在實證研究中,第一手材料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在今后的語體研究中,我們要重視第一手的研究,尤其是第一手口語材料的研究,盡量多地占有真實的口語材料。我們在采集口語語料時,可以參考一些方法,例如美國會話分析學派的轉寫系統、陶紅印(2004)收集口語語料的方法等等。
就當下研究需要而言,我們認為,通過探討深化對語體這一概念的認識,進而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界定,顯得最為迫切。語體究竟是指單純的語言形式特征的聚合,還是一個兼指語言形式特征和造成這些特征的深層動因的復合性的概念,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直沒有定論。如果將語體視為一個復合性的概念,一方面描寫一定使用域中語言的詞匯、句法和篇章結構等的系統性特征,另一方面分析造成這些特征的言說意圖、人際關系和言語行為的類型、規則和條件,或可進一步促進語體研究方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