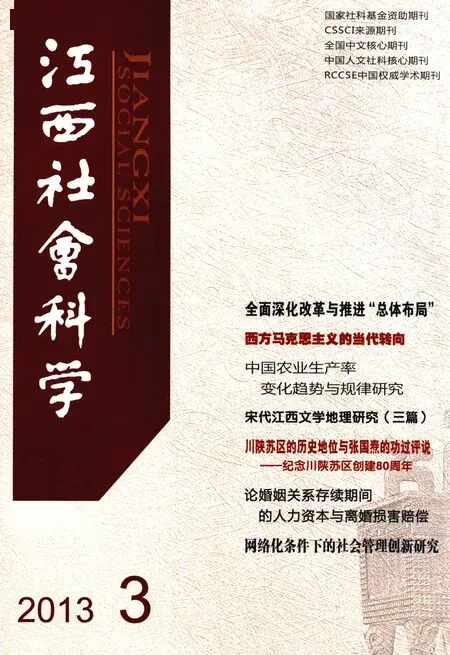從實證角度解析“習慣法”概念
■鄧崢波
“習慣法”(customary 1aw)是一個近代才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法律詞匯。[1]關于何為“習慣法”,我國學界言說頗多。然而這些論說似乎還有不夠恰當之處,本文試圖以現實生活中的實例為依據,對其概念進行解析,以求教方家。
一、幾種常見觀點的質疑
如何理解“習慣法”這個概念,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但這些觀點從實證的角度看均存在一些不當之處。
一是認為只有全社會認可的習慣才是習慣法。此種觀點認為習慣可分為個人習慣和社會習慣,只有社會習慣才能成為習慣法。[2]一般看來,這種觀點并不存在什么問題,但也不應該絕對化。在我國合同法中交易習慣是習慣法。同時我們也知道,交易習慣可分為一般習慣(適用于全國或全行業的習慣)、特殊習慣 (適用于特殊地域或特殊群體的習慣)、當事人間的習慣,并且效力依次增強。[3]顯然,一般習慣、特殊習慣可以稱得上是社會習慣的話,但當事人間的習慣是不可能被稱為社會習慣的。比如“租戶甲有每月5日向房東乙支付租金的習慣”就是該租賃合同的特定當事人間的交易習慣,該習慣當然不是社會習慣,但該交易習慣在該合同當事人間卻具有法律效力,起著法的作用,因而屬于習慣法。由此可見,認為只有全社會認可的習慣才可能成為習慣法的觀點,將會夸大國家法與習慣法的差異。
二是認為只有不與國家法相沖突的習慣才是習慣法。一般說來,這種觀點沒有問題,但同樣也不能絕對化。[4]比如在云南省某傣族地區,一個傣族男子與一個傣族女孩談戀愛,其間雙方自愿發生了性關系。此時,該男子17歲,女孩未滿14周歲。同時,該地區有早婚的習慣。若依據我國《刑法》規定,該行為屬于強奸幼女,性質極其嚴重,但當地人則習以為常,不認為是犯罪。該案件在實踐中就是依當地習慣處理,未追究刑事責任。[5]毫無疑問,這個案件處理的依據是習慣,而且該習慣是與國家法不一致的。所以此種觀點也是不準確的。此外,實踐中我國一些少數民族中的“賠命價”習慣就更為典型。何謂“賠命價”?它是指在發生命案后,受害方的家屬并不要求追究兇手的刑事責任,而是向致害人及其家屬索要一定的金錢和財物,而一旦滿足了受害家屬的經濟要求,事情便了結,這是在藏族地區廣為流行的一種習俗。在此,這種習慣起著法的作用,同時該習慣又與國家法不同,依國家法,致害人要承擔刑事責任。而現在通行的做法是加害人既要依藏族習慣法承擔“賠命價”的責任,又要依國家制定法的規定承擔刑事責任,被認為是“雙重司法”。[6]這些現象足以說明此種觀點的不準確。其實,在法律實務中如何正確理解、運用與國家法沖突的習慣正是習慣法研究中最為主要且重要的課題之一。當然不能認為在習慣法與國家法相沖突時應當優先適用習慣法,同樣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此時習慣法因與國家法沖突而無效,否則就無法理解多元法律文化,無法有效處理現實生活中的糾紛。
三是認為習慣法是具有權利、義務及責任等內容的習慣性規范。[7](P78)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不夠準確。我們知道,法律規范也可細分為強行性規范、倡導性規范、任意性規范、混合性規范、授權第三人規范、裁判規范以及純粹裁判規范等類型。其中的裁判規范從結構上看是不包含權利義務內容的,而倡導性規范、任意性規范、授權第三人規范等是不包含責任內容的。[8]然而,我們并不因此而否認它們是法律規范,為何對“習慣法”卻要求具有權利、義務及責任等內容呢?后文中用來判斷是否有過失的“傳統節日燃放煙花爆竹”習慣就沒有責任內容,但它事實上已經起了法的作用,屬于習慣法。因此那種試圖從內容上來理解習慣法的觀點也不準確。
二、“習慣法”的內涵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習慣法”是個詞匯。從詞匯學角度看[9],詞有詞義,詞義以概念為基礎,概念與一定的詞義發生聯系。因此,作為一個詞,“習慣法”的詞義與“習慣法”概念緊密相連。法律概念的基本要求是準確、嚴密,因此,從詞匯的角度看,其詞義與概念內容都是同一的,即屬術語詞義。“習慣法”也不例外,作為詞語的“習慣法”的詞義與作為概念的“習慣法”的內容是一致的。這樣,確定“習慣法”概念內涵就可通過考察其詞義,借助語法學來實現。根據語法學的理論[10],“習慣法”這一短語是由“習慣”與“法”兩個詞組成的。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習慣”有兩種含義,除了前文引用的含義外,還有“常常接觸某種新的情況而逐漸適應”的含義。顯然這一含義是作動詞用,作為“習慣法”中的“習慣”只能是名詞。所以“習慣法”是兩個名詞(都是實詞)組成的短語。“習慣法”作為短語可做如下語法分析:“法”是中心語,而“習慣”屬限制語,“習慣”限制“法”。可是這里的“習慣”是如何限制“法”的呢?第一種可能的情形是“習慣法”是關于習慣的法(即調整習慣的法)或源于習慣的法,正如民法是調整民事關系的法、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的法、訴訟法是調整訴訟關系的法。但在法學理論中無人將“習慣法”理解為調整習慣的法,所以“習慣法”不是關于習慣的法 (或調整習慣的法)。第二種可能是“習慣法”是源于習慣的法,正如“國家法”是指源于國家的法、“民間法”是指源于民間的法。顯然,這種理解是符合該詞的本來含義的。因為我們正是在與“國家法”、“民間法”等用語相對應的場合來使用“習慣法”這一概念的。因此,就把“習慣法”認為是源于習慣的法。當然,這樣的理解在法學理論的層面上還顯得寬泛,不夠準確,因為在沒有國家前也有調整社會的規范,這些規范大都是習慣,在國家成立后已經轉化成了國家法。這也是“國家法最先都是習慣法”的原因。所以“習慣法”不再指稱已經被法律化了的習慣,已經被法律化了的“習慣法”就是國家法,而是指在制定法之外的起法的作用的習慣。所以,所謂“習慣法”就是起法的作用的習慣。
三、“習慣法”的外延
(一)國家立法認可的習慣
這是指國家制定法明確規定可以作為處理案件依據的習慣,對此毋庸多言。“習慣經國家機關依法認可具有法律效力后,即成為習慣法。”[11]比如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61條規定,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這樣一來,交易習慣就可以成為處理爭議的依據,就起到了法的作用,成了習慣法。如下實例:1995年9月10日,原告因準備建造大樓需要黃沙,與被告簽訂了購買黃沙的合同。合同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黃沙30車,并規定了每噸的價格 (注意,不是每車的價格)。誰知,在合同簽訂后不久,黃沙開始漲價。此時,被告的負責人李某不愿意按合同履行。并借口貨源緊張,要求變更合同,變更的內容主要是黃沙的數量,但遭到原告的拒絕。李某想了個辦法,在第二天便安排了兩輛130貨車裝運黃沙送到原告處 (該車裝載量為2噸),同時要求以已改車型為標準計算黃沙的數量。原告反對,認為黃沙的數量應該以東風牌大卡車作為計算標準。為此形成訴訟。在審理中,法院認為:在當地運黃沙的車都是東風牌大卡車,在此之前被告給他人運送黃沙也用的是東風牌大卡車。據此判決被告敗訴。在本案中,根據當地的交易習慣,在以“車”作為黃沙的計量單位時,該“車”是指東風牌大卡車。這里“車”是指東風牌大卡車的交易習慣就被用來處理案件,就起著法的作用,是習慣法。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此種習慣法是在我國最早得到公認的習慣法。它與國家制定法一樣,是國家主義視野下的法律。可是現今很多研究習慣法的學者卻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了這種習慣法,以至于他們在對習慣法進行論述時都存在前文分析的問題。
(二)國家司法活動中運用的習慣
這是指法律雖然沒有規定可以作為處理案件依據,但司法機關在處理有關案件時卻運用了的習慣。比如:在膠東某村,村民甲在承包地上辦了一個狐貍養殖場,養殖了130多只狐貍。該養殖場(承包地)離村子不遠。狐貍的配種期、懷孕期一般在每年公歷2月底3月初。在此期間需要安靜的環境,否則狐貍會受到驚嚇,從而導致化胎、流產。2007年3月4日是元宵節。在元宵節這天,當地有燃放煙花爆竹的習慣。村民甲害怕處于發情配種期的狐貍在元宵節這天會受到燃放煙花爆竹的驚嚇,便提前在狐貍養殖場邊放置了“此處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違者罰款”的告示牌。元宵節晚上,果然有村民乙、丙在狐貍養殖場邊燃放煙花爆竹。當晚,養殖場中的狐貍出現大規模騷亂。同年4月,甲發現只有十幾只狐貍正常懷孕,損失慘重。村民甲于是要求村民乙、丙賠償損失。法庭審理過程中,兩被告認為是無稽之談,拒絕出庭。在此案中,依法律的規定,乙、丙是否要承擔責任的關鍵是是否存在過錯。但法律對此情況下如何判斷過錯并未具體規定也不可能做這種具體規定。那么法院如何來判定乙、丙是否存在法律上的過錯呢?法院便依據了習慣,認為“傳統節日燃放煙花爆竹”沒有過錯,因此乙、丙不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12]由此可見“傳統節日燃放煙花爆竹”的習慣在司法中得到了運用,起著法的作用,因此這種習慣是習慣法。
(三)非國家權力機關解決糾紛運用的習慣
這是指處理糾紛的不是國家權力體系中有關機關運用的法律規范,而是由非權力機關來處理糾紛或通過協商等解決糾紛時運用的習慣。由于該習慣被用來處理糾紛,定紛止爭,起到了法的作用,因而屬于習慣法。如下就是適例:西雙版納曼村以及周邊傣族村寨普遍有這么一種習慣:外村寨有人死而未葬前,其他村的村民不準該村寨人進入本村,違者由召曼主持對其處以15元罰款并1只雞、10包糯米飯、2支蠟燭用于祭寨心、寨神。2000年1月20日,曼村一戶村民家的老人早上9:00逝世,村長通過廣播把這件事向全村通報。死者家屬立即四處通知親戚來參加葬禮,死者的孫女婿巖某無證駕駛摩托到距離曼村20公里的勐混通知親戚,由于公路上有交警檢查有關證件,巖某即繞道而行,路經短村時被村民攔住,要對其進行罰款。最終由短村召曼對巖某處以15元罰款并1只雞、10包糯米飯、2支蠟燭的處罰。[13]
四、與類似概念的比較
(一)習慣法與習慣
依上文分析,習慣法是起法的作用的習慣。因此習慣法是習慣的種概念,習慣是習慣法的屬概念。當然不是所有的習慣都是習慣法,只有部分習慣才是習慣法。什么樣的習慣可以成為習慣法呢?首先,可以肯定只有具有涉它(他)性的習慣才有成為習慣法的可能。因此,從習慣的內容是否與他或它有關可將習慣分為:涉它習慣、涉他習慣、不涉它(他)習慣。涉它習慣是指與外在的客觀事物有關的習慣,如攀花折枝的習慣;涉他習慣是指與他人有關的習慣,如雖然規定儲蓄所工作時間至下午五點,但四點半就不辦理新業務的習慣;不涉他(它)習慣是指僅與自己相關,而與外在的客觀事物或其他人無關的習慣,如飯后剔牙的習慣。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由此可見,只有與外在的客觀事物或他人有關聯的事項才可能由法律調整。即只有涉它(他)性的習慣才有成為習慣法的可能,不涉他(它)的習慣無法成為習慣法。比如湖南人吃辣的習慣就不可能成為習慣法,因為一個湖南人是否喜歡吃辣與他(它)無關。其次,從習慣的內容看,只有指向重要事項的習慣才可能成為習慣法。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但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法律都予以調整,法律不是管家婆,法律只調整其中較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因此,習慣要成為“習慣法”,其指向的事項應該是重要事項。不過也要注意,法律對所涉事項重要性的認定與習慣對所涉事項重要性的認識會存在一些不一致。比如就“亂搞男女關系”而言,除非一方已有合法的婚姻關系且該達到了非法同居的程度,否則法律認為這屬不重要的事項,不予關注;但有些地方的習慣卻不同,尤其是一些民風淳樸的農村,卻認為一般的“亂搞男女關系”是重要的事項,如1990年3月訂立的《瓦窯屯村規民約》第七條就規定:“亂搞男女關系的罰雙方四個三十:30斤米、30斤酒、30斤肉、30塊錢,辦給全村人吃。”[14]可見在瓦窯屯,“亂搞男女關系”就重要的事。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情形,比如前文引用的發生在云南省某傣族地區的男女在戀愛期間發生了性關系的例子就是如此。根據《刑法》規定,此行為屬強奸幼女罪,性質極其嚴重,但當地傣族人們的習慣認為根本談不上是犯罪,屬正常現象。[5](P242-243)其實,這種不同也是所謂習慣法與國家法沖突的重要表現。
(二)習慣法與非國家立法機關或授權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區別
在我國社會生活中,除了國家立法機關或授權立法的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即制定法外,還有大量非立法機關或非授權立法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如不具備立法權的國家機關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各單位的規章制度、各黨派的章程等。它們與國家制定法一樣,是通過一定的程序制定的,但它們的制定主體不是國家立法機關或授權立法的機關,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所以它們不是法。習慣法與它們不同,習慣法不是制定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是被發現并被用來處理糾紛的。
(三)習慣法與民間法
“民間法”一詞在我國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何為民間法,也是眾說紛紜,至今未達一致見解。但二者的區別可從如下幾點看出:一是比照的對象不同。民間法比照的對象是官方法,它強調的是其在創制主體上與官方法的差異,即民間法是民間的創造物,而非國家或者一定的公權力機構的創造物;習慣法比照的對象主要是成文法,它強調的是在生成機制上與成文法的差異,也即是說,習慣法是自生自發的秩序,是社會經驗進化的產物,而非理性建構的秩序,即非依據特定的立法程序創制的結果。[15]民間法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二是地域性特點表現不同。民間法強調地域限定性,[5](P38-40)民間法往往出自特定的社會區域的人類群體和組織,只對該地區的全體成員有效,作用范圍非常有限,有的僅適用于一個村鎮;而習慣并不強調地域特點,雖然特殊習慣中包含某個地域適用的習慣,但由于習慣還包括一般習慣、當事人間習慣,而這兩者并不強調地域性,甚至它們可能根本就沒有地域性。三是表現形式不同。民間法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但習慣法只能是不成文的。從上述區別可以看出,民間法與習慣法存在交叉關系,有些屬民間法也屬習慣法,如村落習慣法;有些屬民間法不是習慣法,如村規民約屬民間法,但不是習慣法;有些屬習慣法不是民間法,如當事人間的交易習慣屬習慣法,但不是民間法。所以,那種認為“習慣法是民間法的一部分”[15](P21)]的觀點就是不正確的。
總之,習慣法就是起法的作用的習慣。任何其他的定義可能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無法準確揭示習慣法的內涵和外延,無法與類似概念相區分。
[1]李貴連.中國近現代法學的百年歷程(1840—1949年)[A].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法學卷)[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2]張洪濤.使法治運轉起來——大歷史視野中習慣的制度命運研究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4]李可.習慣法——一個正在發生的制度性事實[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5.
[5]于語和.民間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6]杜宇.重拾一種被放逐的知識傳統——法視域中“習慣法”的初步考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7]厲盡國.法治視野中的習慣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8]王軼.論物權法的規范配置[J].中國法學,2007,(6).
[9]戚雨村.語言學引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
[10]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1]沈宗靈.法理學(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2]王新生.習慣性規范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13]王啟梁.宗教作為社會控制與村落秩序及法律運作的關聯[A].謝暉,陳金釗.民間法(第8卷)[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14]高其才.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15]田成有.鄉土社會中的民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