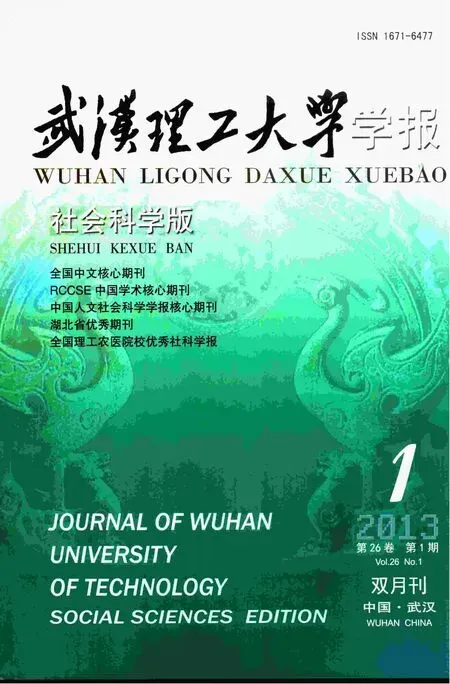米蘭·昆德拉與卡爾維諾小說觀念異同論
黃世權
(廣西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西 南寧530001)
米蘭·昆德拉與卡爾維諾是當代世界上最富獨創性的小說家,他們以其豐富的創作維持了西方小說在20世紀后期高質量的發展,同時他們還引導了小說的敘事方式和結構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更難能可貴的是,與前代大師們相比,他們還展示了許多小說大家所不具備的理論反思能力,憑借其獨到的創作經驗和深入的理論探索,面向未來進行思考,引領了小說在21世紀的發展。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①就是矗立在他們豐富作品中的路標。這兩部出自天才小說家之手的文學反思之作,自然不同凡響,具有一般理論家所不具備的直覺性和生動性。由于建立在小說家對當代社會現狀和文學現狀的敏銳觀察和反思的基礎之上,這兩部著作篇幅不大,不無輕盈感的經驗之談,不僅解釋了各自創作的思想和文學觀念,也揭示了當代小說固有的困境和出路。從總體趨勢上,其顯示了小說創作與觀念在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轉移路途中的一些重要標志。
一、輕盈、復調、百科全書
卡爾維諾和昆德拉最主要的相同觀點首先是:輕盈、復調、百科全書小說。這幾個概念成為他們對現代小說的集中評價,更顯示了他們對未來小說發展模式的向往。如果說“復調”和“百科全書”是對現代主義那些代表作品的準備評價,那么“輕盈”則是兩人對各自小說風格的宣言,也是他們對后現代小說發展的明確指示。“輕盈”在卡爾維諾的《文學備忘錄》中第一個作為范疇提出來,顯示了卡爾維諾對這個概念的重視。經過卡爾維諾的推廣,“輕盈”幾乎成為當今后現代小說的綱領和宣言,引導著當今小說或其它藝術的發展走向,也成為理解現代尤其是后現代主義小說甚至整個當代藝術的關鍵術語。從小說發展的內在規律上看,“輕盈”顯示了現代小說對傳統現實主義小說沉重甚至沉悶風格的擺脫:把小說從反映社會現實的重負中解放出來,恢復小說自由想象和恣意游戲的本性。其實昆德拉、卡爾維諾等人的示范性創作所帶來的使人解放的影響,成功實現了當代小說創作由重到輕的戰略轉移。
卡爾維諾對輕盈的喜愛是建立在對文學深入的理解之上的。他回憶自己剛開始創作時滿腦子也是現實主義的想法,并試圖將外部現實與內心的幻想結合起來,但很快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于是他開始放棄現實社會的重量,轉而用輕妙的手法去撲捉內心閃爍的秘密和奇妙的幻想。他一開始就界定了他對輕的理解:“我的工作常常是為了減輕分量,有時盡力減輕人物的分量,有時盡力減輕天體的分量,有時盡力減輕城市的分量,首先是減輕小說結構與語言的分量。”[1]2
卡爾維諾當然并不是簡單地沉迷于輕,實際上他一開頭就表達了一個辯證的思想:“我支持輕,并不是說我忽視重。”[1]2因此毫不奇怪,他區分出兩種輕:莊重的輕與輕佻的輕。他注意到歐洲文化中輕的普遍存在和意義,從古希臘神話,奧維德的《變形記》,盧克萊修的哲學,到現代科學如電腦軟件,并對意大利的古典詩人卡瓦爾坎蒂和但丁的作者的輕盈意象作為精彩分析,最后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得到啟發。他總結了文學中輕的三個含義:一是減輕詞語的分量,就是使意義附著在沒有重量的詞語上時,變得像詞語那樣輕微;二是敘述這樣一種思維或心理過程,其中包含著細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或者其中的描寫高度抽象;三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輕的視覺形象[2]17-18。
卡爾維諾的“輕”兼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意義,減輕詞語的分量說到底是減輕詞語與現實的聯系,從而使意義也跟著輕盈。這里透露出來的語言與意義的關系,看得出卡爾維諾對如索緒爾語言學以及解構主義等的語言觀念是很熟悉的。敘述中的高度抽象,以及突出輕的視覺形象,則更側重于藝術形式的輕盈化。這里表露了卡爾維諾的文學本質觀,稍后他有明白的表述:“文學是一種生存功能,是尋求輕松,是對生活重負的一種反作用力。”[2]29由于重視小說對現實重負的擺脫,對輕松心境的尋求,卡爾維諾異常重視幻想的價值,他對民間文學如意大利童話的喜好,就是看中其中的幻想成分。在第四講里他充滿熱情地強調幻想的作用:“幻想是一部電子計算機,它儲存了各種可能的組合,能夠選出最恰當的組合,或者選出最有意思的、最令人高興、最令人快樂的組合。”[2]89他認為藝術家的幻想是個潛力極大的世界,任何作品都不能把它全部體現出來,他甚至設想要進行一種幻想教育。這種思想當然是與“輕”一致的,就是要改變傳統認知范式和文化慣例分配給文學的認識功能,尤其要擺脫現實主義傳統對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過度強調,恢復文學固有的輕盈和幻想的本色,從而引領讀者進入幻想的美妙世界,體味自由想象的魅力。這種反撥是對文學的返本歸元的思考,是對19世紀歐洲文學發展的一種糾偏。對文學在現代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創作實踐和理論反思中對文學的幻想本色的維護和發揚,是卡爾維諾對現代文學的突出推進。
昆德拉對于輕的鐘愛與卡爾維諾是一致的。不過有他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表述。他認為現代世界是高度復雜的,人類的生存境遇也是復雜的,因此小說應該把簡練視為藝術的關鍵,這就要求堅定地直達事物的核心。這種簡練手法極大地減輕了結構的重量。這就是昆德拉對輕的理解。他有一段話簡潔地概括了自己對輕與重的辯證理解:
把問題的極端重要和形式的極端輕靈集合在一起——這一直是我的野心。而這不僅僅是藝術的野心,輕松的形式和嚴肅的主題的結合,顯示出我們的夢是何等可怕的無意義——不管那是床上做的夢,還是在歷史大舞臺上演完的夢[3]98。
對于昆德拉而言,除了小說形式的輕靈,對小說游戲成分的呼吁也可以歸結為文學的輕,一種自由嬉戲的輕逸精神。昆德拉認為,現代小說至少有四個呼吁值得認真對待,其中,擺在首位的就是游戲。這種游戲是18世紀小說中頻頻出現的,并構成勞倫斯·斯特恩和狄德羅各自名著《項狄傳》與《宿命論者雅克》中生動展現的小說奇景。進入19世紀,西方小說拘守心理逼真和反映現實的法則,放棄了小說輕快游戲的傳統,小說變得沉重。昆德拉為之遺憾不已。這大概也是昆德拉不太推崇19世紀俄國小說的原因吧,的確那些現實主義的長篇大作幾乎都比較沉重,缺乏游戲精神。昆德拉欣賞卡夫卡就在于卡夫卡小說用幻想喚醒了19世紀的睡眠式想象,真正實現了夢想與現實的融合。昆德拉熱情贊揚卡夫卡的偉大貢獻,不僅在于實現了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步驟,更在于打開了一幅新的景象,讓想象像在夢中爆發,自由地突破看似不可逃脫的逼真的律令。顯然幻想是使文學變得輕靈的基本方法。
在昆德拉那里,還有一種內容上的“輕”,這種“輕”實際上不是輕,而是一種獨特的重,這就是在《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輕》以及其它作品中也出現的輕,這種輕,用昆德拉的語言來說是“虛弱”,面對強敵強權時的疲乏無力。再進一步說,這種輕,我們可以緊扣昆德拉的語言來說,就是對于存在的遺忘。因為遺忘而飄浮無據,而輕飄無力。這正是現代人類尤其是極權主義歷史情境下人們的普遍的可悲的生存境遇。昆德拉用這種吊詭奇譎的方式凸顯了人類的生存困境,同時也展現了小說的沒有窮盡的可能性。也難怪他是那么自信:“小說的形式幾乎是無限自由的。迄今為止,它在這方面并沒有加以充分利用。它尚未獲得這種自由。它留下了許多有待探索的形式上的可能性。”[3]84
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是卡爾維諾一個重要的小說思想,表面上看,這好像是與輕盈相矛盾的,但實際上這是輕盈小說的一個新的藝術境界的開掘,對現代小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說傳統現實主義的小說要求豐富的社會生活的內容,那么對于現代小說來說,在擺脫了認識社會和反映生活之后,就必須尋求其它方面的突破。正如卡爾維諾強調的,他主張輕并不否認重,這種對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融入小說的追求,實際上就是后現代小說特有的重,它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的現實之重,而是一種新的知識和話語的重。也就是說,后現代小說并不簡單地拋棄重。
《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的第五個范疇“繁復”(內容多樣),實際上指的就是百科全書型的小說。進入卡爾維諾視野的既有現實主義大師福樓拜的《布瓦爾和佩庫歇》,也有現代主義大師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介于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托馬斯·曼的經典之作《魔山》,加上他開頭推舉的本土作家加達和奧地利現代主義作家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卡爾維諾將百科全書式視為20世紀偉大小說的特點,并強調這是現代后現代小說的發展方向。他說:“我們最喜愛的現代作品,都是繁復多樣的解釋方法、思想模式和表達風格的聚合與沖突的產物。即使總體設計是經過精心計劃的,最重要的也依然不是要把作品封閉在一個和諧的形體內,而是由該形體催生的離心力——以語言的多元性來確保真理不只是局部的真理。”[1]116他自己的小說,盡管外形上沒有現代主義大師那種深閎富贍和包羅萬象的規模,而傾向于小篇幅,但是他認為《看不見的城市》和《假如在冬夜,一個旅人》甚至《帕馬洛爾》這幾部具有明顯后現代特色的小說屬于百科全書之作。卡爾維諾自陳《假如在冬夜,一個旅人》包含十部小說。一部篇幅不大的長篇小說中竟能包含十部小說,輕盈的形式容納如此繁復多樣的內容,這說明卡爾維諾開創了一種大容量高密度的獨特小說結構,這得力于他強調的“輕”的第三個含義:敘述的高度抽象。
卡爾維諾更進一步把對百科全書的思考深入到人的生命,為小說與生命的同一性作了十分獨到的論述:“每一個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書,一個圖書館,一座物品儲藏庫,一系列風格,而每一樣東西都可以不斷調換位置并以一種可設想的方式重新編排。”[1]124
昆德拉沒有用百科全書式小說這個概念,他用的是博學這個詞。顯然,兩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昆德拉并不簡單地提倡博學,他甚至反對將各種知識雜糅起來,而是強調要保持主題的統一。他對博學的理解與卡爾維諾對百科全書式小說的闡明更有說明力。實際上廣泛地擁有知識展現知識并不是小說的藝術功能。
昆德拉對博學的理解是與復調結合在一起的。他對復調的理解是,把種種不同的話語形式如哲學、夢想和敘述交響為一,各種話語均衡發展,同時又保持主題的統一。實際上,這里昆德拉把復調與博學式的小說或者說百科全書式的小說統一起來了。昆德拉反對一般意義上的博學,也就是那種將各門學科知識雜糅起來而沒有統一主題,尤其沒有深入探索人類生存境況的小說,他重申布洛赫對博學小說的理解:調動所有理智手段和詩意形式,去闡明那“只能為小說所發現的東西”,即人的存在。對于昆德拉而言,小說運用復調是為了擴展小說的認識功能,更深入地扎進存在之謎,以詩意的形式去觸摸表現存在的奧秘,因此他宣稱:復調小說需要的是詩意,而不是技巧。由于有扎實的音樂修養和對存在之謎的詩意體驗,昆德拉對復調藝術和博學小說的理解都是十分具體的。他的作品的獨特的結構就來自復調的精致運用和博學的實踐。在各種話語交響一片的同時,他還特別提倡并反復使用一種小說性的論述,即在敘述之中插進看似離題實則與主題和諧映襯的哲學議論。這也是昆德拉小說藝術的重要標志。
復調在卡爾維諾那里也是一個重要的標準。第五講《繁復》談論百科全書式的小說,直接提到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我們都知道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也就是復調理論。卡爾維諾對百科全書式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復調,但是他對包羅萬象式、非系統性思維、結構的未完成性的肯定,無疑呼應著巴赫金復調理論的基本內涵。
兩位大師都心儀復調,是不奇怪的。復調對于小說的意義,經巴赫金的闡明已經與小說的現代發展聯系在一起。它將各種異質的話語融合起來,打破意義的單一性和封閉性,創造出一個多義的,平等交流,自由對話,永遠開放,沒有終結的世界。在資本主義控制一切領域的當代社會,復調藝術有助于從內部打開缺口,顛覆資本主義高度簡化的單向度的世界,挽救其它有價值的意義元素。至于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國家地區的極權主義,復調藝術通過異質話語的自由對話,特別是通過昆德拉反復強調的嘲諷藝術的運用,足以撕裂其威嚴冰冷的外表,暴露其內在的丑陋和可笑甚至腐爛和脆弱。卡爾維諾認為小說的可能性是不可窮盡的,偉大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他稱贊博爾赫斯小說的宇宙模式,甚至有些夸張地發出這樣的宣言:書要包含宇宙,并等同于宇宙。顯然只有復調、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因引進各種異質話語而達到這種無所不包的宇宙廣度,并因這些異質話語而進行不斷的激情對話、辯駁,從而使小說永遠沒有完結。
二、高度簡化與語言瘟疫
卡爾維諾和昆德拉盡管對現代小說的發展持樂觀態度,這并不說明他們不清楚現代社會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對小說發展的危害。昆德拉從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存在被遺忘的思考,切入對當代西方小說處境的憂思。他看到在這個存在遭受遺忘的時代,小說還受到其它方面的威脅,小說陷進“一個與它格格不入的世界”。昆德拉把這種普遍的威脅概括為“高度簡化”。由于大眾媒介和政治的聯手,促使這種簡化成為時代普遍的特征,昆德拉不無嘲諷地稱其為時代精神。小說精神與這種時代精神格格不入,挑戰這種時代精神,不與時代精神妥協正是小說的使命。在這里,昆德拉主要的批判對象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和橫行一時的蘇聯東歐的極權主義。對于生活在捷克的昆德拉的個人經驗來說,主要的是來自對極權主義的極度厭惡。他有一段充滿了義憤的話,實際上是對小說反抗極權主義最強烈的聲明:
作為西方世界的——這個世界植根于人類事物的相對性和多義性——一種模型,小說和極權主義世界是不相容的。它不僅是政治和道德的不相容,而且是本體論的不相容。據此我的意思是:單一真理的世界與小說的相對和多義的世界被鑄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體。極權主義的“真理”拒絕相對性、懷疑和提問,它永遠不會接納被我稱之為“小說精神”的東西[3]14。
強調小說精神,是這本《小說的藝術》最出彩的地方。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醒目的命題:小說必須說出只有小說能說出的東西。這就是面對存在之謎的獨特追問。他認為現代小說起源于塞萬提斯,堂·吉訶德開始了對個人生存境遇的探索,從塞萬提斯到卡夫卡,構成了歐洲小說的一個圓圈,在曠野上尋找自我的堂·吉訶德最后退化為在城堡外徘徊的K。昆德拉這樣突出現代歐洲小說對存在之謎的執著與深入:實際上,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分析的全部偉大的存在主題——考慮到它們曾經被先前所有的歐洲哲學所忽視——都在這四個世紀(歐洲小說再生的四個世紀)的小說中得到了揭露、展示和澄明。以自己的方式,通過自身的邏輯,小說一個接一個地發現了存在的各個方面:經由塞萬提斯和他的同時代人,它深入探索了冒險的天性;經由理查森,它開始審察“內心世界”,揭示情感的隱秘狀態;經由巴爾扎克,它發現了人在歷史中的根基;經由福樓拜,它研究了過去未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領域;經由托爾斯泰,它全神貫注于人類行為和決定中非理性的侵入。它探索時間:普魯斯特處理了難以捉摸的過去,喬伊斯處理了難以捉摸的現在。而通過托馬斯·曼,它又考察了控制我們當下行為的遙遠過去的神話規則,等等,等等[3]3-4。
在昆德拉看來,現代小說的發生與現代歐洲是同步的。統一世界的解體(上帝之死)開始了意義多元和模棱兩可的世界,這個混沌的世界無法給個體提供統一的意義,個體面對世界,被迫進行探索。這就是歐洲現代精神的體現,也是歐洲現代小說的精神所在。
把小說定義為對存在之謎的探索,昆德拉還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思考。他認為,小說就是從自我的角度,運用虛構的自我對個人的生存和存在的種種境遇進行深入的探索,尋找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他接受“小說是關于存在的詩性沉思”這樣的界定,并且很清晰地理清了小說中的個人生存與歷史語境的關系,他接受海德格爾關于人與世界相互融合的觀點,強調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因此小說與歷史世界的關系,并不是對歷史的圖解(這樣的小說當然是很多的),而是把歷史作為一種生存情境來理解和處理,歷史世界實際上成為個人生存境遇的一部分,而不是現實主義傳統中的背景。“歷史境況不是一種背景,一種人類情境賴以展開的舞臺布景,它本身就是一種人類情境,一種生長著的生存情境”[3]40。正因為有這樣的內化,昆德拉向來都是非常凝練地處理具體的歷史事件,并把歷史事件提升為獨特的生存境遇。他甚至認為了解捷克的歷史對理解他的小說并沒有多大的意義②。基于個體生存境遇與歷史事件的存在主義式的融合,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說中探索了多種生存的境遇,他特別提示的是“虛弱”這種情境,個體面對強敵表現的虛弱,經常是以陶醉的姿態出現,他認為有一種“虛弱的醉意”。其實,這種“虛弱的醉意”并不是昆德拉的首次發現,早在卡夫卡的《審判》里就已得到了有力的展示,就是約瑟夫·K被殺時那種主動配合的情境。顯然昆德拉對個體的生存情境的領悟部分來自卡夫卡的作品,他處處盛贊卡夫卡,并且以卡夫卡的創作來總結小說的探索,因為卡夫卡是把現實與夢幻結合的偉大代表,特別是他深入地探索了人類的生存的可能性:
小說考察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存的東西,它是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是人可能成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說家通過發現這種或那種人類的可能性,描繪出存在的圖形。但是再說一遍,存在意味著“在世存在”。這樣,人物和世界雙方都必須作為可能性來理解。在卡夫卡筆下,所有這些都一清二楚,卡夫卡式的世界和任何已知的現實都不相同,它是人類世界的某種極限的和非現實的可能性[3]44-45。
昆德拉對小說與存在、歷史關系的思考展現出哲學的深度。這也是昆德拉博學的體現,更重要的是對小說精神的熱忱捍衛。
初看起來,卡爾維諾對于小說與現實的關系沒有昆德拉那么激憤,但是他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思,他直言不諱地宣稱一場語言瘟疫襲擊了人類,造成語言平淡和意義平庸,這場瘟疫彌漫到社會各個領域,傳染了生活和歷史,使得歷史模糊不清、枯燥乏味,最令人不安的是社會失去了形式。卡爾維諾認為文學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卡爾維諾所說的這場語言瘟疫實際上是現代社會的文化病癥。他沒有過多地描繪這種肆虐人類的瘟疫,也不愿深思瘟疫產生的原因。毫無疑問,這種瘟疫和昆德拉所說的高度簡化是相同的,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結果。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加上媒體對語言和藝術的惡性影響,造成語言無味、意義單一的現象。也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社會”。因此這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面對的一種瘟疫,不單單表現在語言領域,甚至滲透了社會的所有方面。在后現代主義和消費主義社會里,這種瘟疫正在變本加厲。因此,昆德拉和卡爾維諾對現實的尖銳批判也顯示了小說的反抗作用,這與傳統現實主義畢竟也還是相通的,盡管反抗的方式已經大不相同。如果說昆德拉還保持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嘲諷現實的激情,那么卡爾維諾實施的則幾乎是馬爾庫塞、阿多諾等人倡導的形式的反抗,新穎的藝術形式自動疏離沉悶乏味的現實,在幻想的天地里超越現實,反抗現實③。
三、視覺形象及嘲諷
卡爾維諾與昆德拉也還有不同的地方,體現出兩位大家對文學的理解和愛好的差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卡爾維諾對視覺形象的推崇,顯示出卡爾維諾獨特的小說趣味,也透露出小說發展的當代特性。卡爾維諾對視覺形象的喜愛來自以圖畫為主的童年讀物,這些視覺形象多半與幻想有關,因此卡爾維諾又稱其為視覺幻想。視覺幻想有廣泛的來源,對現實生活的直接觀察,生活中的幻影與夢影,文化傳統流傳下來的藝術形象,以及感覺的抽象、提煉內化等等。他認為優秀的作家都具有這種稟賦,尤其生活在視覺幻想特別受重視的時代的作家,如文藝復興、巴洛克和浪漫主義時代。
卡爾維諾對視覺形象的重視,也可以歸結為他對文學的輕的思考,他在界定文學的輕時就說到輕的視覺形象。盡管卡爾維諾并沒有提到當今的主要藝術形式電影,但是他對視覺形象的重視,實際上呼應了電影藝術的追求。不難看出,電影是最擅長構造視覺幻想的藝術形式,比任何其它藝術形式都更能生動地把視覺幻想呈現在讀者面前。卡爾維諾生活的時代已經是電影技術和藝術都高度完美的時代。這也是電影藝術對卡爾維諾的文學思考的影響。
昆德拉似乎沒有卡爾維諾的瀟灑,他對小說與電影的關系沒有論述,他的小說也沒有特別明顯的視覺效果的追求。相反,他執著不忘的是小說的精神本質,也就是嘲諷。他反復強調小說是一門嘲諷的藝術。把小說的本質界定為嘲諷,主要源于昆德拉對極權主義的憎恨,對人類沉湎于物質利益而迷失存在意義的憂思。同時也看得出昆德拉對現實主義傳統的辯證態度,正是對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自覺繼承,昆德拉甚至仿造了“批判的現代主義”一詞。這個術語不僅揭示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精神相通之處,更顯示出昆德拉的創作原則。他的作品幽默詼諧,舉重若輕,對極權主義和人類的愚蠢極盡嘲諷之能事,極富個性地顯示了現代小說的批判威力。怪不得他充滿感慨地說過,除了塞萬提斯的遺產,他一無所有。
四、結 語
由于身處整個西方文化和文學由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轉移的中途,昆德拉和卡爾維諾的創作理念也自然體現了這一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一方面敏銳地洞察到現代社會對小說發展的窒礙(昆德拉說的高度簡化,卡爾維諾說的語言瘟疫),兩人都表達了深刻的憂思,同時又站在西方文學歷史的總體把握的基礎上,清醒地洞悉小說藝術尚有許多沒有窮盡或者沒有充分開發的空間,如游戲、幻想、嘲諷以及百科全書式的話語組合,等等。兩人都從認識論和存在論的哲學層面上,對未來小說的發展寄予希望。當然由于兩人的處境和文學理念的差別,對小說藝術的志趣還是有一些細微的差異。昆德拉對存在之謎,對人的生存處境的執著探索,對小說嘲諷精神的執著,以及對復調藝術的細致理解和靈活使用,構成了20世紀晚期西方小說藝術的獨特景觀。卡爾維諾則對西方的哲學思潮和文學思想具有親切的感受,對小說的語言屬性具有與西方最近的語言哲學相近的看法,他對幻想的重視,對語言能指的游戲功能的理解與運用,對敘述方式和小說文體的持久探索,結出了《如果在寒冬,一個旅人》、《看不見的城市》以及《帕馬洛爾》這些實驗性的小說,充分顯示了自由優美的想象力、文體混用、敘述變革對于小說可能性的開掘。即使是兩人同樣奉持的輕盈,也是同中有異,各具特色。昆德拉輕得尖刻、熱辣,像把向上飛騰的烈火;卡爾維諾輕得從容、優雅,像山間漂浮的云霞。昆德拉輕中含重,卡爾維諾輕中帶純,都開創了現代小說獨有的迥別于傳統經典的藝術勝境。
而反觀當代中國的小說創作,不論在繼承傳統的現實主義對社會現實的深入研究方面,還是對敘事藝術的不斷創新方面,基本上沒有多少足以傳承的經驗。特別是對人類生存情境的獨創性開掘,幾乎已屬遺忘。至于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對于中國當代作家而言甚至連夢也不會夢到。在輕視現實、輕視學識的普遍風氣里,卡爾維諾和昆德拉這種具有高度理論素養的小說家似乎也不會在我們的土壤上出現。昆德拉說小說是西方的藝術,這如同韋伯說理性主義是西方的思維,德里達說哲學是西方的思想一樣,使我們既感到羞辱而又無可奈何。與昆德拉和卡爾維諾這樣的大家相比,中國當代小說有不少差距,但最主要的差距還在于在缺乏自覺的小說意識。
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甚囂塵上的藝術風潮之中,一些作家還在執著于傳統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的寫作方式,一些則對中國豐富的歷史進行現代的想象。在具有鮮明的后現代主義傾向的創作中,比較突出的毛病是簡單的模仿,或者玩弄一點大眾化雷同化的個人幻想。在昆德拉和卡爾維諾的啟示下,我們的當代創作處處是“性”情洋溢和輕浮想象,然而卻沒有兩位大師的神髓,僅得其皮毛而已。其實,即使是后現代主義,即使作為一種小說藝術風潮,也具有極其嚴肅的一面,絕非任意胡來的,且不說昆德拉的小說嬉笑怒罵之中是對人類存在之謎的探索和展示,即使卡爾維諾的輕盈,也是對小說可能性的探索和想象力的優雅拓展。我們閱讀卡爾維諾只覺一片神行,的確是后現代主義小說的能指游戲的范本,卻看不到等而下之的后現代主義小說常見的胡鬧、惡搞、臟亂丑的通病。昆德拉尤其是卡爾維諾的創作與思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完全不同于我們普遍接受和奉為準則的后現代主義,這對于當代中國的小說發展是一面很好的鏡子④。
注釋:
① 本文參考了卡爾維諾此書的兩個中譯本,蕭天佑從意大利語譯出的名為《美國講稿》,五次講演的標題分別是:輕逸、速度、精確、形象鮮明和內容多樣。黃燦然從英文版譯出的名為《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五次講演的標題是:輕、快、精確、形象和繁復。本文綜合了兩個譯本的術語。對兩版的引用,完全是為了行文的需要。
② 盡管昆德拉這樣說,其實即使他把捷克的歷史事件已經如他所云變成了一種生存情境,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環境轉變成海德格爾式的個體存在境域,無疑捷克的歷史仍然還是他的作品賴以產生的外部機緣,因而也是理解其小說的重要途徑。
③ 見馬爾庫塞的著作《審美之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阿多諾的著作《美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④ 如果模仿以前的陳詞濫調,那么也許可以說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后現代主義,美國理論家杰姆遜在《晚期資本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文化邏輯》以及哈維在《后現代狀況》等等著作中對后現代主義的診斷基本上都是看到了后現代主義的消極方面,如藝術上的戲仿、拼貼、無深度等等。其實昆德拉和卡爾維諾用他們的創作和理念向我們開啟了后現代主義的另一維度。當然,這兩位大家的情形還是有些特別。可以說卡爾維諾的小說已經有了十分典型的后現代主義特征,而昆德拉正處于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過渡之中。
[1]伊塔洛·卡爾維諾.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M].黃燦然,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2]伊塔洛·卡爾維諾.美國講稿[M].蕭天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3]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唐曉渡,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