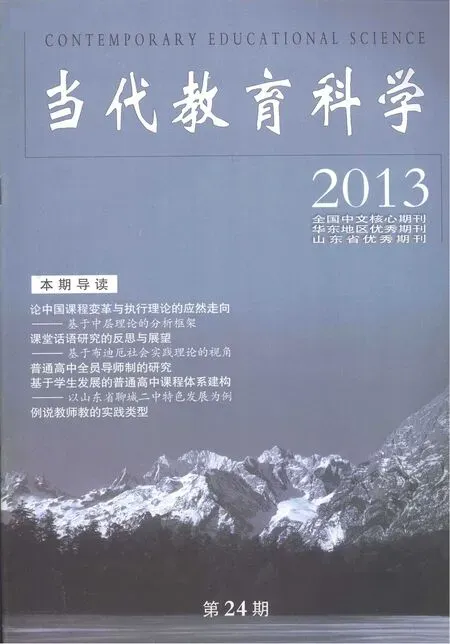課堂話語研究的反思與展望——基于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視角
● 黃 山
師生言語互動是課堂話語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如何通過師生話語揭示師生關系、通過師生關系理解師生話語是課堂話語研究的核心任務之一。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呈現出明顯的關系主義色彩,以此為基礎,布迪厄傾向于從關系的視角來考察語言和話語。因此,布迪厄關于語言與話語的理論探討與課堂話語分析有許多契合之處,也比較適用于分析師生的課堂言語互動,布迪厄獨特的視角也為課堂話語研究帶來了方法論啟示和新的研究視野。
一、課堂話語研究的得與失
幾乎所有的課堂教學活動都是通過師生言語互動來實現的。師生在課堂中的言語互動能夠呈現教學活動的整個過程,尤其在當前課程研究主張“基于證據得出結論”的背景下,師生課堂話語能夠為研究者提供大量真實的經驗證據。并且,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課堂研究中的廣泛應用,使得課堂話語研究成為本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話語分析以日常會話、書面文本等語料為研究對象,“不僅考察語言與教育的相互關系,還關注語言與社會的相互關系,更重視語言和思維的相互關系”[1]。通過話語分析方法,研究者發現了課堂師生言語互動的一般結構。與日常對話不同,課堂對話往往呈現 “教師啟動(initiation)——學生回應 (response)——教師評價(evaluation)”的IRE結構[2]。除了發現這個普遍的結構,研究者也揭示出了上述結構背后隱藏的不平等的師生關系。
雖然課堂話語研究揭示出了課堂師生言語互動的普遍結構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但已有研究對課堂話語權力的運作機制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者往往通過“話語權力”甚至是“話語霸權”來揭示教師對課堂話語的掌控,師生之間不平等的話語權力體現在課堂中不均衡的話輪(speaking turn)分配[3],并認為教師有權力決定何時發起對話、誰來參與對話。因此,課堂話語狀況呈現出以教師話語為主導的特征,從量來看,教師說更多的話。已有針對師生課堂話語權力的研究往往通過“量”來說明教師與學生的權力關系,如有研究者通過計算不同類型教師提問所占全部活動的比例,推斷出專家型教師比新手教師更能熱情、平等地對待學生,有良好的師生互動[4]。通過“量”來分析師生言語互動是課堂話語研究比較典型的研究方法,其中弗蘭德斯(N.A.Flanders)的互動分析編碼系統最早采用這種方法。隨著量化研究的盛行,近年來國內外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的量化課堂話語分析研究以及“以話語為中心”課堂觀察工具。雖然這些工具形式不同,但都遵循了相同的邏輯,即通過記錄不同類型的課堂話語出現的頻率來分析師生言語互動。基于上述邏輯,已有課堂話語研究一致地建議教師把話語權移交給學生。而事實上,為了得到教師積極的評價,學生往往會有意識地迎合教師,而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師生課堂互動存在著“悖論”,即學生越是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不平等的師生關系就越得以維系。
僅僅通過讓學生在課堂中說得更多,而不去分析課堂話語權力運作的深層機制,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師生間不平等的話語關系。并且,“以話語為中心”來獲取經驗證據,忽視了與話語相關的其他因素對理解話語的重要性。因此,課堂話語研究需要借鑒新的視角,對本領域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反思與改進。
二、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對語言與話語的關注
布迪厄的一系列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著作共同建構了他的社會實踐理論。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中,“場域”、“慣習”和“資本”等概念占據核心地位。上述概念賦予了布迪厄獨特的視角,使布迪厄在面對社會問題時能夠提出獨到的見解。因此,國內外有關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已有研究往往重于分析 “場域”、“慣習”和“資本”等核心概念。雖然語言與話語并不是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核心概念,但是由于布迪厄在建構其理論時,對索緒爾 (Saussure)的語言學、列維-斯特勞斯 (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以及阿爾都塞(A1thusser)式的馬克思主義給予了較多的關注[5],并且正值當時的社會學研究正發生著語言學轉向,因此布迪厄仍然保持了對語言與話語的敏感。在分析不同階級、種族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及其得以再生產的機制時,布迪厄常常把語言與話語實踐置于舉足輕重的位置。
(一)布迪厄對語言與話語的理論探討
布迪厄考察了殖民時代或后殖民時代的殖民者在與土著民溝通時所采用的話語策略①;以一個市鎮居民和一個農民之間的對話為證據,揭示了市鎮和鄉村之間的對立②;以文化資本的視角,調查了法國巴黎和外省不同階級大學生的語言資本、選拔程度和語言能力間的關系③。除了上述實證研究以外,布迪厄也對語言與話語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布迪厄主要通過如下兩個視角對語言與話語進行研究:一是以權力的視角,把語言視為一種文化資本:二是以關系的視角,把話語實踐視為關系的建構。
1.權力的視角:語言即資本
布迪厄對語言與話語的理論探討主要始于他對以索緒爾和喬姆斯基(Chomsky)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批判,該流派主要關注語言的內在邏輯(如語法、意義等),因此布迪厄把這種觀點稱為“純粹語言學”。布迪厄認為,“純粹語言學”把語言與話語看作一個自足的系統,“斬斷了與它實際運用之間的任何關聯,也剝奪了語言與話語的實踐功用和政治功用”[6]。
與“純粹語言學”的觀點不同,布迪厄理論體系中的語言與話語帶有明顯的社會語言學特質,他把語言與話語置于產生和流通它的互動情境和結構環境中進行考察。在多種情境和環境中,布迪厄把更多的目光投在了產生和流通語言的權力結構上,以權力的視角重新審視語言。在布迪厄看來,“怎么說”和“說什么”同樣重要,一個人掌握了語言規則就意味著賦予了他一種權力,即進入某一場域,并在場域中獲得某種地位。并且,布迪厄認為這種資本對于所有人來說并不是平等分配的,性別、教育水平、階級出身、居住地點等語言外部的相關因素每時每刻都隱藏在語言背后并發揮作用[7]。語言外部的相關因素影響著人們獲得語言資本的機會,反之,語言資本在社會實踐中的運作也為這些外部因素得以再生產提供了可能。在這個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教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關系的視角:話語即關系
布迪厄明確提出了社會實踐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視角,尤其是在他建構“場域”這一核心概念時,關系的視角體現得尤為明顯。布迪厄認為,關系性是場域一個重要特征場域的關系性具體體現在進入該場域的“游戲者”之間的資本與權力關系。布迪厄常常以“游戲”來隱喻場域,認為“游戲者”所擁有的資本的數量和結構決定了他們參與游戲時所采取的策略。
基于上述理論假設,布迪厄在研究語言與話語問題時主要關注對話雙方的關系是如何影響雙方的話語策略,以及不同話語策略對雙方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因此,布迪厄更加關注人與人之間的言語互動,而非文本分析。布迪厄認為,語言關系是權力關系的另一種形式,“每一次語言表達都是一次權力行為”。對話雙方在言語互動中往往形成不平等的關系(即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不平等的根源則在于對話雙方在相關資本的分配中占據不對稱的位置[8]。雖然對話雙方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在話語理論中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布迪厄對話語背后所隱藏的權力關系的揭示更加徹底。在布迪厄看來,權威不能脫離對權威的認可而孤立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是雙方“合謀”的結果[9]。與大多數話語研究者不同,布迪厄除了考察對話雙方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以外,還關注話語是如何被理解的,話語產生了怎樣的社會效果。因此,在面對話語的支配者放棄支配地位的現象時,布迪厄的理論仍然能夠把這種做法背后的“屈尊策略”識別出來,并認為“這種對權力關系的虛假懸置正是利用這種權力關系產生了對權力關系的認可”[10]——足見布迪厄關系主義視角對話語與權力理解的敏銳性。
(二)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與課堂話語分析的契合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資本”和“慣習”等概念,他的再生產理論也被課程社會學視為批判課程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同時布迪厄對語言與話語保持了足夠的關注和敏感。因此,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與課堂話語分析理論建立起了密切的關聯,兩者之間也存在契合之處。有些話語研究者也把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中的部分概念視為批判話語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論基礎[11]。
如前文所述,話語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在課堂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且在批判話語分析的影響下,課堂話語分析基于“話語具有政治性”的假設揭示了師生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課堂話語研究也帶有了“批判”的意味。除了關注對話雙方的權力關系以外,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與課堂話語分析也共同關注了對話過程中形成的話語結構。話語分析所研究的話語的是作為社會實踐的語用(language use),是在特定場域中使用的語言,話語只有被置于社會背景中才能夠被理解、被分析[12]。而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社會背景通常由“場域”、“慣習”來指代。如前文所述,布迪厄認為場域是一個具有自身邏輯的關系網絡,進入場域的“游戲者”默認場域的邏輯和規則,根據他們擁有資本的數量和結構,“游戲者”采用不同的游戲策略。通過長期的實踐,“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為圖式的形式儲存在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性和它們歷時而不變的特性”[13],進而形成了慣習。基于上述假設,布迪厄認為人們在語言的選擇上也存在某種傾向,而這種傾向在話語研究者看來則是人們對話語的被動選擇。在話語實踐中,人們對話語的被動選擇往往體現在交流過程中形成的相對固定的話語結構,而話語結構恰恰反映了特定場域的權力關系。如話語分析在課堂話語研究中的發現:卡茲頓(Courtney B.Cazden)、梅漢(Mehan)等人共同發現,課堂師生對話往往遵循“教師提問——學生做答——教師給予評價性的反饋”這樣的結構。這種話語結構背后則反映了長久以來支配教育場域的邏輯,即教師對知識的優先占有使得教師有權力評估學生的表達。
三、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對課堂話語研究的啟示
話語分析方法在課堂話語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通過該方法,研究者們揭示了課堂話語的結構,并以話語與權力的視角考察了不平等的師生關系。雖然話語分析方法,尤其是批判話語分析,已經對課堂話語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對語言與話語的關注及其獨特的視角仍然能夠為課堂話語研究帶來理論和方法上的啟示。布迪厄的關系主義視角以及場域和語言慣習等理論為課堂話語研究提出了兩個以往研究所忽視的問題,即學生對教師話語的體驗和課堂話語研究的人類學取向。
(一)學生對教師話語的體驗
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對語言與話語的關注以及批判話語分析的興起,都建立在對“純粹語言學”的批判的基礎上。因此,布迪厄和其他批判話語分析者一樣,在研究話語時更加關注與話語相關的社會因素。其中,“權力”、“權威”和“霸權”等概念的提出為話語研究提供了獨特的研究視角,也為課堂研究通過師生話語討論師生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已有的課堂話語研究大多把研究重點放在教師權威的確立和話語霸權的行使等問題上,并發現在課堂中師生的話語權往往是不對等的,教師主宰著課堂話語,有權力決定何時開始或結束對話、誰來參與對話以及誰的答案是“合法的”。甚至有時教師寧愿放棄知識的線索,也要維持課堂話語秩序[14]。基于已有課堂話語研究的結論,國外的課堂變革和我國的新課程改革都強調把課堂話語權移交給學生,讓學生擁有更多的表達機會。然而,上述做法在布迪厄看來只是教師的 “屈尊策略”,表面上維護了學生的話語權,而事實上教師權威行使則變得更加合法。與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不同,課堂對話是涉及“學生知道了什么”的檢測,為了得到教師的積極評價,學生往往會有意識地迎合教師,或者受到教師的誘導。也有研究者基于經驗證據驗證了上述問題:為了提供學生更多的表達機會,有的教師在提問時會采用開放式問題。在其他語境下,開放問題會得到更多的答案,而課堂上則并非如此——教師的提問更多是去獲取事實信息而不是推理的過程,并且學生會通過教師的提問話語推斷可能的正確答案[15]。
上述證據表明,單純地從教師話語霸權的視角來改變師生課堂話語現狀很難有效地揭示與干預不平等的師生話語關系。而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關系主義視角能夠為解決上述問題打開新的思路。如前文所述,在布迪厄看來,權威是不能脫離對權威的認可而孤立存在的,教師的話語權威得以行使離不開學生對教師權威的默許,事實上學生是不平等話語關系的“合謀者”——學生迎合教師的意愿來回答生動地反映了學生默許與教師權威之間的“合謀”。以往的課堂話語研究往往單純地討論教師權威的行使,很少去解釋學生認可教師權威的機制,而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為課堂話語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學生是如何體驗教師話語的。改變教師課堂話語策略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變革,而澄清學生對教師話語的體驗能夠幫助研究者更深刻而徹底地揭示師生不平等的話語關系背后所隱藏的機制,進而更有效地改變課堂話語狀況。
(二)課堂話語研究的人類學取向
基于證據得出結論已經成為課堂研究的主要取向,尤其是課堂話語研究,這類研究通過課堂師生或生生的對話語料作為經驗證據來開展研究。課堂話語研究有明顯的證據意識,獲得何種語料以及如何獲得語料是課堂話語研究在研究設計時面臨的核心問題。雖然上述兩個問題表面上看是一種獲取經驗證據的技術,但問題背后則反映了深刻的理論問題,即如何看待語言與話語。已有的課堂話語研究揭示出了一般性的課堂話語結構,并探討了結構背后所反映的不平等的師生關系。雖然已有研究在分析課堂話語時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話語外部的社會因素,但獲取證據仍然以話語為中心,已經開發并得到應用的課堂話語調查工具也主要用于記錄師生課堂話語并對其進行分類。例如,最為典型的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的編碼系統僅僅回答了如何記錄互動話語以及如何對師生話語進行分類,因此弗蘭德斯的編碼系統也遭到了其他課堂話語研究者的批判,“弗蘭德斯的互動分析僅僅關注了顯性的、可觀察的行為,不考慮這些行為背后的意圖;互動分析把焦點至于活動與行為的微觀要素,而不是整體的概念”[16]。除了弗蘭德斯的編碼系統以外,其他以話語為中心的課堂觀察工具也存在上述問題。因此,已有課堂話語研究在分析師生話語時仍囿于把“聽得見的話語”作為研究對象,忽視了話語之外的其他因素。
受其早期開展的人類學研究的影響,布迪厄的社會學研究也呈現出鮮明的人類學取向。因此,布迪厄與目前大多課堂話語研究者不同,他在進行話語研究時并不局限于話語本身,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獲取話語之外的其他因素。布迪厄認為,“如果不把語言實踐放在各種實踐共存的完整世界中,就不可能充分理解語言本身”[17]。因此,與以往課堂研究所采用的話語分析方法不同,布迪厄更傾向于通過人類學方法進行場域分析,并且關注不同群體長期形成的語言慣習。話語實踐蘊含在其他社會實踐中,反之其他社會實踐也為理解話語實踐提供了依據。因此,布迪厄人類學取向的話語理論與實證研究對課堂話語研究從“分析話語”轉向“理解話語”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注釋:
①參見[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86-198.
②參見[法]皮埃爾·布迪厄.單身者舞會[M].姜志輝.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66-86.
③參見[法]P.布爾迪約、J.-C.帕斯隆.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M].邢克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84-101.
[1]張發祥,康立新,趙文超.話語分析:理論與案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
[2][14][美]卡茲頓.教師言談:教與學的語言[M].蔡敏玲,彭海燕.臺北:心理出版社,1998.49.79.
[3][15]Nicola Woods.Describing Discourse: A Practical Guide to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68,176-177.
[4]陳羚.專家與非專家教師課堂教學差異之比較——課堂教學的話語分析[J].現代中小學教育,2007,(1):27-29.
[5][6][7][8][10][17][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7-8.188.147.136.190.197.
[9][法]P.布爾迪約,J.-C.帕斯隆.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M].邢克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30.
[11][12]Marianne Jorgensen,Louise J.Phillips.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72,66.
[13][法]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M].蔣梓驊.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76.
[16][日]佐藤學.課程與教師[M].鐘啟泉.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339-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