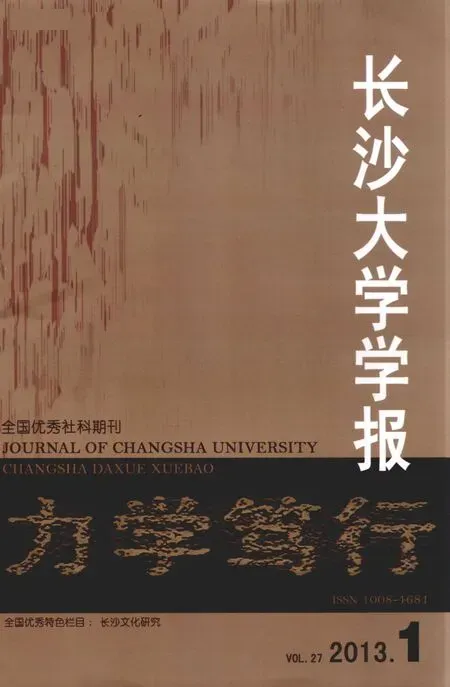基于傳播游戲理論視域下我國傳媒娛樂化研究
單文盛,胡 旋
(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一 我國傳媒娛樂化緣起和現狀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前英國王妃戴安娜之死、辛普森殺妻審訊案以及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緋聞案成為西方新聞娛樂化的三大標志。西方媒介出現“新聞的好萊塢”現象后,國內傳媒緊跟其步伐,最早的便是1981年1月1日《中國青年報》首創的星期刊,星期刊的內容以文化生活為主,包括藝術、文學、地理、生活、歷史、衛生和體育等方面的軟知識。其首次將“軟手法”引入“硬新聞”中,開始了新聞的娛樂化。所謂新聞娛樂化,從內容上來看,就是偏向軟新聞——即西方媒介所謂“大眾新聞”——或盡力使硬新聞軟化。在內容上多以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和帶有刺激性、煽情性的暴力事件、犯罪新聞、災害事件以及花邊新聞和體育新聞為主,減少嚴肅新聞的版面和時間,而形式上則大多采用故事性、情節性較強,帶有戲劇懸念和煽情性效果的表達方式[1]。
自此之后,國內其他媒體開始紛紛效仿,刊登或是播放各種帶有明顯娛樂性質的內容或電視節目。在報刊界,周末報紙、晚報以及都市報的相繼出現,逐漸將報界帶上了市民化、平民化道路;而廣播界也出現了以經濟臺為主導,文藝臺、交通臺等各種專業臺先后涌現的局面;有線電視、無線電視以及衛生電視和教育臺也逐漸興起,至此,娛樂之風刮遍了整個傳媒界。
娛樂作為人類共有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具有一種普遍性接受的社會效果,其能跨越種族、地域、文化和心理的差異而被樂于接受。在眾多因素的一并影響下,我國傳媒娛樂化之路越走越遠,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這乘囂而上的娛樂化濃煙背后,受眾在其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又是怎么推動娛樂化進程的?傳播游戲理論為此提供了不同的理論視角。
二 傳播游戲理論與娛樂
西方游戲論最早可以追溯至康德的藝術游戲論,至此之后游戲概念進入學術研究視野,經過眾多學者的繼承和發展,游戲論最終被英國學者威廉·史蒂芬森引入傳播學領域,將傳播與游戲概念進行了開創性的結合。這不僅拓寬了主流傳播學理論研究視域的邊界,也給新聞傳播界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
(一)傳播游戲理論與娛樂化的關系
對傳播游戲理論與娛樂化的關系進行闡述,首先必須對游戲和娛樂概念進行界定。關于游戲概念,柏拉圖曾說過游戲是一切幼子(動物的和人的)生活和能力跳躍需要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模擬活動。亞里士多德也對其做過界定,他認為“游戲是勞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本身不帶有任何目的性的一種行為活動”。我國辭海對其所做的解釋是“以直接獲得快感為主要目的,且必須有主體參與互動的活動”。而娛樂的定義就相對簡單,被看作是一種通過表現喜怒哀樂,或自己和他人的技巧而予受者以喜悅,并帶有一定啟發性的活動。很顯然,這種定義是廣泛的,它包含了悲喜劇、比賽、游戲、音樂舞蹈表演和欣賞等等。
可見,游戲與娛樂之間存在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游戲只是娛樂的形式之一。而傳播游戲論中的游戲并不是指具體意義上的游戲,只是以游戲過程中的愉悅心理作為評判標準,而娛樂過程則同樣帶有喜悅心理。因此,借助傳播游戲理論對我國傳媒娛樂化現象進行闡釋是再合適不過了。
(二)大眾文化與娛樂功能
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勃興以及傳媒體制改革將中國推向精英文化的邊緣,大眾文化應運而生。中國傳統文化以精英文化為主導,要求傳媒必須承擔守望社會的責任,具體而言便是傳遞信息,發揮正確積極的導向作用。但大眾文化的興起正蠶食鯨吞著精英文化的碩果,將其逼到不起眼的角落,使其被逐漸遺忘。
大眾文化以其感受性、愉悅性、消費性、商品性為主要特征,體現出強烈的娛樂和商業意識,不追求精神的崇高和思想的深刻。現代傳媒的娛樂性在大眾文化中孕育,大眾文化所表征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特征要求傳媒以娛樂的姿態重新展示在大眾面前,而史蒂芬森正好將傳播一分為二,其認為大部分的傳播所承擔的仍舊是信息傳遞功能,但存在著一小部分傳播是為娛樂而生。其提出的傳播游戲理論正是當下傳媒娛樂化的最好闡釋。傳播游戲理論產生在精英文化時代下的信息傳遞功能說時期,卻在大眾文化盛行之時顯示了其存在的理論價值,無意間預示了幾十年后當下的傳媒現狀:娛樂當道,娛樂至上。如今,為娛樂而生的傳播幾乎占據了整個傳媒界的半壁江山,當下傳媒在傳播過程中帶有明顯的游戲成分,以取悅受眾、獲取利益為主要目的。
三 娛樂化:傳媒的游戲
史蒂芬森在其《大眾傳播的游戲理論》(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書中明確詳細地對傳播游戲理論進行了闡釋和介紹,概括地說其整個理論思想就是:傳播即游戲,受眾自主、自愿參與其中并獲得快樂。其中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包括自主性、愉悅性以及趨同性選擇。
(一)娛樂天性
西方學者早在18世紀就對人的游戲本性進行了深入探討,康德認為游戲是人內在目的。席勒也曾說過“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赫伊津哈甚至想恢復人的另一個先驗的本質——游戲者。可見,游戲性很早就被認為是人的天性。傳播游戲理論認為傳播即游戲,受眾則為游戲者。
經過社會和經濟轉型的改革浪潮之后,那些曾經作為媒介受眾的人們就是在這樣變幻莫測的時代風云中,幾乎毫無準備地變成了另一種身份——信息消費者[2]。初看之下,這兩者似乎只是概念上的不同,但實質上,這兩個不同概念背后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傳播理念、喜好和選擇以及審美情趣。在這個資本具有個性和獨立性,而活動著的人卻喪失個性和獨立性的年代,受眾淪落為媒介獲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被媒介大肆利用的正是大眾無限泛濫的娛樂本性。
受眾轉變為消費者并不偶然,是當今媒介環境變化所結的果。在傳媒界開始放棄一直堅守的傳媒責任和操守,轉身為利益服務時,不得不放下身段,俯首稱臣于受眾的娛樂本性,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取悅受眾才能生存”。當下注意力變成一種稀缺資源,媒介在傳播過程中,為了獲取日益稀少和碎片化的注意力,并將其出賣給廣告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不得不利用能最大限度吸引受眾注意力的娛樂本性,不斷地消化一切難于消化的原材料,吐出可供即時消費的噱頭或快餐,猖狂地刺激著受眾的感官。名著被閹割,歷史被戲說,經典被肢解,人民崇拜了幾百上千年的偶像在笑聲中坍塌……幾千年的文明與現代文化的精髓,一登上媒體,就都成了“娛樂”的腳本與商業利益的道具[3]。以本能的滿足來追求淺薄的快樂,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使個體開始進入新的異化過程。
(二)娛樂和愉悅
受眾的娛樂本性之所以能被放大,是因為娛樂能從心理和生理上舒緩壓力,帶來愉悅。史蒂芬森認為,大眾傳播最好的一點是允許人們自由地沉浸于主動地游戲之中。正如人的慣性一般,一旦認定和習慣某種事物便會不受控制地主動實施或參與,當受眾從媒介所傳播的娛樂性內容中獲得輕松和紓解,身體本能地開始喜歡甚至依賴于這種愉悅感,便會一發不可收拾地主動沉浸在傳媒為受眾量身定制的娛樂蜜罐中,不可自拔。在傳播游戲理論中,傳播只是人們娛樂形式之一,傳播游戲不同于現實工作,游戲是愉快的、自由的、非現實的,而工作卻是痛苦的、被迫的、為獲取現實報酬的。受眾迷失于電視播放的搞笑娛樂節目,暫且不論這種迷失對受眾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可在這種盲目中受眾至少是快樂的,享受著旁人也許不理解的愉悅,不是被迫強制,不需獲得現實利益。就是這種參與過程中的自主性和愉悅性使得傳媒界有了投放娛樂煙霧彈的理由和借口,冠冕堂皇地打著“受眾中心論”的旗幟招搖過市,將娛樂化當作是“解救受眾于水深火熱中”的神圣職責。
(三)趨同化的娛樂選擇
傳播游戲理論強調人們可以自由地參與傳播游戲,這并沒有否定社會控制的存在,民意會推動人們被迫去做某事,正如同李普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一般。但傳播游戲只是種趨同的選擇,即使表面上人們的行為整齊劃一,但這是在經過多種可能的選擇之后所呈現出的景象。在國內大部分媒介都走上娛樂化道路之后,媒介為受眾呈現的是一場轟動、炫目的視覺盛宴。在無數次轉換遙控器之后發現,受眾所能選擇的除了娛樂別無他物,無數娛樂大炮同時炮轟著受眾的神經,媒介輕松的將受眾的注意力收入囊中,社會呈現一幅“人人都娛樂,人人需要娛樂”的“美好”畫面。
可見,不管是受眾的娛樂天性還是受眾迫于現實壓力和環境所做的娛樂選擇都在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傳媒娛樂化進程。因此,即使真正促使傳媒走上娛樂化道路的并不是受眾,但實際促進和推動傳媒娛樂化發展的絕對少不了他們。
四 正確把握傳媒娛樂的度
批判學派對傳播游戲理論的批評切中肯綮,該學派認為,在傳播游戲中受眾固然能夠自由幻想,但是大眾傳播的娛樂也具有操縱和控制[4]。早在上世紀50年代,社會學家賴特就曾將娛樂功能并列到拉斯韋爾的大眾傳播的三大功能中,構成經典的大眾傳播四功能說,而且明確指出,娛樂功能是大眾媒介傳播功能中最為顯露的一種功能[5]。的確,改革開放后中國媒介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正視、還原了媒體的娛樂功能,但經過媒介自身不斷地放大和異化之后導致了“泛娛樂化”現象。如何才能將我國傳媒拉回至正確的發展道路上,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軟”“硬”兼施
處于變革時代的中國,社會“異質”化程度上升,多元性的利益群體產生,社會群體分化和多元的趨勢已相當明顯;社會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受眾層次區分大。這種利益和層次的分化必然導致信息需求的分化和多樣[6]。在娛樂本性的驅使下,受眾渴望娛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壓力下,受眾需要娛樂;媒介的“泛娛樂化”使受眾只能選擇娛樂,娛樂無處不在。但對于那些能給受眾帶來主流價值文化、傳遞社會信息以及引導正確價值觀的“硬”新聞同樣也是受眾渴望的、需要的。因此,傳媒界應該為受眾同時提供“軟”“硬”兩種不同程度的信息,以達到各取所需,同步發展的目標。當然,這里所提倡的娛樂并不包括庸俗、低俗、媚俗和惡俗這“四俗”,而且必須拒絕“以追求形式華麗、輕松熱鬧、感官沖擊至上為第一要務,以通俗簡單甚至膚淺為價值取向”的節目內容,傳媒的大眾化并不是低俗化,只是另一層次上的平民化[7]。這不僅需要媒介提高自身素養,而且需要外界加強監督。
(二)“軟”“硬”分流
市場經濟的內在精神要求以及傳媒自身主要功能的職責所在必然要求傳媒娛樂化讓位于真實、公正、客觀、權威和及時的硬性信息。雖然完全遏止傳媒娛樂化并不現實,但是必須做到以“硬”為主流、“軟”為支流的形式進行媒介傳播。在絕大部分主要媒介機構(如鳳凰資訊、南方周末)提供“硬”信息的前提下,允許其他一小部分媒介提供一定的“軟”信息,并且還要克服“硬”信息在報道上的空泛性弊端,在不扭曲和異化信息事實的原則上盡可能地多層次、多角度進行報道,貼近受眾生活。而媒介娛樂節目的生產必須將“追求創新為動力,以平民路線為靈魂,以滿足公眾的需要為先導,同時汲取大眾文化的優質營養”作為目標[8]。
與此同時,媒介從業人員和受眾也應采取相應措施,避免過于沉溺在娛樂的盛世狂歡中。媒介從業人員應不斷提升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加強自律和他律,聚合媒體人的力量將我國傳媒拉至正確的發展道路。而對于推動我國傳媒娛樂化發展的受眾,既然不能阻止其天性對于娛樂的需求,就只能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涵養,消除“金錢至上”和“享樂主義”的不良風氣,抵制低俗化信息的侵入,守住人性和價值這一塊凈土。
[1]黃和節,陳榮美.新聞娛樂化:形式與功能的錯位——對當前新聞娛樂化現象的新探索[J].當代傳播,2002,(5).
[2]鄭根成.傳媒娛樂化的倫理反思[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2).
[3]李良榮,張春華.診斷中國傳媒娛樂化[J].新聞界,2007,(6).
[4]劉海龍.傳播游戲理論再思考[J].新聞學論集,2008,(20).
[5]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6]林暉.市場經濟與新聞娛樂化[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3).
[7]劉艷娥,冉華,徐振祥.試論中國電視娛樂現象發展的基本趨勢[J].云夢學刊,2011,(1).
[8]李良榮,趙智敏.當前媒介娛樂的價值取向——從《亮劍》、《大長今》的火爆及《第一次心動》的叫停分析[J].新聞界,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