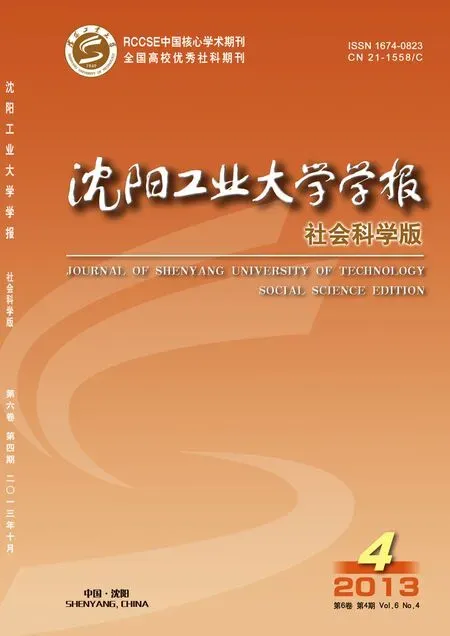論環境權與人權的關系及其實現*
江麗丹
(福州大學 法學院, 福州 350108)
現今,人類面臨著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對生態的關心引起了人類是否擁有保護環境被使用的權利的問題,即環境權問題。為此,必須考慮以下一系列問題:在法律系統與法學話語中是否已存在環境權?現存的法律文件在多大范圍內確認了環境權?如果沒有,那現有的人權是否足以充分地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如果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是否需要創設一個叫作“環境權”的東西,并且將這種權利作為人權體系的一部分,以實現保護環境、保障人權的雙重目標?
一、目前是否存在“環境權”
目前,環境權不受任何全球性人權公約的保護[1]474-481。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中沒有明確提及環境權,只是在其28條規定:“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和國際秩序以充分實現本宣言中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而這種“秩序”被認為包括了環境。布倫特蘭報告強調,無論是在傳統意義上還是在資源不足供應的影響方面,環境壓力作為使社會動蕩、威脅安全的催化劑,被認為構成威脅國際秩序的關鍵因素。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也沒有規定明確的環境權。其他國際人權文書中提及一些關于環境的問題,但僅是個別問題。例如,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中將環境與衛生相關聯,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從預防疾病和營養不良方面來討論環境。
在國際宣言方面,1972年《斯德哥爾摩宣言》通常被視為現代環境法的發端。該宣言明確了一個觀點——人類享有有關環境的權利。該宣言第1條原則中規定:“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環境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承擔一項為現在和未來的人們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神圣義務。”[2]然而,這種認識并沒有得到重復或擴展。1992年的《里約宣言》將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相聯系,以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來表達環境權利。該宣言的原則指出:“人類處于可持續發展的中心,有權過一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健康、有益的生活。”提出可持續發展的重點,是因為在《里約宣言》中提出健康環境權利的努力沒有達到共識,將重點放到了人類、全球人民及其發展上,而不是他們對環境的權利上。可持續發展問題在2002年世界首腦會議通過的《約翰內斯堡宣言》中得到肯定。從《斯德哥爾摩宣言》到《約翰內斯堡宣言》,將人類對優質環境的權利轉為注重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權利語言,實際上已與實質的法律權利相去甚遠。從人權的角度看,有人認為這似乎是一種倒退[3]477-490。
在國際條約方面,自1972年以來已經有超過350個多邊條約、1 000個雙邊協議處理環境方面的問題,大多集中于生物多樣性保護、防治荒漠化、危險廢物處理、瀕危物種貿易、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然而重要的是,這些條約都是監管方面的,其中并沒有關于人權的表達。此外,還有一些區域文書,眾多的國際、區域環境計劃和宣言都可能證明存在環境權,但是它們同樣通常不被作為人權倡議,不被認為是在人權方面的措辭。
綜上分析,在國際層面存在許多國際環境法律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存在明確的“環境權”嗎?根據人權公約或習慣國際法,并不存在作為國際人權法一部分的特定的環境權。盡管這種權利發展是一般的愿望,但是普遍接受這種權利的斗爭已經受到了事實的阻礙。當前的“環境權”理論更多地呈現為一種社會理念的宣揚,一種道德的宣誓,大多數評論家認為,無論是在國際人權中還是在習慣國際法中,還沒有將環境權作為一項單獨的人權明確地提出[4]。
二、現有人權是否涵蓋了環境權
雖然在全球層面現有人權文件未將環境權作為一項單獨的權利,但在涉及環境保護問題時,已經出現的一些司法解釋中許多人權條款與此相關。例如:生命權被視為生命不被剝奪的消極權利,然而在一些司法管轄區,生命權已經開始被廣泛地解釋為包括使用無污染的水和空氣的權利,包括國家對威脅生命的行為進行糾正的積極義務;尊重家庭和私生活的權利已在歐洲適用于對付噪音和工業污染問題;環境污染嚴重影響個人健康和福利的情況下,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條款可能與此有關;健康權也與環境問題密切相關,一些國家認為健康離不開良好的環境;其他權利條款,如言論自由權利等也已被用來支持獲得環境相關信息的權利以及環境決策參與權;教育權、工作權、文化權以及不受歧視的自由權等,也可能是與此相關的。
雖然現有人權確實是環境保護的有力武器,為全球和地方環境保護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幫助,但關鍵問題是現有的人權是否為環境提供了足夠的保護,現有的人權是否已經涵蓋了環境權?謝爾頓教授注意到,重點是沒有專門針對環境本身的權利,這就是一種限制,導致資源管理、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很難被帶到現有人權范圍中[5]。
當然,在這方面還有其他限制。首先,以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來保護環境質量,容易產生人類中心主義問題。因為其關注的焦點是污染的環境對人類的有害影響,而不是環境本身所受到的損害。例如,生命權被解釋為實際或迫在眉睫的危險,申請人個人需要受到影響。另外,環境問題的因果關系及其證明也是困難的。其次,所謂的第二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似乎更適合保護適宜、健康、可持續的環境,因為這些權利直接與人類福利和能力發展有關。但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受資源限制逐步實現的,這可能會嚴重限制這些權利在環境領域的有效性。此外,從人權的國際保護來看,對第二代人權的國際監督機制較弱,這會產生可訴性及司法保護的問題,當然會影響環境權的實現。最后,將環境權作為一種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在有關價值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時(如環境權與經濟發展權相比),環境權往往是脆弱的、居于下風的,這也不利于環境保護[6]。
三、保護環境的新的人權
“環境保護直接關系著人類的前途與命運,影響著世界每一個國家、地區、民族乃至每一個家庭及每一個人的生存與發展。”然而,現有的人權處理環境問題的方法是間接的,不足以應對緊迫的環境任務。對生態的關心給人權提出了新的挑戰,突破現有人權范圍,創設屬于人權的環境權,專門、直接地與環境利益相聯系,促使人權理論的發展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1. 創設環境權的意義
在某些情況下,一個新權利的創設可能造成現有權利的貶值。然而,不愿意去適應現有文書和擴大權利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形勢將產生同樣的后果。正如陳泉生教授認為:“環境權是一項新型的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7]在環境問題層出不窮的今天,加強環境權的理論研究,將公民的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來認識,強調和彰顯其價值和重要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8]。
首先,將環境權作為特定權利將更加突出環境本身。環境保護應避免人類中心主義,其應該不僅是為了人類利益,還為了其他物種和生態系統內在的、固有的價值。環境權倡導生態或自然本位,注重對生態的宏觀性把握,保護其他物種和生態系統[9]。任何對環境的權利,應包括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本身的一般責任。權利不僅涉及到人類的生理需求和欲望,而且它們可以并應該涉及到精神、文化和審美的需求與愿望。
其次,將環境權作為特定權利將使人們更重視弱勢群體的需求。窮人和發展中國家更易面臨環境退化的危險,擁有一個優質環境的權利會使人們集中關注他們的困境。這是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所要求的,其基本原理是:由于認識到當前環境退化問題中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各自的能力和發達國家補救的問題,考慮到具體的需要、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和新興的原則,需要各國互相幫助,以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再次,將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符合人權發展的歷史要求,也是對進步人權的積極回應[10]。環境權作為獨立的權利,應與其他權利平衡,而不是被隔離在法律框架之外。發展新的人權和環境補救措施,是對現存措施的補充和加強,而不是對現存措施的抵觸或重復(特別是針對環境退化的受害者)。實現整體環境和資源范圍內法律權利的有效均衡,將進一步完善人權的內容。
最后,將環境權作為一項單獨的權利也使環境權更明確并與發展權相協調。環境權與發展權是對立統一的[11],當環境權、發展權兩項獨立的權利存在沖突時,需要進行權衡。明確環境權將促使人類正確地處理環境自身利益和環境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
2. 環境權的內涵
將公民環境權確立為人權的一部分,必然會遇到如何界定環境權概念的緊迫問題,新的權利只有明確其內涵才能被廣泛接受和適用。環境權是人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12],其可能需要比其他一些權利具有更為顯著的特征。例如,它必須包括環境自身的利益、包括個人及集體的責任、考慮代際公平和責任等,所以在法律上定義這種權利存在一定的困難。目前,國際上尚未就環境權的準確表達方式達成共識。聯合國附屬委員會也未能明確定義,在其報告中使用了多種表述,如“健康、繁榮的權利”,“令人滿意的環境”,“安全、健康、經濟合理的環境”等[13]244-256。這些大多是主觀價值判斷意義上的術語,何為令人滿意的、健康的環境都是難以明確界定的。因此,一些反對者認為確立環境權是沒有實際意義和效果的,不可能對其作出一個實質性的明確定義。
但是,其實法律實踐中可以繞過對環境權明確、具體的標準定義。這種情況是立法上的常見現象,法律上許多基本的、通行的重要概念都有不同的定義、解釋或含義,都很難在學術界甚至法律中作出統一、明確而普遍適用的定義,但這并不妨礙法律對他們的確認,更不妨礙在法治建設中對他們的運用。例如,很多國家都沒有對“公共利益”下一個統一的定義,但這并不妨礙法律對公共利益的確認。本文認為,可以給環境權一個基本概念,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像其他人權一樣由管理機構和法院進行解釋。
為此,可以借鑒審議環境權問題的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法學家咨詢委員會的建議,將任何對環境質量權利的定義表達為:“所有個人、集體享有一個安全、可靠、健康、生態無害的環境的權利。為當代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并認識到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價值而保護、改善環境。”另外,本文還建議人們應該有獲取與環境有關的信息、參與環境決策和獲得法律救濟的權利[5]。這種權利的定義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環境權是實體性權利和程序性權利的有機統一。實體環境權是程序環境權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內容,為公民開展環境維權行為奠定了法律權利基礎。如果沒有被連接到一個明確的環境權,參與權無異于無源之水,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程序環境權是實體環境權實現的有力保障,增強參與權將促進決策透明度的提高和問責制的實施。其次,環境權既是權利也是義務。每個公民的環境權是平等的,在享有清潔環境以及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權利的同時,也要尊重和維護其他公民的環境權利,特別是要為子孫后代保護和改善環境。再次,環境權既是集體權利也是個人權利。環境權往往被作為集體權利而被歸入第三代人權,但是環境權也是一項個人人權,其主體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國家乃至全人類,甚至后代人。
3. 環境權的實現
將環境權定位為人權的一部分,必然意味著在法律制度上作出回應以使其得以實現。為明確環境權的人權性質,本文認為,應該將公民環境權上升到憲法的高度,通過憲法來直接將環境權規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事實上,當前不少國家的環境權立法已經出現了憲法化、公民權化和具體化的趨勢。例如:《南非憲法》中保障環境的權利,是“不會傷害到……健康或幸福”;《菲律賓憲法》承認需要一個平衡的生態和對大自然的重視,“應保護和促進人民的權利,符合生態平衡和健康地與自然和諧相處”;《帕勞憲法》要求議會采取積極行動,以實現“一個美麗、健康和資源豐富的自然環境”的目標。
憲法是關于法律價值觀的根本法,在憲法層面確認環境權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為其他具體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指出明確的方向,以保障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實現。各國應順應國際社會環境權入憲的潮流,從環境權的基本人權性出發,將環境權入憲并建立健全各項法律制度,以切實保障環境權的實現。
在決策和實施層面上,有關環境保護的問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法律語言來配合,使其能夠容納高度技術化的問題,解決復雜的因果關系以及保護復雜的生物和生態系統,這些都是困難的。當前,國際機構在資源利用方面可謂是低效率的,這可能是由于目前的人權機構缺乏與環境有關的專業知識。同樣,現有的環保團體亦可能缺乏人權專業知識。這表明可能需要一個聯合機構,提供一個受人歡迎的機會,理順人權和環境權領域的現有問題。可以考慮由一個專門機構鞏固相關專業知識以產生更好的協同作用,如環保團體在《21世紀議程》第38章提出了類似建議——應建立一個新的委員會,以確保有效實施《里約宣言》中的環境和發展議程。
四、結 語
人權的內容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歷史的進程,其權利內容會隨著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而不斷得到充實。環境問題涉及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優質的環境是實現其他人權的基礎,因此,在環境危機的今天,將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來認識是對人權的豐富和發展,對于我國貫徹兼具人權保護和環境生態保護目標的科學發展觀也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國際人權法教程項目組.國際人權法教程:第1卷 [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余俊,韋志玲.論環境權入憲的法理基礎 [J].科學發展觀研究理論月刊,2011(1):39-41.
[3]張愛寧.國際人權法專論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Lavanya R.The increasing currency and relevance of rights-base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narional negotiation on climate change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2010(1):12-18.
[5]Susan G.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J].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2009(6):38-42.
[6]那力,楊楠.環境權與人權問題的國際視野 [J].法律科學,2009(6):59-65.
[7]余晴.淺談環境權的人權屬性 [J].能源與環境,2007(6):65-66.
[8]程延軍.人權視域下的環境權及其保護 [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25-29.
[9]張輝.是非環境權 [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124-132.
[10]許明月,邵海.公民環境權的基本人權性質與法律回應 [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41-48.
[11]侯懷霞.論人權法上的環境權 [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32-37.
[12]王迪.環境權實現方式探析 [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1):93-96.
[13]帕特莎·波尼,埃倫·波義爾.國際法與環境 [M].2版.那力,王彥志,小鋼,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