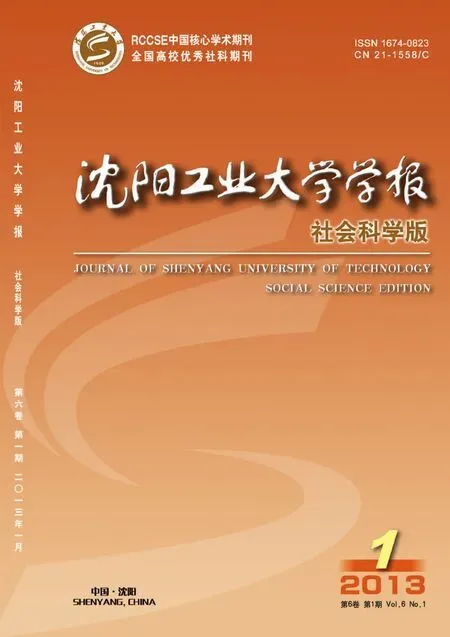論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及其生態意蘊*
劉素盼
(上海理工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上海 200093)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的秘密地,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其中對象化思想的提出。這也是后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徹底清算自己的哲學信仰,形成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新世界觀的關鍵性基礎。該著作主要從經濟學與哲學兩個層面詳盡地論述了其對象化思想:一方面,把對象化界定為創造某種對象的勞動過程,如“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1]52;另一方面,把對象化解釋為主客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其中關于人與自然在對象化活動即實踐中結成的對象性關系的具體闡述,對于當今正確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極富啟發性。
一、馬克思對象化思想的淵源

黑格爾的整個哲學體系主要是圍繞著思維的能動性展開的。在黑格爾看來,人的本質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等同體,而自我意識則是其所標榜的絕對理念。他認為,外部世界、現實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過是自我意識通過抽象的精神活動把自身的本質力量外化、異化的結果。“意識的對象無非是自我意識,或者說,意識的對象不過是對象化的自我意識,是作為對象的自我意識。”[1]102而現實的世界不僅存在事實性的缺陷,相當于抽象的自我意識也是有缺陷性的存在。因此,就需要克服意識的對象,實現對象向自我的復歸。馬克思肯定了黑格爾絕對主體的“自我活動原則”,但批判了其活動原則的抽象性即“抽象的精神活動”。馬克思認為真正的現實活動是現實的、具體的、歷史的、主體性的活動,是感性的對象性活動。此外,黑格爾還通過對象化的概念揭示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理解為人自己勞動的結果。馬克思吸收了其合理因素即“對象化是人類創造對象的勞動過程”,但否定了其把勞動對象化等同于勞動異化的思想,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異化勞動觀。
費爾巴哈批判了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主張用“有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取代“絕對精神”。費爾巴哈認為:“人沒有對象就什么也不是……但是這個與主體有著本質的必然的聯系的對象不外是這個主體固有的但又是對象性的本質。”[2]29在此,他將對象理解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把人理解為“人是人的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客觀本質”,認識到人與自然互為對象性的事實,但卻把人與自然界絕對地分割開來。在此架構上所理解的自然界只是純粹的、抽象性的存在[3-5]。在馬克思看來,對象化的主體不單是受動的、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存在物,更是具有自我意識的、從事感性活動的社會性的人;現實的自然界也不是與人絕然割裂的,而是被人的“本質力量”中介過的人化自然,也就是所謂的人的對象物并不是向人直接呈現出來的自然對象那樣。正是在人的對象化活動中,人使自然界人化即客體主體化的同時,也把自己的才能、天賦、意志等對象化到自然界中,從而使主體客體化了[6]。在主體客體化、客體主體化的交互作用中,人不僅實現了自身的完善,也將自然界的演進推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因此可以說,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正是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對象化觀點進行深刻批判和辯證綜合的產物[7-9]。一方面,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的“現實的人的對象化”批判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對象化”;另一方面,他又通過吸收黑格爾對象化思想中的合理內核——能動性思想批判了費爾巴哈直觀性的對象化,進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對象化思想,即在現實的歷史活動中形成一種對象性的物質力量,通過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活動生產出對象性客體,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
二、馬克思對象化思想的基本內涵
究竟何為對象化?其內涵又是什么?它與對象性、對象性關系究竟有何區別?在《手稿》中馬克思大量使用對象性、對象化等概念,有時在一句話中甚至同時運用[10],例如:“我在我的生產中使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點對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中由于認識到我的個性是對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觀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感受到個人的樂趣。”[1]184“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1]86鑒于此,國內有些學者主張將它們作為同義語使用,即使有學者持不同意見,也對它們的區別乃至各自的內涵存有分歧。因而,重新審閱《手稿》,探究其本意,對于撥開人們思想上的迷霧是極有價值的。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對象性是對象化形成的根基,是人類對象化活動形成、演進過程中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他認為,對象性是客觀事物所普遍具有的屬性,它們總是與周圍的他物處于對象性關系中,如“太陽是植物的對象,是其生命形式的確證”,“植物是太陽的對象,是其生命力量的表現”。也就是說,在人類誕生之前,自然界的物與物、生物與生物之間就廣泛進行著物理的、化學的或生物的對象性活動,各種動物在與自然界共同演進、改變自然環境的同時,也受到自然界的影響。即使是在人類產生以后,處于遠古時代的人依舊未擺脫“動物式的對象性活動”,即單純依靠肢體器官采集天然物,而不是利用生產工具有目的、有計劃地作用于自然物,從而獲取滿足自身需求的價值物。隨著對象性活動的進一步深化,人逐漸感到自身存在的受限性、渺小性,因此,在對象性的本質力量——激情、欲望等的作用下,在人為了確證自己擁有自由能力時,對象化活動便產生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1]86從而,真正意義上的人,能夠確證自身本質力量的人在對象化的過程中生成了。人的活動即對象化活動因此成為人的核心活動,而對象性活動則退居次要性位置[11]。
其次,馬克思認為,對象化是人類特有的屬性,是屬人的、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馬克思說:“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56也就是說,對象化是作為主體的人為了實現自身的某一目的、需求、欲望等,在遵循相關規律的基礎上,將自身的本質力量物化到“對象”上,使對象在“化”的過程和作用下改變其物質形態,以達到屬人化或屬我化的目的。這也正是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05但是“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1]88可以說,正是由于對象化活動的產生,人才得以證明自身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才得以證明自身是“有激情的類存在物”,才得以證明自身是區別于他物的類。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認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人卻懂得結合任何種的尺度以及自身的內在尺度,并按照美的規律和要求來構造和生產。
最后,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在對象化活動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的統一。近代以來的哲學家,無論是黑格爾還是費爾巴哈等都認為人與自然是一種抽象直觀的統一。馬克思則完全擺脫了傳統的、形而上學的、主客二分的思維窠臼,認為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是在對象化活動中實現的,是在對象化活動中形成的感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認為,“自然界,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適合地存在著”[1]107,“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1]89;同時,“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他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1]87。通過人的對象化活動,人使自然界人化的同時,也由于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為勞動產品而使自己客體化了,從而也就實現了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統一。此外,人不僅在意識層面使自身二重化了,在現實能動的活動中也使自身二重化了,從而“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1]88。也就是說,人通過自己創造的作品可以直觀到自身,進而確證了自己的本質性力量[12]。
三、馬克思對象化思想的生態意蘊
縱覽人類歷史,既有以“實體”作為萬能主體支配世間萬物的自然中心主義,又有強調人是萬物之主、自然之所存在于為人所用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這兩種思想傾向實質上都割裂了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忽略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性。環顧當今社會,各種生態“病癥”——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氣候異常等已嚴重威脅和制約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尤其是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危機更是給人們如何正確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敲響了警鐘。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重新審視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互為對象性關系的論述大有裨益。
首先,人以自然為對象,自然界是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環境因子。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可能把類當作自身的對象,乃是因為有自然界即他物的類為對象。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本身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直接的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須臾不可脫離的環境。“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1]56所以,“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的本質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105-106這充分說明自然界是人類的生命之基、衣食之源,它與人類之間并非是征服與被征服、掠奪與被掠奪、剝削與被剝削的對立的、不可調和的關系。如果人類一味地把自然界當作外在于自身的異己之物肆意地攫取破壞,那么自然生態在最后崩潰之時,便會對人類的“虐待”行為發起反“剝奪”的戰爭,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可能會因此陷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絕境,甚至會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這也告誡我們,作為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員,必須牢牢樹立“尊重自然,珍惜自然,關愛自然,呵護自然”的生態文明觀,自覺擔負起維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有意識地抵制符號消費、虛假消費等消費異化現象的侵蝕,以減少廢棄物、生活垃圾等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從而保護好我們的無機身體。
其次,自然以人為對象,自然界的豐富性離不開人的對象化。馬克思雖然承認自然界的先在性,但同時也認為人類誕生之前的自然界是荒蕪的、缺乏生機的、毫無價值的、單純性的物質性存在。自然之所以具有價值屬性,乃是相對于人的存在而言的概念范疇。正是由于有了人類的對象化活動,正是由于人類將自身的本質力量——才能、天賦、意志力、創造力等對象化,從而在自然物上留下了人的印記,才使得單一的物質世界成為一幅豐富多彩的、充滿生機的世界圖景,因而自然也成為屬人的或屬我的人化自然。正如馬克思所說:“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1]58動物的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人的生產活動幾乎改變了整個自然界的原貌。所以說,自然的生成、自然的人化、自然的豐富化等都離不開人類理性與智慧的對象化。在此意義上講,主張自然中心主義、否定人的作用的思潮是狹隘的、有失偏頗的,寄希望于排斥、抵制人類生產活動來保護自然、防止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從根本上說是使自然界退化到洪荒的、混沌的年代,實質上是對人類全部文明的否定。問題的關鍵是人類以何種方式、何種理念、何種模式作用于自然界,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如何實現和諧一致。為了實現自然界的人化、美化、豐富化,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統攝,走一條可持續性的、生態型的發展之路,自覺按照美的、和諧的規律塑造和再生產整個自然界。
最后,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和諧離不開人的勞動這一中介。人與自然的關系之所以不是黑格爾式的、費爾巴哈式的抽象直觀的統一,乃是因為人類勞動,因人類的對象化活動使人得以擺脫“純動物性”,獲得“真正的人的本質屬性”;同時,也使自然界得以擺脫“荒蕪的自在性”,獲得“屬人的價值性”,進而形成感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所以,正是在勞動即對象化活動中實現著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能量、信息的變換,維護著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之間的平衡。人類勞動具有不同于他物活動的特殊性,“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類“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1]57-58,且生產的是整個自然界。此外,人能夠“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58。所以,人類在進行對象化活動之前能夠預見自身的行為對自然和社會的直接或間接的、短期或長遠的影響,能夠在科技發明應用中、在資源開發利用中、在日常生活中順應自然規律,因而能夠在實踐中自覺控制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雙贏。那么,在面對“這個正在變得混亂不堪的世界,需要整體解放的世界”時,我們更應該注重人類生產、科技研發運用等活動之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力求使一切活動最大限度地達到真正的屬人化目的,跳出“人類發展自我——人類改造利用自然——自然報復——人類無機體受損”的怪圈,形成人與自然和睦、友好、和諧共生的對象性關系。
四、結 語
面對現代社會如多米諾骨牌效應般愈演愈烈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深入探尋馬克思對象化思想中的生態哲學觀對正確認識生態環境問題和尋求其解決之道無疑具有很好的理論指導作用。引發當代社會生態環境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認識根源,又有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原因,因而解決環境危機的路徑也不是單一化、速決化的。人類生態文明意識的覺醒乃至現實化的行動表明,人是自然生態系統中唯一有意識、有責任的類存在者,有理由堅信,人類一定可以實現自然界的人道主義和人類社會的自然主義之統一,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著作選集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3]解保軍.馬克思自然觀的生態哲學意蘊:“紅”與“綠”結合的理論先聲 [M].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4]郭景萍.馬克思對象化理論的哲學意義 [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4):1-6.
[5]牛菲.對象性活動中的人與自然: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J].唯實,2008(5):25-29.
[6]曹國圣.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的本質思想的再認識 [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5,21(4):46-49.
[7]周義澄.自然理論與現時代:對馬克思哲學的一個新思考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陳國友.對象化、異化及其揚棄:早期馬克思的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初探 [J].黨史文苑,2008(1):52-55.
[9]敬志偉.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理解 [J].齊魯學刊,2001(1):65-68.
[10]李昭新.論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生態維度 [J].甘肅社會科學,2002(5):58-61.
[11]張紅嶺.解析馬克思哲學新原則的關鍵詞:對象性活動、感性活動和實踐 [J].理論界,2011(8):11-12.
[12]李文耀.人與自然演變發展的歷史思考 [J].江西社會科學,1991(5):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