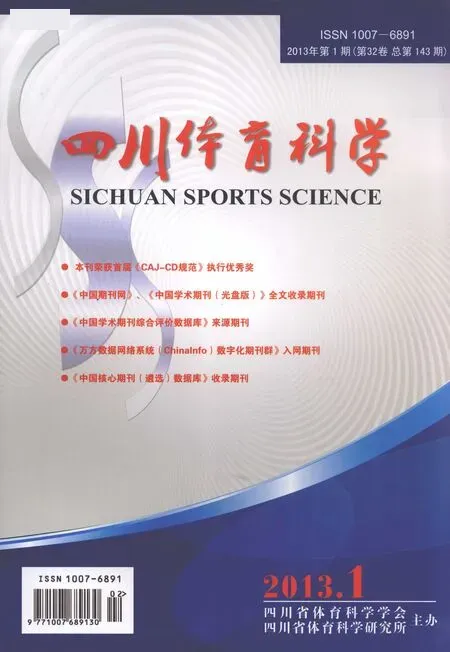身體的哲學研究綜述
——以西方身體哲學為視角
海景龍,陳 麗
身體的哲學研究綜述
——以西方身體哲學為視角
海景龍1,陳 麗2
通過對西方哲學身體觀的歷史考察和梳理,以身體為切入點闡述身體運動的發展嬗變,在哲學層面將身體依據其屬性或特點分成幾種類型,并以此出發提煉身體與體育的聯系,闡述身體觀對體育發展嬗變的影響,最后結合當下身體實踐對身體文化進行了反思。
西方哲學;身體觀;體育
身體問題是哲學中一個亙古彌新的問題。身體不只是生理意義上的形軀,更是由歷史、社會、政治權利與文化的建構而成的,它是人自我理解的起點,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媒介。當代西方知識界掀起的一股“身體”取代“主體”的潮流,表明重新思考“身體”與“主體”的關系已成為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當下,信息化時代的人們過度追求快捷簡便的生活方式時往往忽視了自己的身體。身體知識和身體觀念的陳舊,消費欲望的膨脹和享樂主義的盛行等在實踐中映射為身體的異化——身體成為了消費和性與欲望的代名詞。而過度依賴高科技的生活方式也導致了人們身體運動的不足,現代社會出現了“文明病”、“亞健康”等不可回避的問題。競技運動領域也出現了虐身體化、肉欲化等現象,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深切憂慮和反思。
本文旨在通過對西方哲學身體觀的歷史考察和梳理,同時回顧近年來體育界身體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歸納、提煉身體與體育的本質聯系,以期對建構健康、和諧身體思想的有所助益。
1 西方哲學中的身體觀研究
復光[1]指出,身體論題是一個老而彌新的問題, 一個屬于全人類又屬于每個民族每個人的普遍又特殊的問題。雖然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就注意到自己的身體, 但人的身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時代卻有不同的遭遇, 人們對它的態度亦頗為不同。
王曉朝[2]指出,“如果說蘇格拉底以前的古希臘哲學家們關注的是自然的話,那么,從蘇格拉底開始,哲學的主題開始轉向人自身。”由于蘇格拉底沒有著作留世,我們只能從他學生的記述了解其身體觀。李成實[3]認為,“靈肉兩分的隱秘和曲折悄悄駐扎在古希臘哲學家的理論中,以巴門尼德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就開始拒斥普羅泰戈拉的感性論,他認為只有在理性認識中才能確立知識與對象的同一性。以至于后來蘇格拉底也豎起了理性主義的大旗,摒棄感覺崇尚理性,認為身體對于知識、真理、正義和美德來說,是一個不可信賴的因素和通向他們的障礙。”在蘇格拉底看來,哲學家需要不斷避免不必要地卷入身體方面的任何事情,以便達到使他能夠獲得關于真理、知識所必須的凈化程度。
趙敦華[4]在《西方哲學簡史》中提到,靈魂與肉體的區分蘊涵著后來被稱作身心二元論的觀點。在柏拉圖看來,身體活動始終受靈魂支配,身體只是靈魂的婢女聽任靈魂擺布。在柏拉圖的這個二元論傳統中,身體基本上處在被靈魂所宰制的卑賤——真理的卑賤和道德的卑賤——位置。他認為靈魂是善的、純潔的、不朽的,而肉體卻是惡的、貪欲的、死亡的。肉體的欲望污染了靈魂,妨礙了他對真理和智慧的追求。所以只有學習哲學,或者死亡,靈魂才能擺脫肉體的誘惑和束縛,達到理性和自由。可以說,自此以后,身體陷入了哲學的漫漫黑夜。
陳志堅[5]指出,亞里士多德將靈魂定義為“潛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體的第一實現”。亞里士多德的這個定義一方面肯定了靈魂是非物質性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靈魂和軀體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軀體和靈魂的關系,就是形式和質料的關系。按此理解,靈魂是依賴于軀體的,它是功能,但不是實體。但是,他又認為軀體的所有部分都是靈魂的“工具”,這樣靈魂與軀體就有著二重關系。從存在方面看,靈魂依賴于軀體,沒有軀體也就沒有靈魂;從作用來看,軀體服務于靈魂,沒有靈魂,軀體就不成為軀體。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開創性地論述了精神現象與其身體的緊密聯系,認為如果思維也是一種想象,或者至少依賴于想象,那么他也不能沒有身體。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體育有助于“培養人的勇敢”,他在《政治學》中提到,應當首先關心孩童們的身體,然后才是其靈魂方面,再是關心他們的情欲。當然,關心他們的情欲是為了理智,關心身體是為了靈魂。
趙方杜、侯鈞生[6]認為,在中世紀,教父哲學家認為,在上帝之城面前,身體只是世俗之城的一個罪惡的淵藪,它貪婪、自私自利、追求短暫的歡愉,阻礙了人們對上帝的愛。所以只有禁欲、苦行、極端壓制身體的欲望,靈魂才能升至天國。奧古斯丁主張的禁欲主義把身體推向了苦難的深淵。
季曉峰[7]指出,在笛卡爾那里,身體與物質、廣延聯系在一起,而把心靈與精神、思維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身心二元論,這是清楚分明的要求使然。笛卡爾通過普遍懷疑的方法切斷了在尋找真理的過程中對身體的依賴,把獲得知識和真理的機會都置于無軀體的心靈。從此已降的西方哲學史,心靈和身體成為兩個毫無聯系的實體。笛卡爾從懷疑自己的身體出發到懷疑上帝的存在,最后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結論,從而從思維出發構建了他的哲學體系,同時,也拋棄了人的身體。
于濤[8]在《體育哲學研究》中提到,尼采站在權力意志的高度對統治了數千年的理性進行了猛烈批判用“肉體”來對抗意識哲學的獨斷性從而將身體推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明確提出了“一切從身體出發”的口號,認為身體具有重估一切的價值。他認為,身體乃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異的思想。
陳治國[9]提到,在梅洛龐蒂看來,身體本身就是一個與世界和他人處于不斷互動和對話中的主體,在身體知覺的深處存在著為任何理智的反思所無法達到的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以及自在與自為的統一性。梅洛龐蒂認為我們是以身體在世,身體是現象意義上的身體而非傳統意義上客觀的身體,身體是構成世界的本源,是世界的媒介,身體作為我們能擁有的世界的總的媒介,它不僅在我們周遭預設了一個生物學的世界,以進行保存生命所必須的行動,同時為自己制造出一種工具,在自己的周圍設計出一個文化的世界。
文軍[10]指出,身體能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影響巨大,福柯居功至偉。如果說傳統的身體研究更多是停留在社會建構和文化再造的話,那么福柯的研究則進一步將身體推向了政治層面,建立了身體政治學。張之滄[11]指出,整個人類歷史的悲喜劇都是圍繞身體進行謀劃,展開角逐;精心利用各種組織形式和權力技術試探它,挑逗它和生產它,摧毀它和塑造它。可見,福柯的身體是與權力密切相關的,當現代政治權力運作與身體發生關系時,身體便降格為機器的身體,這種機器的身體是一種被動的、馴服的、奴性化的身體,這種物質性的身體之上批裹銘刻著厚重繁復的社會文化、知識權力話語,各種國家機器,
管理組織對其進行了展開了嚴密的規訓與監控。
汪民安、陳永國[9]指出,德勒茲是尼采的身體哲學忠實的信奉者。尼采的力被德勒茲改造為沒有主體、非人格化的欲望,這種欲望就是身體本身。且欲望只和欲望連接,只向別的欲望流動,欲望的唯一的客觀性就是流動。在德勒茲這里,身體被視為一股活躍的升騰的積極性的生產力量,是一部永不停息的生產機器。就像尼采將身體以及身體的力量視作是世界的準繩一樣,德勒茲同樣將身體看做是一部巨大的欲望機器。德勒茲的這部欲望機器也在不停地生產、創造;欲望生產著現實。
鄧先進[12]指出,在布爾迪厄看來,身體的發展與其所處的社會地位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對身體的運用、塑型恰好顯示了這種身體背后的潛力壓迫和文化資本的隱蔽性存在。身體是一種資本,而且是最為價值承載者的資本,積聚著社會的權利和社會不平等的差異。或許正是在身體成為資本的這種現代圖景中,身體資本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也可以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是資本,也是象征的符號;身體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支配的“他者”,身體還是一種話語的形式,在身體和社會之間,具有多種的不平等權力關系。
綜觀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從柏拉圖—奧古斯丁—笛卡爾路線之虛假的,邪惡的無知的身體到現象學傳統的功能性、形式化、基源性身體,再到后現代理論的物質性、生產性和欲望化的身體,身體意識的覺醒及其推進經歷了一個由隱而顯、由虛而實,從形式到內容、從邊緣到中心的漫長過程。”[13]上述觀點的大致類型,可分為身心二元論觀點,身心一元論觀點,二元論中的身體優先論。
2 身體的屬性與內含
當前哲學界在研究身體時, 更是將身體高度抽象化和象征化,身體成為一種標志物,因而缺少具體特性,哲學家在談論身體時首先將身體不自覺地分裂為生理身體和文化身體,而他們關注的重點就是那個游離于生理身體之外的文化身體。通過對西方身體觀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出,身體是多維的,多層次的、不斷生成的、流動變化的文化存在。身體的屬性在于其具有的物質性、獨立性、時間性、空間性、隱喻性和未定性。概而論之,在傳承了兩希文化的歐美世界,身體具有模棱兩可性,它既是群體性的、客觀的、物質的、自然的身體,也暗含著個體性的、體驗的、社會的身體之意。就在這種二元對立中,生理身體是基礎,而社會身體則更趨近于人們對身體的基本理解。
西方表示身體的詞語往往只側重于身體作為物質實體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性,這與古希臘以來人們對身體所做的二元劃分有密切關系。鄭岷【14】認為,身體背后所依附的意識指向較多,所包容的哲學范疇較大,所以西方哲學中對身體的界定一直以來也都較為模糊。身體是體育發展的原動力,體育改革最終要直面身體,體育文化最終是要回歸于我們的身體。由于身體本身的抽象性與未定性,屬性的多元性、復雜性,為其建立一個標準化的定義無疑是困難的。但也并非虛無縹緲沒有界限,在特定的論域與語境下,我們對其界定如下:本文中的身體指自然人具有的以生物本源性為基礎,以社會文化性為特征的物質實體與文化存在。
3 關于身體結構的研究
童麗平[14]指出,身體首先是作為一種自然物存在的,而這種存在方式主要是以生理身體為標志。生理身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封閉性和獨立性,這就注定了體育活動必然要依附于身體,特別是依附生物身體。指出,生理身體是體育的實踐者,生理身體是體育的創造者,生理身體是體育的受益者。
金川江[15]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更多地關注生理身體,而對社會身體則缺乏注意,潛意識里將社會身體劃歸出去。身體既是一種自然物質存在,同時也是人類文化的構成體;既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發展產物,又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可以說是自然與社會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也是宇宙自然和人類文化的交合銜接點。在其自身發展的同時又與對其本身進行塑造、刻寫、滲透的自然、社會、文化進行著復雜互動交流,它既是自然界的產物又是文化界的產物,并且是處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以至其規定性隨著歷史、地域、種族、性別等等諸多因素而生成、變化著。
肖嬋[16]認為,身體是體育活動的重要物質載體,身體文化對體育的價值有深遠的影響。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出現促進了后現代身體文化的形成,后現代身體文化影響下,當今社會人們的體育價值呈多元化傾向,給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胡科、虞重干[17]指出,作為組成社會的細胞——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改造世界,尋求自由的過程中,必然也受到了歷史與現實環境的雙層規約。不同時代賦予了身體不同的使命,體育是社會實現身體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身體教化的過程中,歷史在身體上留下的刻痕是不被遺忘的,也正是身體教育的歷史性才使得體育能夠由歷史走進現實。一方面,身體通過社會化不斷獲取了身體實踐能力,身體實踐能力的積累促進個體實現社會化;另一方面,身體社會化不斷建構身體,賦予身體意義、價值、內涵。如果說,在個體層面,體育之于個體的意義在于促使個體變成一個合格的存在者;那么,在社會層面,體育則是依據不同社會的需求,對身體實施教化與塑造,使身體能夠由個體走向群體,真正融入社會,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所謂主體性,就是“相對于整個對象世界,人類給自己建立了一套即感性具體、擁有現實物質基礎(自然)又超生物族類、具有普遍必然性質(社會)的主體力量結構(能量和信息)”。生活中我們關注的往往是身體的作用對象的現實和感性,知識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身體,而不是把身體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參考下社會學家奧尼爾的觀點,或許我們對身體結構會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奧尼爾在《身體形態》中提到,我們把目光從世界身體轉向人類社會這一較小的世界時,我們驚訝地發現,人們早已按照人類身體的形態來構想個體生命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了。羅伯特.赫茲對右手的研究表明: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二元論象征主義,其中左手和右手(之間的二元對立)也被歸納了進去,并成為了世界等級秩序的一部分。作者從此類比出發,論證了:正如我們以自己的身體構想社會一樣,我們同樣以社會構想自己的身體。
同樣,體育中的身體也時刻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身體運動從根本意義來講是一種身體實踐,身體就是實踐的主體。就身體運動的發展而言,文化身體的回歸就是身體運動本質的回歸,身體文化發展的基礎是生物身體,隨著人的社會化,生物身體逐漸衍生社會身體的意義,但無論是生物身體還是社會身體,最終都依賴于主體性身體的發展。
4 身體觀與體育發展
謝光前、陳海波[18]提到,解讀體育發展史可以看出,體育的興衰沉浮始終影響人們對身體的感受和認知,關涉到身體的解放程度。由此我們可以正本清源,在今天高揚人文主義體育的旗幟下,讓身體立于體育的核心,使現代體育不再攙雜有與身體走向“更高、更快、更強”和“更人性、更純潔、更快樂”悖反的因素。在我看來,身體觀影響著體育觀的發展嬗變,哲學中對身體的認識和定位,總是潛移默化地指導和影響著現實中的身體實踐。
理查德·舒斯特曼[19]提到,與西方傳統意識哲學的身心二元對立相對應,我們的知識領域也被區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身體自然被歸于自然科學。馬祥海[20]指出,身體之于體育絕不僅僅是工具化的“載體”和“中介”,身體是銘寫著歷史的樣本,同樣也是一條考察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要線索。身體不斷發生著由被蔑視的規訓狀態,被遮蔽的遺忘狀態到被尊重的凸顯狀態的嬗變,與之相適應,體育運動也經歷了從身心二元對立的客體化式體育、身心二元對立的主體化式體育到身心統一的生命化式體育的歷史嬗
變。作者通過回顧梳理體育運動的歷史嬗變,認為體育作為人類自然生命(身體)的延續與發展以及精神生命(心靈)充盈與提升的需要,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的產物。
王振成[21]等一文中提到體育中存在著大量的狂歡現象,當代體育是身體的狂歡。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下,身體不僅是美的載體,力量的源泉,更是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我們對身體在人類哲學和認識歷史中價值和位置的追溯和考察,是為了更好地思考在體育運動和狂歡中身體的獨特意義。在人類文化歷史中始終貫穿著靈與肉、“上半截”對“下半截”、理性與非理性、壓抑與反抗的矛盾抗爭。無論是人對身體產生懷疑,充滿恐俱的時候,還是張揚身體,肯定欲望,尊重生命的時候,身體作為體育核心的地位始終不可動搖。對于體育而言,身體與狂歡永遠是遠未完結的話題。
綜上可知,以西方哲學家們對人體一元論或二元論的認識為主線,我們便可窺得體育發展的全貌。自古希臘以來,當把肉體、靈魂看作統一體時,這時期的體育就會受到重視、繼而取得較為明顯的發展,至少不會被無端打擊和排斥。當把身心看作對立的兩個部分時,在二元論時期體育的發展就會受到抑制。西方歷史長河中交替上演的人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兩種體育思想其實都有著深刻的哲學、歷史背景,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身體的認識。在人文主義者眼中,身體是體育的起點和歸宿,是我們關照與呵護的對象。在軍國主義者眼中,人是捍衛統治階級政權的機器,而身體不過是工具而已。可見,我們對身體的認知、對身體觀念的把握關涉到身體的解放程度和發展層次,關系到人的自由狀態的提升。就體育而言,積極健康的身體理念是體育發展的深層動力,消極腐化的身體觀念則必定阻礙體育的健康發展。如今,中國體育的發展已成蓬勃之勢,構建和諧共生的身體觀就成了當下不可回避的理論問題。至于體育中身體意識,身體資本等問題的探討,乃是留給我們的有待深入的研究課題。
5 對現代體育實踐的反思
在當下的身體運動實踐中,受西方傳統意識哲學的映射,工業時代物化現象的泛濫導致了身體的異化,身體被淪為一種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身體成為了消費和性與欲望的代名詞。值的注意的是,現代體育在其健康發展的道路上,存在著一種虐身體化和泛身體化甚至肉欲化的傾向,興奮劑事件的屢屢曝光意味著某些運動員在某種利益的驅使下, 不惜以虐待甚至犧牲身體為代價去達到目的;運動場裸奔頻現、運動員放縱肉欲則是以身體的名義拋棄了精神和靈魂。
在學校教育中,有人認為體育就是鍛煉身體,身體就是指肉體與精神和心靈無關,結果訓練出的強壯的身體對人的生活來說,往往又是不幸的根源。而更常見的現象是,教育者往往輕視學生的身體導致運動不足,學生體質逐年下降。
周榮勝[22]指出,在步入新世紀之際,我們理應重審自己的身體知識,淘汰陳腐的身體觀念,用更深厚的思想建設健康而美麗的身體。
綜觀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學界對“身體”問題的研究還處于初探階段。由于從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身體”才成為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大陸”,直到近年來身體研究才納入到我國學界的理論研究視野內。所以取得的學術成果十分有限。只要我們談到“身體”問題,不可避免地碰觸哲學史上的永恒焦點——身心問題。綜合體育界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從身體的某一角度或屬性出發展開自己的研究,展現的往往是對身體某方面的看法,很少論述整體性的身體特征。身體與身體運動密切相關,但體育哲學對此的研究卻處于起步階段。身體的概念的界定,屬性,分類等基本理論問題在體育類文獻中或少有涉及,或一帶而過。對哲學史中“身體”觀念的流變的論述大多流于形式,罕有嚴謹獨到之描述。對于身體和身體運動的關系問題,大多文獻對二者關系的理論提升不夠,或天馬行空隨意曲連提煉,或落入程式化的窠臼。在中國學界乃至體育界,不乏對“身心對立”問題的猛烈批判,更有甚者將身體的重要性無限突出,從而陷入了另一種極端。從哲學史角度梳理身體觀念的流變,從而以一種堅固的理論依托界定“身體”,從哲學的角度提煉身體與身體運動的本質聯系,結合現實進行理性批判和解讀,無疑對推動身體運動實踐的健康良性發展是一種有益探索。
[1] 復 光.“身體”辯證[J].江海學刊,2004(2):5~8.
[2] 王曉朝.希臘哲學簡史——從荷馬到奧古斯丁[M].上海:上海三聯書社,2007:128,386.
[3] 李成實.馬克思身體理論研究——身體:理解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新視點[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08(4).
[4] 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85.
[5] 陳志堅.哲學簡史[M].北京;線裝書局,2006:26.
[6] 趙方杜,侯鈞生.論身體社會學的產生和思考[J].理論與現代化,2010(2):99.
[7] 季曉峰.論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對身心二元論的突破[J].東南學術,2010(2):155.
[8] 陳治國.論西方哲學中身體意識的覺醒及其推進[J].復旦學報,2007,2(2):84.
[9] 汪民安,陳永國.身體轉向[J].外國文學,2004:18.
[10] 文 軍.西方社會學理論:經典傳統與當代轉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9.
[11] 張之滄.后現代身體論[J].江海學刊,2006(2):25-26
[12] 鄧先進.當代西方身體文化理論簡述[D].烏魯木齊:新疆大學,2008:14.
[13] 陳治國.論西方哲學中身體意識的覺醒及其推進[J].復旦學報,2007,2(2):84.
[14] 趙 岷.身體·體育·文化——西方身體哲學視野下的體育反思[D].江蘇:蘇州大學,2007:15.
[15] 童麗平.身體哲學視野下的體育文化反思[J].體育與科學,2007,28(3):31~33.
[16] 金川江.身體視角從新審視體育教育[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1):81.
[17] 肖 嬋.后現代身體文化語境下的體育價值觀[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9,29(3):8~10.
[18] 胡 科,虞重干.論大體育的邏輯起點與演繹路徑:從身體的角度[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10,24(2):49.
[19] 謝光前,陳海波.體育之興衰與身體解放[J].江南大學學報,2006,5(4):108~111.
[20] 理查德·舒斯特曼[美].通過身體思考:人文學科的教育
[J].2007,39(10):5~10.
[21] 馬祥海,宋紅玉,程衛波.身體之維:體育運動的歷史嬗變[J].體育學刊,2008,15(8):16~18.
[22] 王振成,李亞英,劉少華.當代體育哲學文化反思之四——體育、身體與“狂歡”[J].體育文化導刊,2005,(1):32.
[23] 安德魯·斯特拉桑[美].身體思想[M].王業偉等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1.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Body Research——form Perspective of Western Physical Philosophy
HAI Jing-long1,CHEN Li2
Based on a carefu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body studie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indic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dy move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body, and further divides body into different types in terms of its properties and features, 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It also suggest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body views on phys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Finally, reflection on physical culture concerning current physical exercise is presented.
Western philosophy;Views of body; Physical education
G80
A
1007―6891(2013)01―0018―05 四川體育科學
2012-10-19
1.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510006;2.河南大學體育學院,河南 開封,475001。1. P.E. College of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60, China; 2. P.E.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