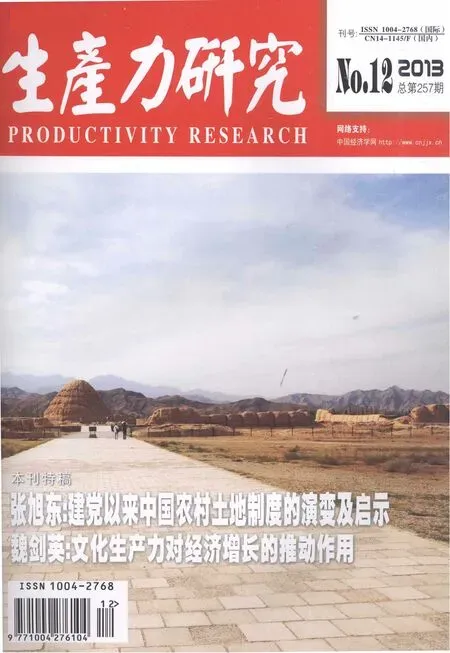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補貼機制的思路建議
劉 云,廉李章
(1.蘭州城市學院城市經濟與旅游文化學院;2.蘭州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鐵路實行政企分開,建立健全規范的公益性線路和運輸補貼機制。隨后國務院在《關于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有關問題的批復》中進一步明確,對鐵路的承擔的學生、傷殘軍人、涉農物資等公益性運輸任務,以及青藏線、南疆線等有關公益性鐵路的經營虧損,研究采取財政補貼等方式,對鐵路公益性運輸虧損給予適當補償。本文從分析現狀和把握難點入手,就順利推進改革提出一些設想。
一、鐵路公益性運輸服務的現狀
1.公益性鐵路。公益性鐵路是指主要服務政府政策目標的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的鐵路,在規劃設計時就突出考慮政治穩定、國土開發、民族團結、國防建設、社會公平等因素,而將項目經濟效益放在次要和服從的位置。公益性鐵路修筑工艱款巨,初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項目交付使用后,因低運價、低運量和高營運成本造成鐵路企業收不抵支,經營虧損不可避免。然而公益性鐵路項目又產出了顯著的國民經濟效益,外部利用者和一般消費者享受到低運價便利,隨著運輸流向鐵路轉移和集中,社會物流成本整體降低,它既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還是某些純公共物品(國防、國土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1]比較而言,西北鐵路是我國鐵路網中公益性最強的板塊,已建和在建青藏、南疆、蘭渝、敦格、敦煌等公益性鐵路,其中青藏鐵路是邊際社會產值與項目產值最大化分離的鐵路建設項目,而南疆鐵路則是公益性因素導致政策性嚴重虧損的典型。
2.公益性運輸。公益性運輸是指鐵路部門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的社會運輸服務。學界目前界定的公益性運輸項目主要有:學生、傷殘軍人運輸;搶險、救災物資運輸;支農物資運輸;軍事物資運輸;軍運客運;鐵路支線運輸;特種物資運輸等。全路18個鐵路局(公司)均不同程度地承擔公益性運輸任務。其中,支農物資運輸量2010年已占全路貨運總量的4.68%,為運量最大的公益性運輸項目。有全國人大代表統計鐵路對糧食、棉花、化肥、農藥、磷礦石等支農物資實行減免鐵路建設基金和低運價政策,年均減收約136億(武汛,2009),而鐵路部門近年則披露涉農物資運輸年損失額達數百億。盡管這些數據還有待核實,但可以確認公益性運輸使鐵路自身蒙受的利潤損失相當之大。公益性運輸涉及面廣,折扣率高,如學生、傷殘軍人運輸的折扣率為50%,收入難以彌補成本。鐵路企業承擔的公益運輸運量越大,損失也越大。鐵路部門以自身收益的大量外溢為政府公益性目標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鐵路公益性線路和運輸是基本公共服務中成本大于收入的部分,公益性運輸虧損是企業不能自化解的政策性虧損。長期以來,中央政府指令鐵路實行“交叉補貼”,即在鐵路行業內部以經營利潤彌補公益性虧損,“整體打包”自行消化公益性運輸成本。中央政府無需說服協商就向企業轉嫁公益性運輸成本的權威行使成本很低。表面上看,公益性運輸成本交由企業承擔,政府的財政負擔減輕。公益性運輸成本在政府低運價管制下固然未向前轉嫁給消費者,而是向后完全轉嫁給鐵路企業,中央政府最終還是鐵路龐大積累債務的“買單”者,所發生的交易費用實際上高不可估。政府的公益性事業讓企業承虧減負是不合理的,建立公益性運輸補貼機制是應有的制度安排。但由于長期執行“交叉補貼”,公益性運輸責任主體不清,政企財務邊界模糊,“如何補貼、補貼多少”是政府和企業都不熟悉和不擅長解決的改革現實難題。
二、針對“如何補貼”難題,統籌確定補貼原則、范圍、對象和方式
1.建立補貼機制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也是中央政府處置鐵路公益性問題方式由“交叉補貼”轉向“購買”的高級別和高難度改革。著眼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立足重塑新型政企關系,依據國務院政企分開、理清職責、確保穩定、適當補償的有關要求,先立補貼原則,據以制定認證細則,是改革有序推進減少試錯性成本的前提保障。
2.公益性線路主要鋪設于西部特別是西北民族邊疆欠發達地區。公益性運輸主要包括軍人、學生的半價優惠和搶險、救災、支農、軍用物資的優價和無償運輸。雖然補貼范圍已匡定包括“公益性線路”和“公益性運輸”,然而,由于前者除了強公益性的青藏線、南疆線,還存在不少公益性強度次之但公益性亦強于經營性的線路,且干線、支線和專用線構成復雜,學界至今對“公益性線路”仍無統一清晰的劃定。而后者除上列諸多項目還涉及到市郊旅客、專列及國際運輸等,學界普遍認為“量大面廣”為我國鐵路公益性運輸的突出特征。因此,有必要在充分研究與論證基礎上,對納入補貼框架的“線路”和“項目”予以再確認,從而細化改革方案,進一步廓清補貼范圍。
3.補貼對象為鐵路運輸企業。調研發現,全路18個鐵路局(公司)均承擔公益性運輸任務,近5年經營總盤點為11家盈利7家虧損,企業間公益性運輸虧損的拖累程度及自化解能力差別甚大。太原、鄭州等鐵路局的經營性利潤足以彌補公益性虧損,而青藏鐵路公司單一管理“天路”運輸根本不存在保本經營的機會。鑒于鐵路內部的復雜情況,補貼對象可先確定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由其遴選確定二次補貼對象,引入特許權競爭并擇選適用模式,那些達到補貼規定條件、補貼額度要求合理、承諾保障服務質量的企業獲得補貼資格,那些托管強公益性線路和因公益性運輸造成政策性嚴重虧損的企業列為重點補貼對象。
4.從青藏線的調研情況來看,公益性線路經營虧損主要由低運價、低運量、高營運成本的“兩低一高”因素所致。財政補貼可作為收入使用,使低運價低運量下的有限收入得到追加;財政補貼還可使用于彌補成本,使高營運成本得以削減,分別形成“收入大于成本”和“成本小于收入”的補貼效應。就后者而言,青藏鐵路高寒凍土區多災害線路養護、“多套冗余、互為備用”專用設備購置維修、旅客列車特殊服務等支出費用是普通鐵路所沒有的;高原牽引主力機型——內燃機車每萬噸公里耗油量為全路平均水平的1.48倍,大修、中修、小修、輔修的平均時間分別高出全路平均水平的6.9%、49%、48%和59%。[2]對其特殊線路養護、專置設備維護、高原機車作業、旅客特殊服務成本予以專項定額補貼,以原始消耗報表及有關記錄為依據,以達到全路平均成本水平為標尺,是一種涉面小可單獨并透明化操作的成本補貼方式。因而認為在強公益性線路經營虧損補償上,直接追加運輸收入和直接彌補營運成本的補貼方式均可奏效。而同時注重運價、折舊、稅收、貸款、輔業和債務處置等配套政策的研究與應用,對深化補貼機制改革及其與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接軌都具有現實而重要的意義。
三、針對“補貼多少”難題,務實擇定補貼比例和建立成本分攤機制
補貼多少的前提依據為虧損多少。問題在于,鐵路部門從未正式公布過公益性線路和運輸虧損的完整數據,現有文獻也未見之基于定量分析的企業個案實證。僅根據調研獲得的內部數據得知,近5年運輸盈虧年平均值,青藏鐵路公司和烏魯木齊鐵路局(托管南疆鐵路)均在-20億以上,承擔繁重糧食調運任務的哈爾濱鐵路局則在-50億以上。雖然可判定鐵路“三大虧損戶”的虧困主要由公益性因素所致,卻很難測定其具體損失額及客運、貨運、路網各自成本費用。客觀地說,在公益性與經營性因素交叉情況下單獨分離前項成本的難度很大,加之長期執行交叉補貼,鐵路運輸企業發生虧損無需界定究竟是公益性還是經營不善虧損,“整體打包”的處置成為常態。[3]公益性運輸成本賬是企業的模糊賬,也是企業在“大鍋飯”體制下不愿公開的信息數據。
政府僅對上述三家企業按“保本經營”標準補貼,每年就要支出近百億元。改革需要考慮政府財政的可承受能力。意、法、英、德、西等歐洲發達國家,政府給予鐵路的財政補貼分別占成本的20%~70%;加拿大相關法案初始規定政府對公益性運輸虧損承擔80%的補貼;美國聯邦政府對“非盈利”的全國鐵路客運公司(Amtrak)依法令補貼其營運成本的50%,因未扭轉虧損后轉向貸款方式。[4]各國的補貼標準不盡相同,但都沒有對公益性運輸虧損予以完全補償,公益性運輸損失額并不等于補貼額,且補貼管理嚴格,不支持一味依賴補貼而經營不當的企業。
第一,國家鐵路局等規制機構加強對鐵路企業運輸成本數據的監督,將顯示真實成本數據列為企業申請補貼的“硬約束”條件,核定企業披露的公益性運輸成本數據,聽取來自外部會計、審計機構等第三方的評估咨詢意見。但政府監督和第三方評估也需掌握有關的信息,成本數據的不易獲得性意味著需要使用具有較高激勵強度的補貼機制。另一個突破性的思路是,選擇固定或上限補貼機制,使對成本的補償不依賴于成本的觀察數據,用機制來排解公益性運輸損失額測定成本很高且不完全準確的難題糾結與困擾。[5]
第二,政府對公益性線路和運輸虧損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在具體操作中,不僅要考慮不同線路和項目的具體情況,以及不同地區鐵路運輸企業的資產質量、公益性運輸周轉量等,還要充分考慮滿足企業可解困和政府可承受的激勵相容條件。傾向根據上述因素建立一套合理的分值測度體系,確定不同線路、項目及企業的適度補償率并相對固定。新機制運行有必要擇定線路和項目先行試點,探索社會監督補貼預算和公共支出績效考評的方式方法。
第三,補貼比例的確定還是一個如何在中央政府、鐵路運輸企業、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攤公益性運輸成本的問題。中央政府擔當補貼主體。繼續鼓勵和引導鐵路運輸企業履行社會職責,承擔一定比例的公益性運輸成本,政府對企業的業績考核更加注重引入社會效益變量。欠發達省區政府普遍受困于地方財政短缺,籠統實行“誰受益、誰補貼”原則似不現實,而是期待其在公益性線路建設的規劃協調、用地預審、環境評價、土地拆遷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1]呂振宇,倪鵬飛.鐵路公益性:理論與經驗[J].財經問題研究,2005(10):51-56.
[2]何壁.鐵路改革模式選擇[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299-336.
[3]榮朝和.探究鐵路經濟問題[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113-118.
[4]劉擁成.加拿大和美國鐵路的公益性運輸[J].中國鐵路,2006(12):25-28.
[5]徐立凡.鐵路工程越開放越能贏得公信力[N].新京報,201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