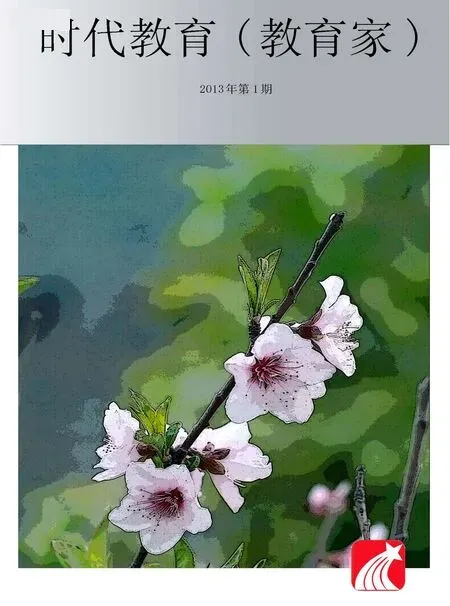來自一所中學校園體表的教育力量
本刊記者 何永志 攝影 何永志
來自一所中學校園體表的教育力量
本刊記者 何永志 攝影 何永志
深夜抵福州,海風拂面,氣溫驟降。
從機場沿西北一路上行,穿過浩蕩的閩江,橋下是馬尾。歷史教科書描繪的民族屈辱在這里已找不到,兩岸搖曳的繁華燈光、依稀可見的巨型船舶,說明這里曾經是、現在依然是中國的造船圣地。
此行的目的地——福州第一中學,從書院到全閩大學堂到省立中學,一直與中國近現代史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汽車在接近城區的地方拐了一個彎,一路難覓城市燈火。抵達閩侯的大學城福州一中新校區已近凌晨,夜幕下的校園寂靜無聲,校外感覺像鄉村,有些荒涼。
一座沒有校服的學校
清晨,和眾多學校一樣,校園廣播早早放起了叫醒音樂。
早餐時間,食堂內學生還不多,零零星星坐在餐桌前,玩著手機,安靜就餐。也有些學生,隨意買點吃的,然后轉身離開,走向教室。即便臨近上課,也少見學生成群結隊抱書奔跑,看上去,這里的學生似乎很淡定。
記者很快省悟過來,淡定的真實原因是,整個福州一中的學生都沒有穿校服,這幾乎是記者有生以來看到的唯一一座沒有校服的中學校園,恬淡皆因于此。
米歇爾·福柯在他著名的《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學校、軍隊、監獄、醫院等,是對人的身體進行規訓的重要空間,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都要求穿制服。
福柯的權力理論,至少在福州一中成了例外。自孔子始,因有教無類,中國的學校便不再有所謂“校服”。福州一中延續了這一傳統。在福州一中我們看到,有著豐厚教育傳承的中國學校可以不同于西方工業化革命以來的那種學校。事實上西方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教育體制,也在不斷改革,所謂統一校服之類,亦在改革之列。
校園一端,一路平坦的校園突然出現了一座小山坡,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松林,生長應該已多年。對于一所遷建不到10年的新校園來說,這些松林顯得過于年長了。記者最感驚訝的是三棵菩提樹,它們呈品字形栽種,移栽的痕跡還很明顯。以菩提樹作為校園景觀,殊為少見。
此時,校園鈴聲響起,下課了,寧靜的校園多了幾分生氣。
負責接待我們的鄒永春老師上完課,熱情地走來為我們當向導。雖然是學校辦公室主任,但教學任務未減。他說,福州一中從上到下,所有行政人員都要上課,校長也不例外,這是教師的本分。
見我們在菩提樹前流連,鄒老師笑了。“面前這座小山坡是建校時特意保留的,山坡上松樹共有99棵,還有一些荔枝、龍眼樹,原生多年了。至于菩提樹,是學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兩年前從深山老林里找來的,學校希望學生心境澄明而向學。”
鄒老師此言讓我們想起釋迦牟尼菩提樹下悟道、鹿野苑傳法的典故,更進一步想起孔夫子杏壇設教、刪定六經的傳統。優秀的校園,每一處景觀都應該具備教育因素,是謂“無言之教”。
極簡是錘煉的結果
除了小山坡,學校地勢平坦,建筑布局一覽無余。整個校園的中心建筑是留給學子們課外活動的科技圖書館,宿舍樓、教學樓、實驗樓等建筑體依左右展開。左側為學生生活區域宿舍、食堂、足球場、排球場、籃球場等,右側為行政樓和教學樓,在中國的古老傳統中,左為上,右為下。
雖然功能分區明顯,但一條條長長的風雨走廊又將樓宇連接在一起。建筑色調只有紅白兩色,白屋頂、紅墻面,然而幾何元素極多:細密的方格小窗,或寬或窄的外墻裝飾,高大的方形門,走廊里的長方體柱子與弧形拱門。學校的藝體館倒是一座獨立的建筑,整體呈圓形。
極簡風格是錘煉的結果。學校遷建之時,花了一年多時間與設計院反復研究方案,學校老師、各屆校友、甚至包括民國時期畢業的校友深度參與其中。在外人眼中看似簡單的紅白色調,其實寄托著廣大校友的深厚情感。因為老福州一中過去的宿舍,便是一幢紅色外墻的老樓,每當校友念及母校,都會親切地想起這座“紅樓”。在福州一中人看來,紅樓,不是單一的顏色,而是一種情感,一種傳統。
與極簡的建筑風格相輝映,福州一中的校園墻面清爽,沒有任何名人名言的裝點,也沒有我們通常會在校園里看到的鮮紅而鼓舞人心的勵志標語。至于校訓,非常低調地位于墻腳一隅。
最終,在辦公樓的一樓大廳的一個角落里,記者看到了福州一中的校史走廊。中國近代史上,一大批經歷了近現代史檢驗的文化名人與福州一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沈葆楨、嚴復、陳寶琛、陳衍、林紆、林長民……
校訓很精煉:植基立本,成德達材。這八個字承續著福州一中的歷史與辦學傳統。福州一中的前身是全閩大學堂,再往前則可追溯至書院時代,即清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創建的“鳳池”書院和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創建的“正誼”書院。1901年清政府諭旨各省要改書院、設學堂,光緒帝師陳寶琛曾賦閑在家興辦教育多年,1902年將兩所書院合并改為全閩大學堂,成為福建第一所公立學校。同時,學校也將諭旨的其他精神加以提煉、傳續,把“心術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用”作為育人目標。
最為人稱道的是福州一中的辦學宗旨“為天下人謀永福”,文句出自林覺民的《與妻書》。林覺民正是一中的校友。1902年,林覺民父親林孝穎雖無功名,其詩文卻頗受陳寶琛賞識,將他聘為全閩大學堂的國文教師,15歲的林覺民因而得以進入這所學校就讀。1907年,林覺民東渡日本,又過四年,林覺民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慷慨赴死。林覺民寫給妻子陳意映的《與妻書》因此永世流傳,被稱為千古第一情書,海峽兩岸都曾經將其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印尼、新加坡等國的華文教材中,據說也有它的位置。
把最好的留給圖書館
鄒老師說,“走,去看看我們的圖書館吧!這是學校最好的建筑,也是畢業學生記憶最深的地方。”
還在上課,圖書館并無學生。
圖書館一樓,有期刊閱覽室以及英文閱覽室。期刊閱覽室,書柜上方是陳寶琛像。書架上,除了市場上常見的一些報刊雜志之外,赫然放著《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這是一本專業性和前衛性很高的科普讀物,作者史迪芬·平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系世界公認的繼喬姆斯基之后的語言天才,對西方國家近年來的基礎教育改革具有開拓性的意義。記者也是在最近兩年才看到這部作品,而圖書館余秀菊館長告訴記者,學校在2008年就已引進此書。英文閱覽室同樣不乏英文領域的前沿期刊。福州一中的閱讀視野與品質可見一斑。
圖書館二樓是綜合閱覽室,每個書柜上,都擺放著相關的杰出校友的簡介,其中包括17位院士以及抗日空戰英雄陳盛馨烈士。余館長介紹說,這可以讓學生近距離感受榜樣的力量。綜合閱覽室的設計細致體諒。比如,文科閱覽室建成書吧形式,設有沙發卡座,學生看書累了可以在這里小睡;露天的小陽臺和樓梯轉角處,設有個性化的桌椅以方便學生閱讀;另外還辟有獨立的小房間,那是研究室,重要的套系文獻陳列其中,如《中國教育年鑒》、《中國百科大辭典》系列等,供師生開展專業研究使用。
記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走廊旁的一個露天休息區,功夫茶具、藤編桌椅、太陽傘,以及咖啡,圖書館都給學生備足了,而屋頂上蔥綠的紫藤遮擋了夏天的烈日。鄒老師介紹說,因為福州一中另一位杰出校友鄧拓一生最愛紫藤。因此,書屋名為紫藤齋。“文革”前期,鄧拓自殺以示清白,其妻子得知消息后,以一束紫藤花送別鄧拓的最后一程。鄒老師說,對面的小山坡取名鳴陽山,以后山上還將建一座紫藤書院。
圖書館三樓,是學校的第三圖書館,以福州一中1934屆旅臺老校友、國民黨中將梁孝煌的名字命名。梁先生將其百歲壽宴從簡,并將子女為其籌辦壽辰的費用、賀禮及其平生節衣縮食的積蓄共新臺幣100萬元,捐獻給母校福州一中創立圖書館。
這里不同于傳統的紙質實體圖書館,而是基于網絡虛擬世界的現代化交互式圖書館,可容納200名學生同時使用。此外,這里還開辟十個功能廳,供學生社團開展活動使用。
圖書館的網站上開辟了課程體系、博覽體系、視聽說體系、自評自測體系等模塊,豐富學生的學習資源。在課程體系中,許多校本課程的資料按照學科門類歸置,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興趣愛好進行自主學習。福州一中圖書館余秀菊館長告訴記者:“因為場地人數限制,很多學生不可能上完自己感興趣的所有課程,課程體系可以彌補這一遺憾。而在博覽體系下,由教研組推薦,學術委員會評定、審查的精品課程視頻和文字資料則是學生自主學習的良好素材。而通過分類導航條,學生也可以便捷地查詢到國內各大主流文獻網站,如中國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中國科技館、微軟百科、中國知網……
可惜,由于第三圖書館剛投入使用不久,網站課程資源還正在建設中,記者沒能看到更多的精品課程視頻。
對高中生最為實用的系統,應該是自測自評系統。教師組建題庫,學生可以根據課程進度,設置難易深淺來抽題自測,有不懂的問題還可以發征集令讓老師和同學解答。
記者在校幾日觀察,圖書館有俯看校園的最佳視線,人氣完全不是問題,尤其每天中午、傍晚時候,到圖書館坐坐,已經成為學生的習慣。
至此,學校將最好的位置留給圖書館的用意不彰而顯:讓圖書館成為一中學子記憶最深的地方。濃郁的書香,自會讓少年躁動的內心學會寧靜。圣人所謂“不言之教”的真正內涵在于:高級的教育應該是用優美的環境熏陶人,而教師們則以師德感染人,以立身為范的榜樣力量塑造人、引領人。
老校區的君子之澤
福州一中校外沒什么可逛的。不遠處,有商品房以及大學,建筑周圍均有不少荒地,雜草叢生。腳下之地,是福州大學城,距離市區15公里,于2000年前后開發修建。目前,已有12所高校入駐,包括福建師范大學、福州大學等知名院校,福州一中成為入駐大學城的唯一一所中學。
在擴招、地產經濟等諸多背景下,從中學到大學,各地名校外遷擴張已成當下中國的主流趨勢,有的甚至成為上萬人的超級中學。可少有中學像福州一中這樣,新校區不過2000人,而老校區,依然被保留著。
其實理由很簡單,圣人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福州一中近兩百年的歷史文脈里,就算近現代史上那些英烈志士們的“君子之澤”已經被斬斷了,文脈還應該續上,更不能將其物質載體拆掉。
第三天,記者來到福州一中老校區,探訪之后,為老校區能夠得以留存深感慶幸。
福州一中老校區位于東街口,福州市區最繁華的地帶,在一些“老福州”眼中,這片地帶是福州、甚至整個福建的風水寶地。
學校圍墻外的小巷子,叫三牧坊,正是福州一中校園文化的一大靈感源泉。一百米外,正誼書院的遺址還在。曾經,翻譯家林紓就讀于此。如今大門緊閉,許多人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倒是門口的一小塊空地,成了老年人健身的地方。記者端著相機對著書院不停地比劃,反而成了行人眼中的風景。
右行500米,是著名的“三坊七巷”,被稱為中國里坊文化的活化石。當然,更讓人駐足敬仰的是兩百年來在這里進進出出的人: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覺民、林徽因、謝冰心……這里也是福建辛亥革命的重要發源地,黃花崗七十二位英烈里,后來的統計表明,福建省有23名,僅次于廣東省。
據說,多年前,三牧坊與這片地帶仍然街巷相連,后來城市開發,不少街巷隨之萎縮甚至消失,得益于當地有識之士的多年呼吁,才有幸形成今日“三坊七巷”之格局。
老校區面積狹小,占地僅28畝,近千名學生只有一塊操場。盡管條件逼仄,學校還是竭盡所能,在校門一側的小樓里,建起“校史展覽室”,并聘專人管理。同時,這里還有一個校友會客廳,方便校友回校聚會。
校內多榕樹,蔥郁蒼勁,年代久遠,但教學樓看起來挺新的,外立面風格與新校區一致,校長助理陳海冰老師介紹說:“現在這里是初中部。遷建后曾短暫停辦,在2007年復辦。復辦時,建筑太陳舊了,所以統一風格重新裝修。”
可傳說中的“紅樓”呢?他指向教學樓外的工地,說到:“紅樓太陳舊了,以前拆了,我們正準備重建。”
TIPS
陳盛馨
陳盛馨為福州一中1933屆校友,芳名傳于一中校史。
陳盛馨學業優秀,為人豪爽,與同學友誼甚篤,愛好體育,民國二十一年,福州市舉行“中等以上田徑對抗運動會”,他在鐵球、鐵餅比賽中皆獲得冠軍。同時也愛好文學,曾在當時福州《民報》和《南方日報》副刊上,發表愛國詩歌、抒發慷慨熱情。
“九一八”事變后,陳盛馨萌發從軍報國的志向,高中畢業后毅然投考空軍學校。他說:“外人之敢于欺辱我國者,圖憑借海、空優勢而已”。杭州筧橋中央航校招生極為苛刻,陳憑借健壯的體魄、優異的成績,終被錄取。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陳盛馨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航空學校第四期并留校見習,同年12月1日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空軍少尉,編入被譽為“中國空軍最強勁部隊”的第四大隊第二十一分隊。
1937年松滬會戰,8月14日,日軍出動大批飛機狂轟上海、杭州等地,第四大隊選出幾位最優秀的飛行員迎敵。此役,我共擊落日機6架,我方無一傷亡。為慶祝中日首次空戰大捷,此日為中國的第一個空軍節。8月15日,在杭州“筧橋空戰”中,陳盛馨一人擊落兩架敵機,再立大功,被譽為“空戰英雄”,他的名字隨著電波傳遍大江南北。余杭縣志有詩贊曰:“百年仇恨奸飛賊,萬古春秋頌筧橋。”
1939年3月,陳被任命為第二十一大隊隊長,12月30日,桂南告急,陳盛馨率隊參加柳州空中大會戰,以擊落敵機八架而我方無一傷亡的輝煌戰果,創造了中日空戰史上我方前所未有的大捷。
1942年8月,陳盛馨犧牲于四川成都雙流機場,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