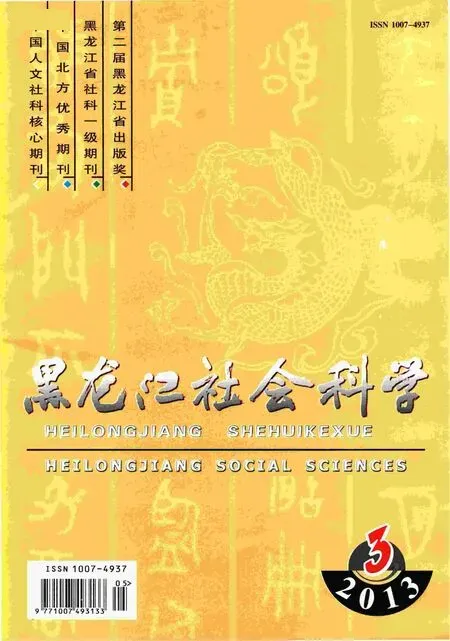論郭沫若抗戰史劇的特征及政治理念
佟 波
(延邊大學 歷史系,吉林 延邊 133002)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僑居日本的郭沫若再也不能在書屋里進行學術研究,他毅然決然“別婦拋雛”,回到祖國投入到抗戰的洪流。回國后,郭沫若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中將廳長、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炮火連天的戰斗間隙,郭沫若以筆為武器,連續創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孔雀膽》、《高漸離》等六大抗戰史劇。這些史劇都創作于1941年12月至1943年春,其時正處于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抵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為此,郭沫若創作出了具有現實針對性、政治尖銳性、鮮明時代性的抗戰史劇,并以獨特的創作手法表達了反對分裂投降、主張團結抗戰的政治理念。
一
郭沫若的抗戰史劇有著“失事求似”的創作特征。例如,歷史中的屈原是因投降賣國派權貴的迫害而被流放的,而史劇《屈原》則改為投降賣國派的代表——南后因出賣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害怕屈原反抗而施以迫害。這樣的改動使得抗戰與投降、愛國與賣國的對立矛盾更為突出。再如,歷史上的聶政是抱著“士為知己者死”的個人情感而刺殺俠累的,而《棠棣之花》中的聶政則是懷揣為國為民之心而刺殺了“勇于私斗,怯于公仇”的俠累和韓哀侯。這樣,聶政就從一個“士為知己者死”的不羈游俠變成了愛國英雄。此外,根據主題突出和劇情發展的需要,郭沫若還虛構了一些歷史人物,如“《棠棣之花》中的酒家母女、冶游男女、盲叟父女、士長、衛士之群,《信陵君》中的信陵君的母親魏太妃和侯生之女與朱亥之女,《屈原》中的嬋娟、衛士,都是于書無據的。”[1]16-17
由于當時國統區文網森嚴,動輒得咎,郭沫若不得不采用以古喻今、借古鑒今的手法對歷史重新詮釋,進而宣傳反對分裂投降、團結抗戰的時代主題。“失事求似”的創作手法志在隱喻現實、推動現實,用意與魯迅在散文中摻用雜文、小說中混合“故事新編”相近。這一特殊的文藝斗爭形式給了敵人措手不及的打擊。深感威脅的國民黨反動派急忙組織反動學者和文人歪曲、攻擊這些抗戰史劇的主題思想、創作意圖、史料運用和人物形象塑造等問題,企圖貶低抗戰史劇的價值,阻止郭沫若進行抗戰救國的政治宣傳。面對敵人的威脅與中傷,郭沫若毫不動搖。他多次在各類場合闡述自己“失事求似”的史劇創作主張,并堅持創作史劇的精神與原則。郭沫若說:“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精神。”[2]501可以說,郭沫若是以自己的史劇創作來實踐這種精神的。他那豐富的想象力,對材料的精細鉆研和對現實的深刻表現力在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更有效地闡明了“發展歷史精神”的史劇家的歷史作用。
《屈原》是郭沫若六部抗戰史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尖銳、強烈、啟蒙意識與批判精神通過神圣的儀式化的舞臺爆發出炫目的光環。《屈原》的誕生不僅僅是郭沫若的政治理想的寄托和個人情懷,更得力于那個悲壯的全民抗戰的年代。”[3]在《屈原》中,郭沫若將皖南事變后的“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里,宣揚了反對分裂投降、反對倒退的政治理念。因此,國民黨將《屈原》視為假借歷史、諷喻現實的“骨鯁”,并組織《中央周刊》、《中央日報》等報刊對《屈原》進行欲蓋彌彰的污蔑。作為反擊,共產黨則以《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為陣地竭盡全力宣傳《屈原》,還動員左翼作家和文藝界人士開設了持續半年之久的“《屈原》詩詞唱和”。國共兩黨在大后方重慶圍繞著《屈原》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政治較量,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深遠的政治影響力。以《屈原》為核心,郭沫若六大抗戰史劇在特殊的年代有效地形成了文藝斗爭的戰斗力,使敵人震驚,使革命青年振奮鼓舞。
二
郭沫若的抗戰史劇創作具有“人物形象美丑分明,善惡對立”的風格。《屈原》中的屈原、嬋娟與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瑩與俠累、韓哀侯,《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孔雀膽》中的阿蓋與車力特穆爾等人物的沖突對立,深刻揭露了反動統治者、叛徒漢奸以及侵略者貪婪狡詐、專橫兇殘、自私自利的本質,同時又有力地發掘出英雄義士的愛國情操,熱情地贊揚了他們忠貞剛直、愛國愛民、不怕犧牲、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郭沫若還有意識地讓觀眾從時代背景、人物、事件中體會到彼時與此時的對立關系,以此展示出主人公面對的斗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殘酷性。
郭沫若抗戰史劇都是以歷史上動蕩激烈的時期為背景,始終貫穿著進步與倒退兩大對立路線的激烈沖突。反動統治者為保全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個人利益,極力維護著落后的腐朽制度,他們和立足于民族前途的志士仁人之間形成了直接沖突,雙方矛盾不可調和。郭沫若的抗戰史劇把暴虐的、反人道的人和事視為“歷史的障礙物”,宣揚反暴政、反侵略、反壓迫的反抗精神以及“把人當成人”的民權思想。
郭沫若抗戰史劇圍繞邪惡與正義、侵略與反侵略以及暴政與仁政進行的描寫,無形中與抗擊侵略者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產生了內在聯系,從而使歷史事件和人物具有了某種象征性,突出了歷史與現實的相通之處。觀眾自然而然地將眼前的劇情和抗戰現實進行比較,從而引起強烈的共鳴,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的投降政策并堅定了抗日的斗志,有力地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政策,從思想上推動了正在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
三
“悲劇精神”是貫穿于郭沫若史劇創作中最為突出的寫作風格與特征。被壓迫階級對壓迫者的反抗,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都很容易遭到失敗。把這種個人的、團體的失敗史形成文章就會自然成為一篇悲劇。《屈原》中合縱輸給連橫,失去由楚人統一、由屈原的思想來統一的機會,在《虎符》里如姬竊符救趙后壯烈死去,《棠棣之花》里聶政為刺俠累而死等劇情都讓觀眾震撼。
郭沫若認為,“真正的悲劇的發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2]428他的抗戰史劇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深刻性,“體現了民族危亡、國家遭受到侵略的重大的歷史沖突,反映出了代表歷史進步的新生力量產生和壯大的‘歷史要求’,以及‘這種要求不可能實現’之間的關系,闡明了悲劇產生的必然性。”[4]50郭沫若以這種歷史觀展開了悲劇的畫幅,讓觀眾把握歷史發展趨勢,聆聽時代的呼喊。
強調悲劇必然性的郭沫若最為推崇的是社會悲劇。他的抗戰史劇全都是社會悲劇,都揭露出悲劇產生的社會根源。例如“《屈原》、《虎符》揭示的悲劇根源在于抗秦的愛國主張與腐朽的統治階級的私利之間的矛盾,《孔雀膽》揭示的悲劇根源在于阿蓋、段功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要求違背了統治階級的意愿,《南冠草》揭示的悲劇根源在于夏完淳那改變現實的努力已經難以改變時代發展的趨勢,腐朽的明王朝注定要覆滅。”[1]18抗戰歷史劇所揭示的社會根源,與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相呼應,更有效地傳播了郭沫若的政治理念,起到了啟蒙作用。
郭沫若認為,“悲劇比喜劇更具有教育意義……悲劇精神的目的正是在于號召悲壯的斗爭,它的作用是鼓舞新生的力量克服種種的困難,以爭取勝利并鞏固勝利。”[2]428而且他深信,被英雄人物的悲劇感召的觀眾在傷感之余,會把悲憤的情感轉化為斗爭的力量,更加牢固地堅定起抗戰的信念。
四
郭沫若的抗戰史劇有著“英雄主義”的特征。他曾說過“……不自欺與知恥,是勇,然是勇之初步。進而以天下為己任,為救四海同胞而殺身成仁的那樣的誠心,把自己的智能發揮到無限大。”因此,占據史劇中心的都是那些愛國豪杰、英雄志士:屈原那民族靈魂般地舍生取義,聶政、高漸離那英雄般地視死如歸,夏完淳那英雄氣概,美的化身阿蓋公主那純潔無瑕都讓觀眾無比震撼、深受鼓舞。同時,郭沫若構筑了表現英雄們的偉大痛苦和崇高精神的歷史舞臺,又加重了他們所遭遇的苦難。使英雄主義有更大的宣傳效果,讓人們被古代的英雄所感動,為今天的英雄所激勵,從內心深處認識到抗敵斗爭的正義性[4]49。
值得注意的是,深知女性對抗日巨大貢獻的郭沫若特意在劇中塑造出了為真理、為正義獻身的女豪杰的形象。例如在《虎符》里,魏王的寵妃如姬協助信陵君盜出了虎符,她本有機會逃生,卻慷慨赴死,用鮮血詮釋了生命的尊嚴與價值。在《屈原》中,郭沫若筆下的嬋娟同樣有著崇高的人格,她堅定不移地相信屈原是楚國的靈魂,她憑一弱女子之身同實力雄厚的南后、張儀等抗爭,最后從容地代替屈原去死。在《孔雀膽》中,郭沫若為了突出“民族大團結,共同對付邪惡敵人”的主題,創造出了蒙古族阿蓋公主的形象,阿蓋公主站在民族團結的立場上,與破壞團結、主張妥協的車力特穆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她的勇敢、善良、無私、無畏,使她成為真善美的化身。郭沫若筆下的英雄人物代表著歷史的進步方向,有著高尚的操守和完美的品格,在關鍵的歷史轉折時刻,為真理而舍生忘死的英雄舉動催人淚下、感人肺腑。可以說,郭沫若的抗戰史劇鮮明地彰顯了英雄主義的歷史價值。
在日本生活二十多年的郭沫若對中日之間的強弱關系有著清晰的認識。郭沫若深知,為侵華養精蓄銳幾十年的日本,其國力遠遠超出了軍閥林立、一盤散沙、工業落后的病弱中國,中國的軍事和軍事工業更不能與日本相比。中國在抗戰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全民一心、不怕犧牲、抵抗到底、至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和信念。作為一種理想、愿望和期待,郭沫若在歷史人物中尋找到了像屈原、信陵君、高漸離、夏完淳、阿蓋公主這樣能夠使人民覺醒的英雄形象,并突出了英雄人物“抵抗到底,不怕犧牲”的抗斗精神,讓他們在“最終會失敗的定局”面前逆流而上,以身死赴國難,與故國共存亡。可以說,這些英雄人物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空曠地帶充分發揮出了郭沫若的藝術才情,創造出郭沫若與理想英雄間的價值認同以及政治理念共鳴的條件。
五
郭沫若的抗戰史劇總是貫穿著把悲劇轉化為喜劇的氣勢和脈絡,有著浪漫主義的特征[5]。六大抗戰史劇都有著隱喻光明與勝利的結尾,使觀眾看到一條光明的前途,尋找到一條斗爭的道路,從心中感受到溫暖并樂于沿著英雄人物指引的道路前進,對抗戰的最后勝利充滿信心。
例如,《屈原》中的嬋娟為了能讓屈原繼續領導漢北人民斗爭,以死換取了屈原的生命,屈原于是發出了《雷電頌》那樣的吶喊:
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地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著了,都沉在夢里,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
詩與人物的完美的結合,突出了英雄人物的浪漫主義精神,更暗示了“雷”、“電”必將沖破黑暗勢力,人間即將獲得光明的美好結局。又如在《虎符》里,如姬逃離皇宮后,大量群眾自發地尋找如姬,衛士還率領群眾刺死衛士長。而“《孔雀膽》中阿蓋公主在氣絕倒地之前,還吟頌著激動人心的詩句:‘一切都過去了,讓明天清早呈現出一片干凈的世界。’”這樣的劇情安排讓觀眾在悲悼主人公不幸的同時,又看到了新的希望。雖然劇中代表著正義的力量被摧毀,但是進步力量猶如一粒正義種子,同那些英雄的言行和事跡一樣播撒于大地之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感召并鼓舞著人民不懈地進行抗戰。使觀眾不僅看到了一個在血泊和烈火中傲然屹立起來的英雄形象,而且從中感受到歷史性轉折的偉大契機。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抗戰路線的指引下,郭沫若用他戰斗的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殘忍兇惡的侵略本質,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丑惡行徑。打擊了敵人,教育了人民,鼓舞了中華民族的抗戰熱情。
[1]宋嘉楊.論郭沫若抗戰時期歷史劇的創作理念[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04,(6).
[2]郭沫若.郭沫若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3]高音.《屈原》——用戲劇構筑意識形態[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5).
[4]王文英.論郭沫若抗戰時期歷史劇的審美價值[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2).
[5]譚洛菲.抗戰時期的郭沫若[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