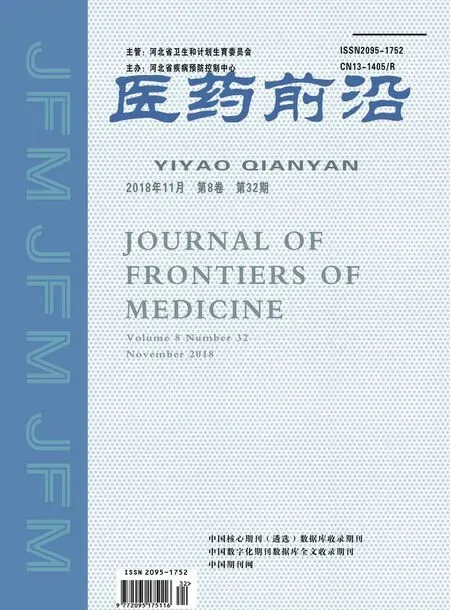優質護理在腦梗塞護理中的應用效果探究
張愛萍
(徐州市銅山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 江蘇 徐州 221006)
腦梗塞的病因是腦部供血功能出現異常,致使腦部缺氧,嚴重者伴有腦血栓、腦組織壞死等狀況發生。腦梗塞患者在發病時常常會有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癥狀,嚴重的會失去意識陷入昏迷[1]。腦梗死發病急,如果不及時進行救治,會對患者的生命健康以及生活質量造成極大的威脅,致死率、致殘率較高[2]。為了改善患者預防嚴重狀況發生,有必要在對患者進行治療的同時給予積極有效的護理。本文共納入90例患者展開分組對照研究,旨在分析優質護理對腦梗患者的護理效果,具體研究過程呈報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選取對象與資料
以入住我院的90例腦梗塞患者為對象,選取時段定于2018年1月—2018年6月。根據護理方案的不同將90例患者均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兩組。觀察組患者45例,其中男性21例、女性24例,年齡56~82歲,平均年齡69±2.12歲;對照組患者45例,其中男性30、女性15例,年齡54~80歲,平均年齡67±1.03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不大,無統計學意義(P>0.05)。入選患者已簽署協議且自愿加入。排除精神異常或無自主行事能力者,排除合并心肝腎功能不全者。
1.2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進行一般性護理,包括對患者進行用藥干預,指導患者保持合理科學的飲食搭配,保證營養搭配合理,減少脂肪的攝入量,戒掉不良嗜好等。觀察組進行優質護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內容:(1)提供良好休息環境。護理人員應該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療環境,病房內應該舒適整潔,使病人感到身心放松,可以根據病人意見設置娛樂設備,以減輕患者緊張抑郁心情,如廣播、音樂等。(2)進行健康知識宣講。護理人員定期進行健康宣講,向患者及其家屬講解腦梗塞病理以及治療的必要性、治療方法及其效果等。進行講解時應該根據患者受教育程度進行適時調整,如果患者文化水平有限,應該用通俗語言進行溝通,對患者疑問給予正確回答,對患者錯誤觀念應該給予糾正。(3)進行心理干預。患者由于罹患疾病身心都受到消極情緒困擾,同時有來自經濟以及親人人際方面壓力,難免會對生活失去信心,失去繼續生活的希望。針對這種狀況,護理人員應該與患者進行積極地溝通交流,掌握患者的心理動態變化情況,采取適當心理疏導措施平撫患者消極情緒,并安慰鼓勵患者,對患者出現的心理問題給予深層次分析以及解決,最大程度提供給患者有利幫助。(4)恢復期康復指導。護理人員應該對不同階段的病人進行針對性的康復指導,昏迷期康復指導:護理人員應該密切觀察患者狀況,定期改變患者臥位睡姿,以避免因為一種姿勢造成的患者身體出現瘡患,要經常對患者進行身體按摩,使機體保證正常運轉,血液流通順暢。穩定期康復指導:護理人員應該對處于穩定期的患者進行機體康復訓練,從簡單到復雜,一步一步,循序漸進,使得病人肢體逐漸恢復良好狀態。
1.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的康復優良率,NIHSS評分、護理滿意度。康復效果評定分為優、良、差3個等級,護理后患者生活能力得到顯著提升,精神狀態良好視為優;經護理患者生活能力有所恢復,精神狀態得到一定改善視為良;經護理患者仍無法進行簡單的生活活動,精神狀態未見好轉視為差。護理滿意度評定分為4個等級,最高分為100分,其中>90分為非常滿意;90~60:滿意;<60分:不滿意,
1.4 統計學方法
分析工具選擇SPSS22.0軟件,計數資料通過χ2檢驗,計量資料使用(±s)表示,用t進行檢驗,如果P<0.05則說明組間差異明顯符合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組間康復優良率差異分析
由表1獲知,觀察組康復優良率為97.78%,僅1例患者康復較差,較對照組生物16例,明顯要少,組間差異經χ2檢驗得出P<0.05。

表 組間康復優良率差異分析
2.2 護理前后NIHSS評分差異分析
護理前對照組患者NIHSS評分(6.2±1.3)分,護理后對照組患者NIHSS評分為:(4.9±1.6)分。觀察組患者護理前NIHSS評分為:(6.8±1.4)分,護理后NIHSS評分為:(3.0±1.4)分。兩組患者護理前NIHSS評分無明顯差異,護理后兩組患者NIHSS評分均顯著降低,且相較于護理后的對照組,觀察組患者護理后的NIHSS評分更低,組間差異經t檢得出P<0.05。
2.3 對比兩組患者護理滿意度
由表2得知,觀察組患者對護理工作均持滿意態度,而對照組中有12例患者對護理工作持不滿意態度,相較于對照組,觀察組患者護理滿意度更優(P<0.05)。

表2 組間護理滿意度差異分析
3.討論
腦梗塞有腦栓塞腔、隙性梗死等類型,是心腦血管科常見的一種疾病[3]。腦梗塞的病因是腦部供血功能出現異常,致使腦部缺氧,嚴重者會有腦血栓、腦組織壞死等狀況,腦梗塞患者在發病時常常會有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現象出現,直至失去意識陷入昏迷[4]。這種疾病通常情況下發病比較突然,如果不及時救治,會導致患者出現種種意外,嚴重時甚至會威脅到患者生命健康。同時腦梗塞會帶來很多并發癥像心率失常、糖尿病等,加劇患者身體負擔,同時給治療帶來更多麻煩。這種疾病危害嚴重往往會給患者家庭帶來極大不幸。為了改善腦梗塞患者治療后恢復效果,需要對患者進行護理,優質護理內容主要有提供良好休息環境以減輕患者緊張抑郁心情;對患者進行健康知識宣講,讓他們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疾病的產生;對患者進行心理溝通,以使患者感受到溫暖與生活的希望,盡量使患者解除心結,積極配合治療;護理人員進行恢復期康復指導以使患者機體保證正常運轉,并且肢體逐漸恢復良好狀態[5]。從本研究結果可知觀察組康復優良率為97.8%,康復較差者僅1例,較對照組中的16例明顯要少;經過優質護理后的觀察組患者NIHSS評分達到了(3.0±1.4)分,較對照組更低,且觀察組中無對護理工作持不滿意態度者,由此可見優質護理較于單純一般性護理能更有效地促進腦梗塞患者的康復,改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提高患者對護理工作的認可度。
綜上所述,腦梗塞患者護理工作中優質護理措施的開展有利于促進患者的康復,改善患者神經功能缺損,并提高患者對護理工作的滿意度,具有較高的推廣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