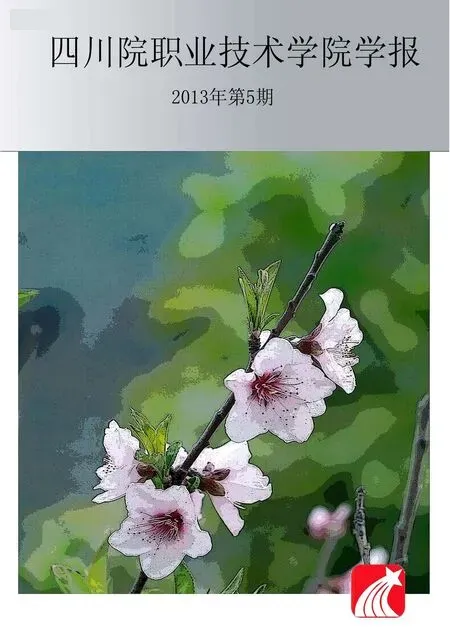朱熹善惡觀的德育內涵及現代價值
陳蘇珍
(福建師范大學,福州旗山 350108)
朱熹善惡觀的德育內涵及現代價值
陳蘇珍
(福建師范大學,福州旗山 350108)
朱熹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其道德觀與其認識論密切相連,其中關于善惡的思想認識體系豐富而深刻。從研究朱熹善惡觀的價值出發,探尋朱熹善惡觀形成的道德思想淵源,分析朱熹善惡觀的德育內涵,結合當代德育特征對朱熹善惡觀予以現代審視,力求探尋朱熹善惡觀在現代道德倫理建設和德育工作中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朱熹;善惡;德育;倫理;現代審視
朱熹理學思想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后期的官方統治思想,其道德哲學無不滲透到社會倫理和德育教化中。善惡問題不僅是德育領域涉及的最直接問題也是人類哲學史上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在儒家文化熱潮興起和當今德育工作面臨新形勢與新挑戰的情況下,研究傳統文化中朱熹善惡觀,是文化發展和德育建設過程中的必然需求,是文化進步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1 朱熹善惡觀的德育思想淵源
中國傳統思想中十分重視德育教化問題,對社會倫理道德問題的探討是一直伴隨道德倫理學的發展,其中對于人性之善惡的探討是最多的。朱熹的善惡觀并不是簡單地將人性分成善或惡,他的善惡觀貫穿了其宇宙本體論、理氣論、心性論等理論,是朱熹德育和教化思想的哲學理論依據,在中國傳統的德育觀念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的深遠。探討朱熹善惡觀形成與發展的的德育思想淵源,發掘其現代價值,發揮其合理理論內核對當今德育工作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第一,中國傳統善惡觀皆有其核心概念所在。周易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1],以“陰陽”的概念釋善,善由天道而來,由陰陽變化衍生,而終賦予人之善得以體現。儒家以“仁”釋善,仁為至善,即善的最高境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2]具有了仁也就具備了判別善與惡的能力。道家以“道”釋善,老子有言“上善若水”[3]認為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的品性一樣,滋潤萬物,自己卻不爭名奪利。周敦頤的宇宙觀涉及善惡本源的探討,以“太極”和“誠”的概念來解釋善,將善惡的產生分為三個基本過程,善惡未分之本然到善惡由分再到萬事萬物形成。張載自然哲學中將“太虛”即是“氣”作為善惡和宇宙萬物之本源。二程皆以“天理”釋善惡,朱熹延從二程“天下善惡皆天理”[4]的觀點,以“理”為核心,認為善與惡都是源于理,性在本然之狀態下并無善惡之分,“理”也是朱熹認為至善之所在。
第二,中國傳統德育觀念多通過與善惡緊密相關的社會道德表現加以闡釋。周易中對善惡的討論多與道德相關,也體現在追求內圣外王的道德修養過程中。“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5]強調個人道德的修養的重要性,即“內圣”的過程,也是自我德育教化的過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6]這是闡釋社會對個人道德與行為的要求,個人好的德行是得到社會認可與宣揚的,不好的德行也將遭受社會道德的譴責,即求“外王”的過程。內圣與外王是傳統社會德育教化的重要過程。
第三,中國傳統善惡思想中各流派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德育教化理論。周易中德育教化思想強調對善性的積累,“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7]通過善惡積累的理論來強調善性的養成,此謂積善成德。儒家的教化思想主張舉善而教、擇善而從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8]這是孔子德育教化思想體現出對善惡的揚棄。“存心養性”則是孟子在人性善的基礎上提出的,也是強調對善性的培養。荀子言“化性起偽”,“偽”指人為向善,這個觀點預設了人性為惡的前提,荀子認為人性本惡,而要不斷通過后天修養才能達到“善”。儒家德育思想的共同點都是強調自我修養以及教育引導的作用,堅持通過后天努力的不斷積累善性。
2 朱熹善惡觀的三重德育內涵
2.1 宇宙本體論角度的善惡觀
朱熹從宇宙本體論的哲學角度出發,探求關乎善惡自身的問題。朱熹善惡觀不僅以中國傳統德育教化思想為土壤,更在前人關于善惡本體的討論基礎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學善惡觀,是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內涵之一。結合理氣辯證觀點討論善惡的來源和善與惡的關系等,通過宇宙本體論角度而展開的探討是朱熹善惡理論的第一重德育內涵。
在善惡來源上,朱熹認為宇宙的本體是太極,世界萬物都由太極而生,善惡也是如此。“太極只是個一而無對者。”[9]這說明太極是絕對的至善的本體,沒有惡與之相對,是宇宙最初的狀態。本源之善乃是純然至善不與惡對,及至有惡生出乃與善相對。理乃宇宙純然至善之最高本體,是無對者。從純然至善之理,及到陰陽五行處產生了氣。天下萬物從造化天理中直接稟得的皆為善,但或過或不及便成了惡。在善與惡相互關系上,不論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還是從心性倫理角度善惡之起皆由理,理是萬物統一源頭,即至善之本體。惡在善之后由于有所偏差產生出惡來,并與善相對。在善與惡時間先后問題上善先惡后。善乃先天存在于理之中,惡則是后來衍生的。在善惡賓主問題上,善惡各自存在萬物之間,無賓主之分,這也是事物保持自身相對穩定的狀態的原因。
2.2 心性與社會倫理角度的善惡觀
朱熹善惡觀的第二重德育內涵是結合社會倫理道德而展開的,與人心、人性和社會倫理及德育準則密切相關,這與中國傳統德育觀念一樣也從社會倫理角度來結合善惡等社會行為表現來討論。這里的“心性”區別于朱熹的心性哲學,是講側重從與人心、人性和社會倫理相關的角度探求善惡。朱熹善惡哲學除了系統地圍繞宇宙本體論展開對善惡本身的討論外,對心性倫理角度善惡也有豐富的闡述。
朱熹善惡觀中關于德行的討論常結合具體社會倫理極其行為表現。首先儒家思想對于社會道德要求一向倡導孝、悌、忠、信、勇、義、禮等美好的品格。“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10]這些都是強調德育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表現,通過學、問、思、辨來擇善以為知,通過篤行加以鞏固,將善落實到具體的社會道德實踐中去。其次,“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朱熹認為以統一的道德標準來規范社會的言行,則人人恥于不善,而至于善;發揮德禮之效,則將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此乃強調發揮德育教化之潛移默化的引導人們向善的作用。再者,社會道德修養貴在長期堅持,所謂“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廢,吾弗能已矣。”[12]朱熹強調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而半涂而廢,雖然在思想上知道道德之善,而在行動上卻沒有落實到位,這也是不對的。
2.3 朱熹善惡觀與德育教化哲學
朱熹在其善惡觀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他獨具特色思想體系,為其德育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哲學基礎。朱熹善惡理論與其教化思想的相互滲透,各成體系又彼此相聯系。朱熹在他的善惡觀中論述了教化成善的可能性,而其整個德育思想理論體系又是圍繞著對“至善”的追求而展開的。朱熹善惡觀關于宇宙本體是至善的觀點為德育教化實踐提供了實現的強大理論支持。在教化過程中,朱熹認為人有辨別善惡,擇善而從的能力。“人皆可為堯舜”是其德育教化哲學的重要觀點,認為人人都夠通過提升個人自身的修養而達到善的境界。朱熹的善惡觀為其德育教化思想提出了主觀的能動因素,尤其體現在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論上。同時,德育教化在求善求圣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追求“至善”的理想目標提供了系統且明確的方法論,如致知力行,變化氣稟等都是其教化理論在求善過程中具體方法論的體現。通過德育教化使人辨別善惡,識得求善的途徑,這是朱熹善惡理論的第三重德育內涵。
3 朱熹善惡觀的現代價值審視
朱熹將宇宙本體論角度與心性倫理角度完美結合的善惡觀是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也是極其寶貴的傳統德育教化思想寶藏。其最顯著的觀點是以“理”為核心概念來闡釋善,認為萬物之善與人之善本質上是相同的。人在道德選擇中的能動作用是朱熹善惡觀獨具創造性的體現,以現代德育工作視角審視也有其特殊的價值意義。
第一,朱熹善惡觀追求道德至善之境。將宇宙本體之善惡與社會倫理之善惡貫通闡釋,理論體系完備,體現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特點。朱熹將“仁”上升到宇宙本體角度,對“仁”思想范疇的發展有突破性貢獻,將仁的德育內涵由心性論延伸至宇宙論。仁為天地生物之心,是溝通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橋梁。
第二,朱熹的善惡觀積極的德育教化態度。總體上來看朱熹的善惡觀還是屬于“性本善”的理論范疇,理是純然至善的本體,善先于惡而存在,這個理念預設著萬物本質之中必然存在著善性,重點就在于引導成善的德育實踐。這種積極的德育教化態度對現代倫理學的發展和現實社會的道德建設是有利的。
第三,朱熹的善惡觀中重視人的作用。人能“擇善而從”這是說在善惡的辨別和選擇方面人具有主觀能動性,這是德育教化能夠得以實現的重要理論依據。“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13]將道德之善通過具體的行為表現得以落實,是擇善而從的具體表現。朱熹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欲”,將人的主觀需求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也是對于德育教化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體現。
總之,現代社會過度的人欲帶來物質滿足的巨大追求極易引起忽略道德甚至違反道德的行為,德育工作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善惡標準問題成為人們所要反思的迫切問題。從社會道德建設角度講,倡導朱熹善惡觀中的合理理念有利于當前構建正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對倡導可持續的發展路線、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和道德的建設提供理論支持。朱熹善惡觀中的合理內核對于引導正確的道德價值判斷和做好新時期德育工作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朱熹善惡觀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在當今的德育工作領域仍有發揮光芒的意義。朱熹善惡觀中留給我們合理的思想寶藏仍有待進一步挖掘并為現代德育工作而服務。
[1][宋]朱熹.周易本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8.
[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69.
[3][春秋]老子,[魏]王弼注.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
[4][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64.
[5][宋]朱熹.周易本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
[6][宋]朱熹.周易本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9.
[7][宋]朱熹.周易本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173.
[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2549.
[10][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31.
[1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54.
[1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22.
[13][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31.
Moral Connotation and Modern Value of ZhuX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
CHEN Suzhen
(Moral Connotation and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Qishan Fuzhou 350108)
Zhux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s and educators in Chinese history. His morality and epistemology are closely linked, in which the idea of good and evil is deep and profound. From the study of the value of h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morality in the forming of Zhu X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 analyzes moral concept of Zhu X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moral characteristics to survey Zhu Xi’s theory on good and evil, to explore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odern ethical construc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Zhu Xi;Good and Evil;Moral Education;Ethics;Modern Survey
B82
A
1672-2094(2013)05-0019-03
責任編輯:鄧榮華
2013-08-12
陳蘇珍(1985-),女,福建閩侯人,福建師范大學軟件學院助教,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