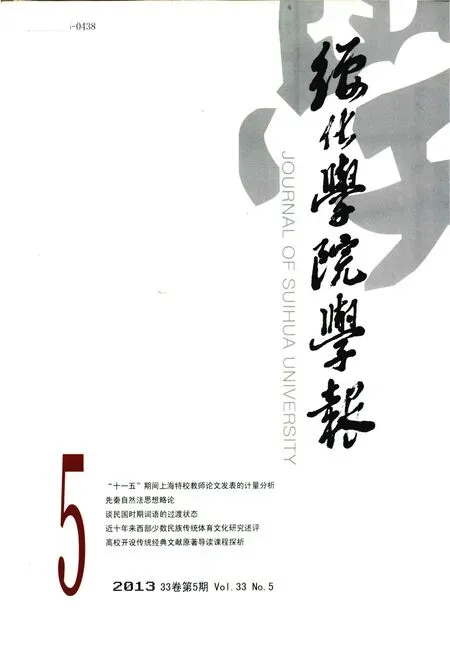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明峰《北宋經學與文學》評介
閆 薈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遼寧大連 116081)
經學曾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中國社會兩千年之久,其中蘊藏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而珍貴的史料。經學所產生的影響和理論家對其所作的闡釋貫穿中國文化的始終,這就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烙上了經學之印。而研究儒家文化與文學之關聯,第一重點是研究經學與文學之關聯。因此,進一步理清經學與文學的關系,對于我們把握文學在古代的存在形態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經學存在的兩千多年中,宋代經學的作用是突出的,是經學史上的一個高峰,這就使得宋代的文學勢必會受其影響。因此,加強作為經學史之重要一部分的宋代經學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經學的思想內涵,掌握經學對中國文學的獨特影響。高明峰副教授撰寫的《北宋經學與文學》(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就是這方面的一本專著。通觀全書,作者用獨特的視角,通過其掌握的大量北宋歷史、文化資料和查閱相關的經學史原典,對北宋經學與文學的關系做了較為詳細且有價值的探討與研究,而該探討為宋代經學與文學關系之研究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在文學與經學關系研究領域留下了嶄新的一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從中我們也感受到作者文學素養之濃厚與治學態度之嚴謹。因此汪俊先生在該書的序中寫到:“此書博考經籍,高屋建瓴,在理論上對經學與文學的關系作了總體探討和準確把握,梳理北宋一朝的經學發展脈絡,揭示其與文學發展的互動面貌和演進規律,探討了宋人經學新風對文學內容、風格、形式的影響。”這段話無疑是對全書的整體概括。總而言之,高明峰副教授在《北宋經學與文學》一書的寫作中,“為了求真而不避繁難,可見其問學之篤實”,該書也是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領域的佼佼者,值得一讀。
從具體內容來看,《北宋經學與文學》一書共分六章,按照時間的順序從中晚唐到北宋熙寧、靖康年間,詳細論述了經學與文學的密切關系。
要討論經學與文學的關系,首先要了解并掌握經學的基本含義。在第一章緒論中,作者指出所謂“經學”,指的是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包括字句的注釋、義理的闡發等。筆者認為,這一闡釋作為本書的開頭,使讀者更加明確“經學”一詞的涵義,同時也讓讀者在閱讀伊始對本文的主題“經學與文學的關系”有更加明確的理解。
隨后作者又向我們提出了談經學與文學的關聯,應當討論的三個問題:經學與文學的關系、經學與文學的關系得以實現的途徑、對經學與文學關系的基本看法與評價。通過論述,作者向我們展示了研究的客觀態度與清晰思路,而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也為下面經學與文學關系的具體研究論述做了理論鋪墊,體現出極強的邏輯性。而提到經學與文學的具體關系,書中寫道:“文學在發展過程中既受制于經學,要時常迎合經學,又不斷地發現、挖掘自身的特質,表現出對經學的疏離和突破。經學與文學這種緊密的聯系,既制約了文學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學的演進。”作者通過以上簡短的話語就對經學與文學的關系作出了明確的說明,這是作者邏輯和概括能力的體現。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經學與文學的關系簡單來說就是,二者相輔相成,可以說是既統一又對立。
研究價值是一個課題的骨力支撐,而在《北宋經學與文學》這本書中,作者認為“經學與文學的關系”這個課題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并對該價值作出了介紹:“從經學方面來說,這本身可以算是經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文學方面來看,它有助于具體、客觀地把握文學生成和演進的原生狀態,展示文學發展豐富的歷史面貌,同時也有助于深層的揭示文學理論背后的思想文化內涵,闡述文學理論的邏輯生成與變遷。從綜合研究的方面來講,它既可以豐富經學研究,有為文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對于純粹的、單一的經學研究或文學研究來說,都是一種突破。”筆者認為,作者從經學、文學與綜合研究三個方面對該課題的研究價值作出了介紹,說明該課題具有特殊的價值,而這些都是研究經學與文學關系領域中必不可少的。當然,這些價值在《北宋經學與文學》一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并成為該書的閃光點之一,因此該書有著很強的研究意義和學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僅向我們介紹了該課題的獨特價值性,還對其研究現狀進行了詳細的說明。研究過程中,作者對從“六經”誕生起至今有關經學與文學的研究現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認為宋代經學與文學的關系研究,多屬個案研討而少整體觀照。而高明峰副教授的《北宋經學與文學》就為我們彌補了這個遺憾與缺失,并為我們提供了此領域精研譚思的成果,從中可見此專著之必要性與重要性。
以上都是對“經學與文學的關系”這一課題的整體概括與論述。在第二章開始,作者進行分期論述。書中共分為四個時期:中晚唐時期;北宋慶歷以前;慶歷、熙寧間;熙寧、靖康間。作者對不同時間段的經學與文學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要討論宋代的經學與文學關系,就必須要了解掌握與之相關聯的中晚唐時期的經學與文學各自的發展及其相互關系。因此,作者在《北宋經學與文學》的第二章中探究了“安史之亂”以后在經學方面的新風及與之相關的在文學領域引起的新變。該探究為下面章節關于北宋經學與文學關系問題的展開提供了參照,也豐富了我們對存在于不盡相同的時代背景下的經學與文學之關系的認識。
高明峰副教授認為,中晚唐經學的新風與文學的新變,是當時所興盛的“儒學復興”風氣下的產物,也可看做是復興儒學的重要表現與內容。這是作者向我們介紹的中晚唐經學的新風與文學新變產生的主要因素,而這種新風、新變也相應地顯示出與該因素相符的新特點。因此,筆者認為,作者對背景、相關因素的介紹有其必要性,可見作者思路的縝密與清晰。
再者,中晚唐所體現出的經學新風主要表現于兩個方面:一是舍傳求經、以己意解經;二是原經求道、依經立義。在論述這兩方面時,作者舉啖助、趙匡《春秋》學派和韓愈、李翱等人的經學為例,通過理論聯系實例的方式,對以上兩個不同學派各自的主張進行詳細論述,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中晚唐時期經學新風所表現出的獨特性。
“這種經學新風,不僅在經學領域產生了普遍影響,也從根本上造就了文學的新變。”這是一句承上啟下的話,而作者通過這樣一句簡短的話直接將主題轉入到另一個論述內容中,從中可見作者寫作的巧妙之處。隨后,作者認為這種新變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在文學創作和批評方面,要求以“六經”為典范,要求文以明道,要求詩以諷喻,突出強調文學對現實的干預作用。二是在文學風格方面,或奇詭,或淺切,都與經學新風有著深層聯系。作者同樣結合最具代表性的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諷喻詩風展開了詳盡論述。總之,筆者認為,第二章對中晚唐經學的新風與文學的新變的論述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僅增添了本書的完整性,還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與掌握本書的主題:“北宋經學與文學的關系”。
從第三章開始,作者對本書的主要內容“北宋經學與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期而具體論述。在論述伊始,作者首先對北宋經學與文學的演進背景從經濟與政治兩個方面作了簡單的介紹。隨后,作者以“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為分界點,將北宋的經學發展大致分為如下三期:慶歷以前是過渡期,承中有變;慶歷至熙寧前,是變革期,主要功績是破漢學;熙寧以來直至北宋滅亡,是自立期,主要功績是立宋學,出現“荊公新學”、“蘇氏蜀學”、“二程洛學”等鼎足而立的學派。與此經學演變相關聯,文學的進程也顯示出相應的變遷。以上是作者對后面內容的一個概括介紹,讓讀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本書論述的整體走向。一本書的思路是否清晰是影響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高明峰副教授在本書的論述過程中對主題走向與整體思路進行了顯明的梳理介紹,這體現出作者的“問學之篤實”。
首先是北宋慶歷之際,在政風、士風和學風上都表現出過度的性質,較多地沿襲唐五代以來的陋習之風,但承繼中亦有新變的因素在內。這是對該時期政風、士風和學風整體風貌的總結,同時也引出下文對經學與文學新面貌的論述。作者認為,經學與文學也呈現出諸多相應的面貌,其主要的特征,即是均表現為守舊(因襲)與革新的并存。在論述經學方面,作者從官方組織編著或認可的經學著述和私人經學著述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其中著重介紹了以柳開、王禹為代表的,以“復興古道、古文”為任務的私人經學著述,作者通過介紹這兩個人在經學方面的重要貢獻,來進一步論述慶歷以前的經學風貌。而在文學方面,作者從詩、文、詞、賦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從而得出:這時期的總體面貌是因循守舊多于創新變革。本小節作者通過對經學、文學兩個方面在北宋慶歷之際的特點進行逐一論述,揭示出本時期經學、文學的總體面貌,可以說是由點及面,詳略得當。
作者為更好地引出下章內容,在本章結尾處留下了伏筆。作者認為:雖然在慶歷以前,經學與文學在柳開、王禹等人的努力下,已經開始表現出一些具有革新性質的特點,但遺憾的是,在當時的文壇上,緊接著出現的楊億、劉筠等人的西昆體風靡一時,柳、王等人開創的復興古道、古文的運動,限于才力,不能夠徹底的扭轉局面。以古文取代駢儷之文,這樣的任務只能由后面的人來完成了。筆者認為,這一段話的論述,勾起了讀者的好奇之心,自然而然將讀者是視線引入到下一章節中,為后文作了鋪墊。同時,這一寫法也增添了全書的流暢性,增強了全書的邏輯性。
值得慶幸的是,像歐陽修這樣的后來人并沒有讓前人失望,他們在繼承前人遺產的基礎上進行不斷革新,體現出一定的進步性。作者在文中指出,慶歷、熙寧間的經學,其特點在較為徹底地“破”漢學,而慶歷以來的經學新變,其主要方面在于疑傳惑經的盛行和通經致用的取向。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突出代表是有“宋初三先生”之稱的胡瑗、孫復、石介三人所身體力行并通過教學而廣為傳布的“明體達用”之學。
沿著“宋初三先生”開辟的路徑,慶歷以來的經學面貌豁然一變。當然,其主要方面是前邊已提到的疑傳惑經的盛行和通經致用的取向。作者對這兩個方面內容分別列舉出了其代表作品與人物,前者是劉敞的《七經小傳》,而后者是以李覯為代表。就慶歷、熙寧間的“疑傳惑經”來說,是由歐陽修導之于前,劉敞承之于后,而就實際成績和影響來說,則劉敞似更值得注意,這或許也是作者選劉敞作為其代表的主要原因。而在慶歷之際,范仲淹等人掀起一股改革之風,終于形成“慶歷新政”這一高潮。與現實變革有關的是,在經學領域也呈現出強烈的通經致用,以經學干預政治、服務政治的色彩。這種取向最為突出的代表是李覯及其《周禮致太平論》。通過作者的具體分析,我們足以了解當時學者們通經致用的情況。
經學面貌的新變也滲透到了文學的領域中,促進了這一時期文學面貌的新變。簡要地講,慶歷、熙寧間的文學是初步奠定了宋代一朝之文學的面貌,體現出了宋代文學自身的諸多特征。而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歐陽修、尹師魯兄弟、蘇舜欽、梅堯臣等。在書中,作者通過對這些人在古文、詩歌兩方面的主要成就作詳細的分析,揭示出這時期的文學新面貌:力行古文、以文為詩。隨后又向我們介紹了產生這種文學新面貌的現實背景。通過介紹,我們可以得知,這時期的文學面貌是與當時的經學新風密切相關的。經學新風影響了文學的內容、風格與體式。除此之外,作者還對慶歷、熙寧間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的經學與文學做了單獨的討論,這樣既有助于較好地把握歐陽修的文學風貌和學術成就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看做是研究慶歷、熙寧間經學與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富有代表性的個案。
到熙寧、靖康年間,經學是沿著前人開辟的路徑繼續推進的。在本章節的開始部分,作者就向我們指出了熙寧、靖康年間的經學實績和文學面貌。本時期的經學除了在疑傳惑經和經世致用方面更推進一步之外,在性命之辨方面也開始重視起來,而這兩個方面,正是此期經學的主要內容。能夠體現以上經學內容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自我樹立,自成一派,分別形成了所謂的“荊公新學”、“濂洛理學”、“蘇氏蜀學”等。這些自我樹立的、獨重義理的經學流派,構成了熙寧、靖康間經學的總成績。而這時期的文學面貌也呈現出與學術相應的特色。換句話說,就是一派有一派之文學,而這樣各自成派的文學,即組成了當時文壇的基本面貌和整體走向。這些具體展示了經學與文學的聯接,但這種聯接也受到了社會環境的諸多制約,主要表現于紛繁復雜的黨爭和改弦更張的科舉兩方面。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作者又分設荊公新學與文學、蘇氏蜀學與文學、二程洛學與文學三節,進行具體而深入的個案研討,評述其經學成就與特點,掘發其經學與文學的內在關聯。這些論述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王安石、蘇軾等人的學術建樹,更能深化我們對其文學特質的理解。
就本書的論述方法來看,作者為了讓讀者更加明確的了解所論述的內容,皆以理論聯合實例的方式進行討論研究,避免了一味的理論論述引起的枯燥乏味,增添了本書的趣味性和論證的說服力。除此之外,文獻基礎的扎實、研究視野的開闊也都為本書增色不少。
總體而言,高明峰副教授《北宋經學與文學》一書,緊扣經學與文學二者,點面結合、時空交織、勾勒與分析并舉、宏觀與微觀互證,既展示出北宋經學與文學的互動演進,又闡述了北宋經學與文學互動中的諸如制約因素、邏輯成因、主要途徑等重要命題。大體實現了作者“在整體上既做到豐富經學史的研究,又為文學史的研究開辟新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