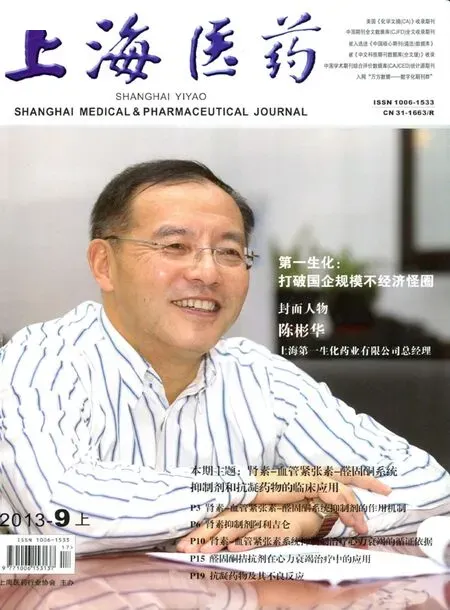溶栓合并丹參酮IIA對(duì)30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治療的臨床觀察
王小沙
(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西苑醫(yī)院神經(jīng)二科 北京 100091)
近年來,溶栓療法已經(jīng)成為治療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最有前途的方法之一。動(dòng)脈內(nèi)介入溶栓以其較高的再通率和良好的療效,已越來越得到了廣大臨床醫(yī)師的認(rèn)同,并使越來越多的患者受益[1-2]。在動(dòng)脈介入溶栓的同時(shí)合并運(yùn)用丹參酮IIA磺酸鈉注射液,不僅能提高療效并能減少并發(fā)癥的產(chǎn)生,促進(jìn)神經(jīng)功能的恢復(fù),改善預(yù)后。本文總結(jié)了30例局部動(dòng)脈介入溶栓合并丹參酮IIA磺酸鈉注射液聯(lián)合治療急性頸內(nèi)動(dòng)脈系統(tǒng)缺血性卒中的臨床觀察,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標(biāo)準(zhǔn)
參照《介入神經(jīng)放射診斷治療規(guī)范》[3]和《中國腦血管病防治指南》,制定入選及排除標(biāo)準(zhǔn)。入選標(biāo)準(zhǔn):①年齡80歲以下,②發(fā)病6 h以內(nèi),③神經(jīng)系統(tǒng)體征符合頸動(dòng)脈系統(tǒng)缺血表現(xiàn)并持續(xù)加重1 h以上,④頭顱CT無低密度影及排除腦出血和大面積腦梗死,⑤無動(dòng)脈內(nèi)溶栓的禁忌癥,⑥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有出血傾向,②嚴(yán)重心肝腎功能障礙或衰竭,③治療前收縮壓大于160 mmHg或舒張壓大于95 mmHg。
結(jié)合以上標(biāo)準(zhǔn),接診患者后除做詳細(xì)而標(biāo)準(zhǔn)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檢查外,均于術(shù)前行頭顱CT掃描、心電圖、血常規(guī)、凝血功能、肝腎功能、血糖和電解質(zhì)等檢查。
1.2 一般資料
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因急性頸內(nèi)動(dòng)脈系統(tǒng)缺血性卒中,在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西苑醫(yī)院神經(jīng)二科行動(dòng)脈內(nèi)介入溶栓及合并中藥治療的患者共30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10例,年齡 44~80歲。
1.3 臨床表現(xiàn)
全部30例患者均伴有肢體癱瘓,溶栓前肌力在0~3級(jí),其中伴意識(shí)障礙7 例(昏迷1 例,昏睡 1例,嗜睡 5例),失語10例。伴高血壓病20例 ,糖尿病12例,高血脂16例,房顫4例。
1.4 治療方法
術(shù)前常規(guī)準(zhǔn)備后(備皮、碘過敏試驗(yàn),不配合者置導(dǎo)尿管等),平臥于手術(shù)床。利多卡因局麻后,行股動(dòng)脈Seldinger穿刺,成功后置6F鞘管,全身肝素化。首先行弓上大血管造影,并分別做雙側(cè)頸動(dòng)脈及顱內(nèi)段、雙側(cè)椎動(dòng)脈造影,盡快找出“責(zé)任血管”并了解側(cè)枝循環(huán)情況。若發(fā)現(xiàn)血管堵塞則換微導(dǎo)管在微導(dǎo)絲引導(dǎo)下,置于血栓遠(yuǎn)端再行超選動(dòng)脈造影,以了解遠(yuǎn)端血管情況。經(jīng)微導(dǎo)管于血栓遠(yuǎn)端5 min內(nèi)推入生理鹽水10 ml+丹參酮ⅡA磺酸鈉20 mg后,將微導(dǎo)管置于血栓內(nèi)部或近端,于30 min內(nèi)手推或泵入尿激酶50萬~100萬單位,再行超選血管造影。若仍未見血管再通可追加尿激酶,但最大不超過150萬單位。若術(shù)中未發(fā)現(xiàn)血管狹窄或堵塞,根據(jù)臨床表現(xiàn),在癥狀對(duì)側(cè)頸內(nèi)動(dòng)脈手推或泵入尿激酶100萬~150萬單位。溶栓手術(shù)結(jié)束時(shí)再復(fù)查腦血管造影。術(shù)后留置動(dòng)脈鞘管4 h后拔鞘。
術(shù)中及術(shù)后全程監(jiān)測心電、血壓、呼吸、血氧至術(shù)后3~7 d。術(shù)后24 h、7 d復(fù)查頭顱CT。術(shù)后24 h后口服阿司匹林,并繼續(xù)靜脈點(diǎn)滴丹參酮ⅡA磺酸鈉60 mg/d共14 d,并根據(jù)病情予以降壓、脫水、改善腦灌注等治療。尤其注意控制血壓在150/90 mmHg以下 。術(shù)后監(jiān)測凝血功能、肝腎功能等變化,常規(guī)查血脂、C反應(yīng)蛋白、血管炎性介質(zhì)、第二聚體等。于術(shù)前、術(shù)后6 h、24 h、7 d、1個(gè)月、3個(gè)月分別行NHISS及Barthel指數(shù)評(píng)定。
2 結(jié)果
2.1 血管閉塞情況
全部30例患者,腦血管造影未見明顯異常(或未發(fā)現(xiàn)責(zé)任血管者)7例,有腦血管閉塞23例。其中頸總動(dòng)脈閉塞1例,發(fā)生于伴有房顫患者,考慮為心臟附壁血栓脫落栓塞所致;頸內(nèi)動(dòng)脈閉塞7例;大腦中動(dòng)脈及分支閉塞13例,大腦前動(dòng)脈閉塞2例。
2.2 血管再通情況
1例頸總動(dòng)脈閉塞者局部再通,但栓子移動(dòng)至遠(yuǎn)端頸內(nèi)動(dòng)脈未能再通;7例頸內(nèi)動(dòng)脈閉塞者,完全再通2例(28.57%),部分再通3例(42.85%),2例未通;13例大腦中動(dòng)脈閉塞者再通或部分再通者9例(69.23%);2例大腦前動(dòng)脈閉塞者再通或部分再通2例(100%)。血管再通評(píng)價(jià)用TIMI灌注分級(jí)法: 0分,完全閉塞 ;1分,極少灌注;2分,部分灌注;3分,完全灌注。其中無再通為TIMI 0~1級(jí);部分再通為TIMI 2級(jí);完全再通為TIMI 3級(jí)。
2.3 臨床恢復(fù)情況
臨床癥狀完全恢復(fù)或有明顯好轉(zhuǎn)19例(63.33%);癥狀無好轉(zhuǎn)6例(20%);死亡1例(3.3%),為頸總動(dòng)脈閉塞溶栓后栓子移動(dòng)至遠(yuǎn)端頸內(nèi)動(dòng)脈未能再通,于48 h腦疝。臨床癥狀完全恢復(fù)或有明顯好轉(zhuǎn)是指溶栓治療過程中意識(shí)程度轉(zhuǎn)清,肢體癱瘓肌力提高2級(jí)以上。
2.4 溶栓并發(fā)癥
30例中僅1例發(fā)生無癥狀腦出血(表現(xiàn)為頭顱CT小片狀滲血),牙齦出血3例。
2.5 CT情況
30例患者均進(jìn)行了頭顱CT復(fù)查,其中3例為大面積腦梗死;11例出現(xiàn)新的小梗死灶;16例無變化。
3 討論
急性缺血性卒中是由于腦動(dòng)脈內(nèi)血栓形成、栓子脫落阻塞腦動(dòng)脈或血流動(dòng)力學(xué)改變,導(dǎo)致供血區(qū)域血供減少,相應(yīng)部位腦細(xì)胞缺血缺氧而壞死。缺血半暗帶的存在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溶栓治療的理論基礎(chǔ)。早期溶栓的目的就是挽救缺血半暗帶部分殘留的可逆性神經(jīng)元和腦組織。頸動(dòng)脈系統(tǒng)缺血性卒中的溶栓時(shí)間窗已得到理論和實(shí)踐的認(rèn)可。故本研究的病例選擇均為6 h內(nèi)的患者。然而,對(duì)于某些剛一開始臨床癥狀較輕的患者,初期肢體癱瘓程度較輕,也應(yīng)該積極做溶栓的術(shù)前準(zhǔn)備。因?yàn)槟承┻M(jìn)展型的卒中患者病情呈持續(xù)加重過程,稍許的遲疑將直接影響到溶栓的療效。
動(dòng)脈介入溶栓能借助數(shù)字減影放射技術(shù),直接了解腦血管的影像,發(fā)現(xiàn)閉塞的腦動(dòng)脈,并能同時(shí)評(píng)價(jià)側(cè)枝循環(huán)。直接在血栓部位給予溶栓劑及藥物,局部藥物濃度較高,加上微導(dǎo)絲的局部機(jī)械作用及微導(dǎo)管藥流的刺激作用,均有助于使血栓得到機(jī)械性的破碎,從而提高溶栓的療效。介入下腦動(dòng)脈溶栓這一技術(shù)已被越來越多的神經(jīng)內(nèi)外科醫(yī)師及介入醫(yī)師所掌握,已成為治療缺血性腦卒中的最有前途的治療方法[1-2]。
本報(bào)告30例急性頸動(dòng)脈缺血性卒中病例,有7例未見到閉塞的責(zé)任血管,可能是由于某些穿支血管內(nèi)微小血栓形成而不能被血管造影所分辨。如豆紋動(dòng)脈的血栓直接影響基底節(jié)的供血,雖然腦血管造影圖像上大血管主干通暢,見不到所謂閉塞的責(zé)任血管,但不及時(shí)溶栓,肢體癱瘓程度亦相當(dāng)嚴(yán)重。故我們建議應(yīng)根據(jù)相應(yīng)的臨床表現(xiàn),在相應(yīng)的血管區(qū)域溶栓。
本報(bào)告7例頸內(nèi)動(dòng)脈閉塞病例,有2例未溶通,其中1例死于大面積腦梗死后的腦疝。而其余3例也是部分溶通,造影時(shí)均可見局部頸動(dòng)脈高度狹窄。由此可見在頸動(dòng)脈硬化斑塊的基礎(chǔ)上,局部血栓形成是頸動(dòng)脈急性閉塞的主要原因,其溶栓效果欠佳。急性期可考慮同時(shí)局部支架植入,但也要考慮到此時(shí)過度灌注的風(fēng)險(xiǎn)。值得今后探討和驗(yàn)證。
本報(bào)告30例急性頸動(dòng)脈缺血性卒中病例,僅1例出現(xiàn)非癥狀性腦滲血。其出血并發(fā)癥遠(yuǎn)遠(yuǎn)低于有關(guān)報(bào)道。我們認(rèn)為與溶栓前后的中藥丹參酮給予有關(guān)[4]。
此組研究我們均在導(dǎo)管溶栓前予丹參酮ⅡA磺酸鈉局部動(dòng)脈給藥,并此后持續(xù)2周靜脈點(diǎn)滴。有關(guān)研究已表明溶栓存在再灌注損傷、出血等并發(fā)癥,同時(shí)亦存在溶栓后再梗死等。而缺血再灌注損傷的發(fā)生主要有自由基、鈣超載、興奮性氨基酸、炎性因子釋放等多種因素。如何使用腦保護(hù)劑來減輕再灌注損傷、增強(qiáng)神經(jīng)細(xì)胞對(duì)缺血缺氧的耐受力一直是目前研究的熱門課題。
中藥對(duì)溶栓后再灌注損傷有獨(dú)特優(yōu)勢。研究發(fā)現(xiàn)丹參酮ⅡA磺酸鈉不僅能直接增加缺血側(cè)大腦中動(dòng)脈血流量,對(duì)于腦缺血再灌注損傷能減輕鈣超載、抑制缺血損傷灶的炎癥反應(yīng)及神經(jīng)元壞死,清除多種氧自由基、抑制興奮性氨基酸、降低一氧化氮的毒性以及使腦缺血再灌注c-fos基因下調(diào)等多種作用,而且不受治療時(shí)間窗的約束。表明丹參對(duì)缺血性腦損傷有良好的神經(jīng)保護(hù)作用,并有較寬的時(shí)間窗[5-7]。
另外,嚴(yán)格控制血壓(溶栓前后血壓應(yīng)控制在150~160/90~100 mmHg),也是降低溶栓后腦出血并發(fā)癥的有效措施之一。所謂靠提高血壓而維持腦灌注壓,對(duì)于血管已經(jīng)閉塞的壞死區(qū)域腦組織及缺血半暗帶來說風(fēng)險(xiǎn)巨大,為灌注壓而冒腦出血的風(fēng)險(xiǎn)是得不償失的。從事急性腦血管病溶栓的臨床醫(yī)師應(yīng)從臨床實(shí)踐中細(xì)心體會(huì),根據(jù)患者的具體情況而掌握最佳的血壓值,即在腦灌注壓和出血風(fēng)險(xiǎn)中找到最佳契合點(diǎn)。
總之,動(dòng)脈介入溶栓結(jié)合中藥丹參酮ⅡA磺酸鈉治療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安全有效,能明顯減少再灌注損傷而使腦出血風(fēng)險(xiǎn)降至最低,值得臨床進(jìn)一步研究。
[1] del Zoppo GJ, Higashida RT, Furlan AJ, et al. Proact: a phase II randomized trial of reco-mbinant pro-urokinase by direct arterial delivery in acute middlecerebral artery stroke: PROACT investigators: Prolyse in acutecerebral thromboembolism[J]. Stroke, 1998, 29(1): 4 - 11.
[2] Furlan A. Intra-arterial prourokinase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the PROACT II Stud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rolyse inacute cerebral thromboembolism[J]. JAMA, 1999,282(21): 2003 -2011.
[3] 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神經(jīng)外科分會(huì). 介入神經(jīng)放射診斷治療規(guī)范I(修訂稿) [J]. 中國腦血管病, 2005, 2(8): 381-384.
[4] 金征宇, 張青, 黃一寧, 等. 急診動(dòng)脈內(nèi)溶栓治療急性缺血性腦梗死[J]. 中華放射學(xué), 2002, 36(8): 720-726.
[5] 葉農(nóng)彬, 奚濤, 陳峰, 等. 丹參酮Ⅱa磺酸鈉對(duì)大鼠局灶性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保護(hù)作用[J]. 中國藥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 35(3): 267-270.
[6] 黑明燕, 殷萍, 曠壽金. 丹參酮Ⅱa對(duì)缺氧缺血新生大鼠腦細(xì)胞內(nèi)游離鈣的影響[J]. 醫(yī)學(xué)臨床研究, 2004, 21(8):876-878.
[7] 王金華, 劉佩芳. 丹參酮ⅡA對(duì)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神經(jīng)元L-型鈣通道表達(dá)的影響[J]. 中國中醫(yī)藥科, 2008,15(6): 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