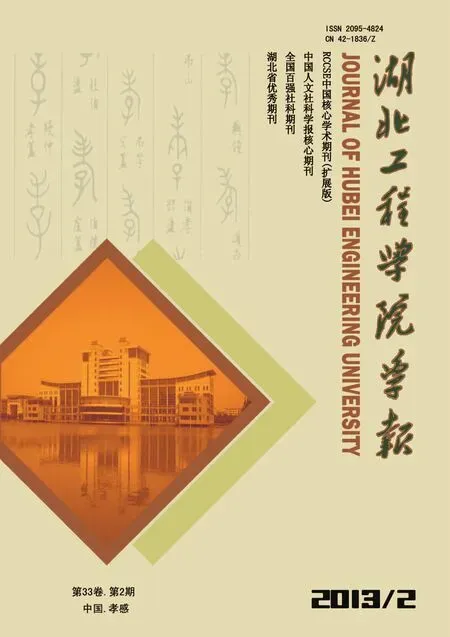論英國憲章派詩歌中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變化
肖四新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憲章派詩歌內容上突出的特點,在于描寫了工人階級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過程。而這一過程其實就是工人階級挖掘自身主體性、自我確證的過程。工人階級從自身處境出發,認識到了自己在社會歷史中的客體地位,形成了群體的自我意識,并通過經濟斗爭、政治改革、社會革命等一系列實踐活動以確立自己的主體性。
主體性是“主體所潛在地具有并且能夠發揮出來的屬性”[1]。這一屬性,需要在主體與對象的關系中顯現出來。它既包括對外在世界不適應的感覺,也包括通過維持與對象的關系,確立其主體地位的傾向,還包括自覺地改造對象,使對象主體化的傾向。從工人階級主體性覺醒這一角度,可以將憲章派詩歌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1842年之前的詩歌屬于早期創作,1843-1847年間的詩歌屬于中期創作,而1848年之后的詩歌屬于晚期創作。三個時期的詩歌創作,明顯體現出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變化。
早期詩歌的主要內容是描寫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萌芽。工人階級從自身的生存處境出發,認識到貧窮的根源,具有了階級對立觀念,并反抗自身的處境與階級壓迫,以罷工的形式進行爭取以普選權為中心的斗爭,初步具有了階級意識。這其實是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覺醒。工人階級認識到了自己在社會歷史中的客體地位,與壓迫階級形成了對立關系,并希望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只是憲章派文學中的主體,不是以個體而是以整體的形式出現的,對象不是自然界而是社會歷史中的另外的群體,于是主體性以階級意識的形式呈現出來。
早期詩歌多描寫工人的生存處境。在200多首“憲章派詩歌”中[注]詩歌主要來源于皮特·謝克納編選的《憲章派詩歌選》,其中收錄了 220多首詩歌。見Peter Scheckner(ed.).An Anthology of Chartist Poetry:Poetry of the the British Working,1830s-1850s.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P,1989.,早期詩歌約占三分之一,而直接反映工人生存狀況的就有30首左右。如西姆的《勞工歌》(1940年),描寫了工人們整天苦役般的勞作但最后一無所獲的現實。他們“從一線曙光干到天暗”,織造出的“最貴重的金色禮服,最華麗的絲綢”,卻被那些合法的強盜小偷掠走,自己卻“衣服破爛,面包不足”,居住在矮小的茅屋中,冬天凍得“瑟瑟發抖”。
表面上看,它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描寫工人生活的民主主義詩歌沒有多大區別,表達的是對工人悲慘遭遇的同情。但事實上,它們之間有本質的不同。比如布萊克《掃煙囪的孩子》(1789年)、雪萊的《給英國人民之歌》(1819年)等,都是描寫工人悲慘遭遇的詩歌。但這些詩歌僅僅只是對工人個體生活處境的經驗性描述,沒有體現出工人階級整體的生存狀況。詩歌中的工人形象,也僅僅只是讓人同情與憐憫的弱者,并沒有形成超越具體經濟結構的自覺意識。更不可能具有階級意識,因為工人階級盡管作為一個階級已經出現,但社會中還存在著不同的等級與階層,社會結構也還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階段,他們還無法從整體上把握自己作為社會的存在。
即使與同時代民主主義詩人們描寫工人生存狀況的作品相比,憲章派詩歌也存在很大不同。比如胡德的《襯衫之歌》(1844年),描寫了織工繁重單調的勞動和惡劣的生存環境。她們整天“干呀!干呀!干呀!直干到頭昏腦痛;干呀!干呀!干呀!直干到兩眼朦朧”,但“老天爺啊,糧食如此昂貴,我們的血肉這樣低廉”。詩歌也描寫了女工對美好生活——陽光、綠草、鮮花的渴望,但這并不是希望把握自己命運的主體性的覺醒,而只是希望這吟唱貧窮、饑餓、骯臟、疾病的歌聲,能“傳到富人的耳中”,求他們發發慈悲之心。正如恩格斯所說,這是一首“使資產階級女郎們流了不少憐憫的但毫無用處的眼淚”[2]的詩歌。
相比之下,憲章派詩歌不是從工人個體,而是從整體上把握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存在的。憲章派詩歌中的工人,幾乎都是以整體形象出現的。早期的70多首詩歌中,直接以工人階級整體為敘述主體的占一半以上。其他有些詩歌,盡管表面上描寫的是個體的生存遭遇與情感,而實際上所表達的仍然是工人階級整體的遭遇與情感。整體的自我意識,是階級意識形成的端倪,也促使主體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憲章派詩歌也描寫工人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并不是單純展示苦難,乞求憐憫與同情,而重在挖掘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早期詩歌在展示苦難的同時,總是要尋找苦難的根源。比如《勞工歌》就指出,工人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果實被“那些合法的強盜小偷掠走了”。在地西的《壓迫》(1842年)中,我們看到工人階級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冷酷的權貴豪紳的侮弄”和“不義橫行”。
對貧窮根源的認識,使工人階級有了階級對立觀點。在林頓的組詩《無選舉權之歌》(1839年)中,工人形象與資產者、地主、貴族的形象,總是以利益對立的“我們”與“你們”的形式出現。在山基的《歌》(1840年)中,“國王、貴族、豪富”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在瓦特金斯的《谷物稅和移民》(1842年)中,我們看到,工人階級認識到“老爺們”的享受——“大廈和高樓,珠寶,舞會,酒肴”,是靠勞動者“光屁股、餓肚皮”來實現的。
階級對立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還體現在文化教育、法律、選舉等各種權利上。比如女工斯泰利布里奇在一首詩中,就比較了兩個階級的不同命運。工廠主的妻子與女兒不僅可以穿綾羅綢緞,還可以接受教育;而女工們則既沒有金錢,也沒有時間去接受教育[3]。
階級對立導致了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意識中具有了反抗性。早期詩歌幾乎都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性。在艾夫的《萬眾一心》(1842年)中,工人階級決心萬眾一心,奮勇向前,去“粉碎那萬惡暴君的奴役”,去“爭取做人的權利”。吉爾在《歌》(1842年)中引用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展示了工人階級“奮力把暴君從寶座推下,好讓自由升上來代替它”的自覺意識與反抗意識。在《勞工歌》的結尾,西姆寫到:
唱吧,兄弟們,我但愿聽到
你們的歌曲嘹亮豪放,
因為唯有渴望自由的心靈
才能這樣豪放地歌唱!
你們快快唱起壓迫者的挽歌,
快快大聲地敲起喪鐘,
葬送公開的掠奪和朝旨王命,
這曲調才配你們歌詠。
在另一首名為《壓迫》的詩中,作者地·西連用五個反問,確立起被壓迫者“做人的尊嚴在心中閃光”的自覺意識,并進一步產生“必須解放,一定解放”的反抗意識:
難道我們永遠得忍受
冷酷的權貴豪紳的侮弄?
難道我們永遠做臟品,
供那些貪婪荒淫者享用?
眼看著不義橫行,白勞動,
心里憂傷而態度從容?
……
別讓我們這樣,
做人的尊嚴在心中閃光,
正義在要求,自由在吶喊:
必須解放!必須解放!
表面上看,這些詩歌所體現的是詩人主體性的覺醒,不能算是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覺醒。但因為憲章派詩歌的作者無一例外的是工人和憲章運動者,所以這些作者基本可以代表工人階級。
但早期詩歌中工人階級的主體意識還十分有限。盡管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與對象的對立關系,但對象的概念還比較模糊。在他們筆下,對象不僅包括資產階級,還包括地主、貪官甚至惡霸、無賴。多數人還不明白階級對立的根源,即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受壓迫和剝削。盡管他們已經有了反抗意識,但主要還囿于經濟層面,反抗也多停留在抽象的抗議上。即對社會現存制度還存有幻想,希望通過“人民憲章”的實現,改變自己惡劣的生存環境。比如無名氏的《歌》(1840年)中,一再呼吁“憲章萬歲”;本斯在《致投我于獄中的官吏們》(1840年)、《憲章主義者母親的歌》(1840年)、《賜給我們每日的口糧》(1840年)等詩歌中,認為“憲章是我心愛的東西”,為了憲章的實現,不怕坐牢甚至殺頭;米德在《憲章派之歌》(1841年)中認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就靠這光榮的憲章”,呼吁人們緊緊團結在憲章的周圍,去“要求自由人的權利”;艾夫在《致威爾斯憲章派》(1842年)、《萬眾一心》等詩歌中,呼吁人們“展開憲章主義的大旗”。可以說,早期詩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將改變工人命運的希望,寄托在“人民憲章”的實現上。
中期詩歌大約70首左右,產生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請愿失敗之后。兩次斗爭的失敗,使工人階級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利益,具有了政治獨立性。中期詩歌中,工人階級的主體意識進一步增強。這主要體現在,工人階級對壓迫階級的概念更清晰了,明確把對象界定為資產階級。并且通過對資產階級本質的揭露,弄清楚了自身受壓迫剝削的根源,并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在社會勞動過程中的物化地位,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他們希望通過政治斗爭,保障自己的權利。如果說早期詩歌中的工人階級作為主體,更多關注主體自身的生存狀況的話,那么中期詩歌中工人階級,更多關注的是對象——資產階級的屬性,以及自己與對象的關系。他們認識到自己只是對象謀取利潤的手段,但他們希望通過與對象在互為目的的關系中確立自身的主體性。
這一時期的詩歌,很大一部分是描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工人階級認識到,資產階級的財富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比如在《蒸汽王》(1843年)中,米德將蒸汽機比做工廠主的巨臂,它在主人的指使下,“把千百萬工人治死……拿小孩當食品充饑……把工人的血液變成黃金”。而驕橫的工廠主,壟斷一切天生的權利,無視工人的瘦骨嶙峋,“大口吞咽人血和黃金”,驕橫無道,尋歡作樂。在《憲章派之歌》(1846年)中,瓊斯指出,那些所謂的棉紗大王、小麥大王,正是“仗著紡織機和田地謀生”。
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剝削工人的勞動成果,是因為他們手中握有先進的生產工具。而這些先進的生產工具,是他們通過卑鄙手段得來的。林頓在《工人和利潤》(1847年)中,就揭露了竊取別人發明成果而暴富的阿克拉特、皮爾、柯布登等人的丑惡嘴臉。他們的“光景過得真美好……在財富中打滾,錢多得花費不了”,而真正的發明者哈格里夫、皮爾、柯布登等則“孤零零的死掉”,甚至“白白餓死掉”。工業革命的成果被他們無恥地占有,用來作為剝削工人的工具。他們又通過剝削得來的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宰。在《黃金大王歌》(1845年)中,艾伯納叟模仿“黃金大王”的口吻,描繪了資本統治一切的社會現實:
我們的奴隸數不清,
我們的權力無止境,
別人的死活我們定,
我們出租,創造,殺人。
……
什么地方有生命,
黃金大王是主宰。
資產階級不僅享用“千萬人呻吟著做工”的成果,而且還通過資本占有,獲得話語權,將物化現象轉化為社會生活中的每一種表現形式,特別是生成有利于資本統治的國家形式和法律制度,將剝削制度合法化,名正言順地統治他人。1846年工廠主操縱議會廢除“谷物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林頓在《工人和利潤》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工廠主以合法的手段“再壓低工資”,其結果是“商業的利潤猛漲又飛升,自由貿易真繁榮”,而“每日里餓死勞工”。
工人階級也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在社會勞動過程中的物化地位,看清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在《工廠城》(1847年)中,瓊斯描寫了工人在大生產流水線上緊張勞動的場面,飛轉的車輪就是“當今的刑臺”,“血肉和鋼鐵進行殊死戰”,工人的“生命之線飛快地斷掉”了。而在工廠主眼中,工人只是能產生利潤的機器。辛勤勞作的工人,最后一無所獲,成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物化的階級:
機器飛旋,老板發財,
鋼鐵發出保衛的光芒;
工人雙手所創的財富,
卻被自己的敵人花光。
工人階級認識到,要獲得解放,就必須改變與對象的關系。第二次請愿失敗之后,詩人托馬斯·柯伯就號召工人“把罷工變成政治斗爭”。中期詩歌中,普遍體現出工人階級希望通過政治改革確立自身主體性的傾向。
克力圖在《自由頌》(1843年)中,表達了工人階級不惜為自由而獻身的壯烈情懷:“萬千大世界,一錢也不值,假使自由盡喪失;為了爭自由,失去全世界,代價輕微不足惜。”柯爾在《暴君的力量》(1846年)中呼吁人們“粉碎手銬和腳鐐”,去“把暴君滅掉”,爭取自由。米德在《蒸汽王》中,呼吁工人們“用子彈、烙鐵,還有木棍”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去“打倒那君王,莫洛克王,和他手下的惡官暴吏”,只有這樣,“公理得伸張,自由得勝利,暴力終于屈服于正義”。以哈尼、瓊斯為代表的暴力派甚至主張采用暴力手段推翻現有統治,哈尼就說:“我們的任務是立即行動,全心全意地為推翻這個制度而努力。”[4]瓊斯在《憲章派之歌》中指出,“我們的生命不是你的麥子,權利不是你的物品”,呼吁工人階級大膽的站起來,粉碎統治者的“十字架、寶劍和王冠”,把自己勞動的果實奪取。在《工廠城》中,瓊斯鼓勵工人們“別垂頭喪氣”,要獲得徹底解放,要敢于舍棄自身。義無反顧地“織自己的尸衣,掘自己的墳墓”。
這種自覺意識甚至超越民族與國界,形成了全球工人階級一家的階級意識。工人階級認識到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只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進行斗爭,才能求得解放。瓊斯就曾說(1854年):“我不只是一個英國人——我是人,我-我們都有一個比狹窄的島嶼更廣大的國家,它包括法國和德國——它也包括匈牙利、意大利和波蘭——我的祖國是世界,我屬于最廣大的被壓迫階級。我本質上只承認兩個民族,暴君和奴隸,富人和窮人。就后者而言,我是一個戰士……”[5]215這方面的內容在憲章派詩歌中占相當的分量,而且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期。比如瓊斯的《自由進行曲》(1848年),山基的《致世界各國工人》(1840年),阿諾托的《給兄弟民主黨人之歌》(1846年),林頓的《列國哀歌》(1848年)、《保衛羅馬》(1849年)等,都是呼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詩歌。
盡管工人階級的主體性發展為比較成熟的階級意識,但大多數工人,甚至包括憲章派主要領導人,還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政治改革,通過“人民憲章”的實現,在現存制度下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1848年之前的詩歌中,都仍然將“人民憲章”的實現作為斗爭的最終目的。比如艾夫在《致威爾斯的憲章派》(1843年)中再次呼吁人們“展開憲章主義的大旗”,吉爾在《歌》(1843年)中熱烈地歡呼憲章,米德在《蒸汽王》中呼吁工人們爭取憲章的實現。甚至1848年之前的瓊斯,都還對“人民憲章”抱有幻想,在1846年發表的《憲章派之歌》中,仍然將實現憲章視為最終目的,堅信“憲章一定屬于我們”。在1847年發表的《工廠城》中還認為,“要保衛自己的土地,最好的辦法——把憲章實現”。
但是,工人階級試圖與資產階級在互為目的的關系中確立自身主體性的努力,只是幻想和一廂情愿。因為互為目的的關系是以功利為基礎的,即工人階級所希望的是,與資產階級形成主體-物(客體)-主體的關系,我為你創造利潤,你給予我應有的報酬和權利,通過物的中介形成平等關系。而資產階級為了謀求利益的最大化,必然通過占有資本而擁有的統治地位,將工人階級客體化、物化和對象化,變成他們牟取利潤的手段和工具。
晚期憲章派詩歌中的工人階級,再也不滿足于政治改革,發出了社會改革的呼聲,希望通過埋葬不合理世界求得自身的解放,成為了“自為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主體性,發展到了使對象主體化,朝著適合于自身方向發展,自覺改造對象的高度。
1847年還在為“人民憲章”的實現而吶喊的瓊斯,在1848年發表的《人民之歌》中,已經拋棄了對統治者的幻想,呼吁詩人們“為人民歌唱——為工人歌唱”,呼吁工人階級團結起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徹底打倒貪婪的權貴人物和黃金大王,不讓其統治“再延續片刻”。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是因為第三次請愿活動的失敗,使以瓊斯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認識到,僅以“人民憲章”作為綱領是不夠的,必須“從單純政治改革的思想走向社會革命”[5]38,消滅成為一切剝削根源的社會制度。
盡管在此之前,憲章派已經認識到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在利益上的不可調和。但由于工人階級還缺乏自覺改造對象的主體性,所以斗爭一直停留在政治改革階段。但統治階級通過殘酷手段鎮壓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使憲章運動處于低潮。這是工人階級幻想在互為目的的關系中確立自身主體性的必然結果,因為互為目的的關系必然轉化為互為手段的關系,而必然導致兩個階級更大的對立、對抗和沖突。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同時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以哈尼、瓊斯為代表的工人階級,具有了使對象主體化的傾向。瓊斯就說:“我再也不向政府呼吁!我要著重指出,我們不能通過游行來達到我們的目的。讓每個人拿起槍來準備戰斗,那時我就能向你們保證,憲章很快就會被宣布為國家法律。”[6]在1851年憲章派國民大會頒布的新綱領中,已經將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了。
這一時期的詩歌大約80首左右。因為群眾性的憲章運動在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下陷入低潮,大多數詩人隱退了,繼續創作的僅限于瓊斯、林頓、馬西、尼古爾斯、查德威克、柯爾、艾爾弗雷德、羅布森等七八個詩人。盡管如此,但這一時期的創作仍體現出工人階級對自身主體性的挖掘。而且因為資產階級激進派與工人投機分子的退出,使工人階級隊伍更純潔,階級意識更強,主體性更自覺,不僅反對資本,而且要改造世界。
晚期詩歌在內容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為社會革命提供依據的詩歌。工人階級之所以要進行社會革命,是因為他們已經從政治改革的迷魂湯中覺醒,看到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和兇殘。比如尼古爾斯的《國會》(1851年),諷刺那些國會議員只關心地主的權利、工廠主的利潤,而對工人階級的利益避而不提,對工人的死活置之不理。在《和平世紀》(1848年)中,瓊斯通過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嘲諷英國政治改革的欺騙性。在長詩《新世界》(1850年)中,瓊斯虛構了一個叫印度斯坦的地方。在那里,資產階級利用人民取得勝利后獨吞勝利果實,并用改革的謊言欺騙人民。當人民認清了他們的本質起來反抗時,他們原形畢露,進行殘酷鎮壓。很顯然,詩歌是在影射英國資產階級的虛偽與兇殘。他還通過印度斯坦人民的覺醒,說明人民的主體意識是怎樣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同時說明,如果不進行社會改革,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自由神》(1851年)中,瓊斯通過對為自由而犧牲的英雄們的追思,控訴“壓迫者的滔天大罪”。林頓的組詩《現代碑銘數題》(1851年),甚至用墓志銘的方式,為資產階級及其幫兇唱挽歌。統治階級對人民欺騙與鎮壓,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
二是表達進行社會革命決心的詩歌。瓊斯被捕后,敵人將他關在單人牢房中度過了孤寂的兩年,但他沒有屈服,相反堅定了革命的信心。在《沉寂的牢房》(1851年)中,他寫到:
從來不打算卑鄙地后退,
或者做個不肖種;
只要我心中脈息在跳動,
勇敢自豪向前沖。
監禁一解除,他們會發現
我堅強而沒有改變,
我不是恨哪一個,而是
為他們全體感到可憐。
從監獄出來的時候,他再次表白:“當我被捕入獄時,我是一個憲章派,但當我出獄時,我成為了一個共和主義者……我曾經因為說要讓綠色的旗幟飄揚在唐寧街的上空而被捕,但被捕后我改變了我的顏色,我現在變成紅色的了。”[5]113在《賤民之歌》(1852年)中,瓊斯堅信只要“軍號一旦吹鳴”,工人階級就會伸出手,“擊碎那狂妄君主的心”。在《未來之歌》(1852年)中,他鼓勵同伴踏過統治者的宮殿,讓他們“像玻璃一樣破碎,滅亡”,把“新世界”的美好未來變成“今朝”。
在《人民的集結》(1851年)中,林頓將社會革命比做暴風雨的來臨,那時候一個個工人如同“雪花”,“全都集齊、結成整體”,變成一場“雪崩”,發出雷鳴般的吼聲,滾向統治者,摧毀統治者。在《出路》(1851年)中,林頓鼓勵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不要畏縮”。哪怕是流血犧牲,也是為新世界的建設付出的應有的代價。
另外如查德威克《暴風雨即將來臨》,(1850年)、馬西的《他們死了》(1850年)等,都是激勵工人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的詩歌。前者將工人階級的革命比做暴風雨,它是自由的閃電,是憤怒的咆哮,它將使奴役的大地蘇醒。覺醒的工人階級是不可戰勝的,他們將驕傲的挺立,去審判統治者的罪行,而專制魔王將在他們的面前瑟瑟發抖。后者通過歌頌1848年革命中犧牲的烈士,鼓勵工人階級在烈士們敲響的戰鼓聲中,在紅色曙光照耀下前進,去迎接專制魔王的末日。
三是設想與建構未來社會的詩歌。社會革命不僅包括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還要建構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那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呢?詩人們進行了憧憬與展望。羅布森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正在到來》中,為工人階級憧憬了一個沒有失業,沒有饑餓,沒有剝削的“偉大的時代”。艾爾弗雷德在《紅色的旗幟》中,為人們描繪了一幅公平正義的共和國藍圖。瓊斯向人民描繪的“新世界”,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人們悠閑地生活,傳統得到延續,科學技術用來為人類造福,沒有了紛爭,人與人之間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未來世界在向人們召喚,從而激發起工人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的信心與勇氣。
晚期詩歌中的工人階級,主體性已經有了質的飛躍,認識到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自覺地改造世界,成為了“自為的階級”。但是,工人階級的主體性離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還有很大距離。無產階級是代表全人類的,也是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但憲章派詩歌中的工人階級,所爭取的主要是工人階級的利益與權利。由于工業革命的成果被資產階級竊取,用來剝削工人階級,而且從自由貿易中獲取利益的也是資產階級,所以工人階級對大工業生產以及自由貿易都抱有抵制態度。這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所應該有的態度,也就是說,它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全盤否定,沒有將資本主義社會當作歷史過程的總體來認識。既然這樣,它就不可能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主體。同時它對于社會革命的內容和方法都缺乏明確的概念,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也是抽象的,還帶有空想社會主義性質。
盡管如此,但憲章派詩歌作為工業革命后英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結合的產物,通過對工人階級主體性的挖掘,參與了新的世界體系的生成。
[參 考 文 獻]
[1] 魏小萍.主體性涵義辨析[J].哲學研究,1998(2):22.
[2]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61.
[3] Mikes Sanders.The Poetry of Chartism:Aestheics,Politics,History[M].London.Cambridge UP,2009:1.
[4] 沈漢.英國憲章運動[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178.
[5] John Saville.Ernest Jones:Chartist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 Jones[M].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52.
[6] 庫捷爾.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M].楊靜遠,譯.北京:三聯書店,197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