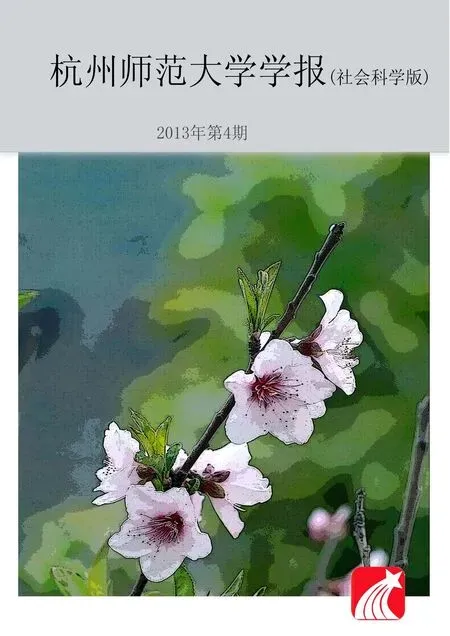情感與品味:影視劇觀賞的受眾美育
孟 麗
(中國傳媒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24)
文藝新論關于“觀賞文明與審美教育”的討論
情感與品味:影視劇觀賞的受眾美育
孟 麗
(中國傳媒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24)
作為藝術觀賞的一部分,影視劇的觀賞在社會美育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影視劇的觀賞過程中,虛擬性消解了欣賞者與審美對象之間的距離感,欣賞者融入到對象中。影視劇通過它的情感化效應作用于觀賞者。因此,我們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應該是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受眾獲得心靈的震撼和凈化,在審美愉悅的過程中得到情感的感染和向上的力量。影視劇觀賞可以成為社會性美育最為便捷、也最為有效的途徑。
觀賞文明;影視劇觀賞;情感化效應;社會美育
“觀賞文明”的提出,是對精神文明內(nèi)涵的充實與具體化。當然,觀賞文明只是精神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當下,隨著藝術觀賞的日益普遍化,人們在觀賞過程中得到情感體驗。藝術觀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額越來越大,社會和家庭環(huán)境中的審美教育成為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關于美育,已有為數(shù)眾多的研究成果,單純談論美育,對于當代精神文明建設和美學理論,都沒有什么裨益。而從美育的角度來理解觀賞文明,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實際提升,抑或是對于美學理論的發(fā)展,都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觀賞文明古已有之,而且中國和西方有著各自的觀賞文明傳統(tǒng)。但在大眾傳媒成為人們主要審美方式的今天,觀賞文明一方面應該具有自覺的理論建構,另一方面在內(nèi)涵和外延上都應該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觀賞文明關涉到的對象領域其實有很多,諸如文藝演出、美術展覽、體育賽事等等,而影視劇的觀賞,則是當代人們最為普遍的藝術觀賞方式。美育是國家的教育方針之一,學校美育是學校教學計劃的組成部分,那么,學校之外呢?社會與家庭,其實更應成為更為廣泛、持久的美育場所。這是因為:美育對于人來說,不能止于學校,而是終其一生的教育方式。學校美育,更多的還是有計劃的、自覺的、帶有某種灌輸?shù)暮圹E,而在社會和家庭環(huán)境里,美育則是不自覺的,帶有普遍性和娛樂性。影視劇的觀賞,是社會美育的主要途徑,但它的實現(xiàn),往往都是在工作之暇的放松情境下進行的,而且是抱著愉悅自己的態(tài)度。這種情境下獲得的美育效果,恰恰是潛移默化的。這樣,影視劇作品作為審美對象的內(nèi)容和藝術效果,對于受眾來說,就十分重要。“寓教于樂”是關于教育或美育的老生常談,對于影視劇的觀賞來說,這也許遠遠不夠。影視劇作品作為社會的精神產(chǎn)品,其品味的高下,藝術水準的優(yōu)劣,會直接作用于受眾的心靈。因此,當我們將觀賞文明與美育作為議題時,影視劇觀賞自然不容忽視。
影視劇成為大眾主要的娛樂方式,是不可避免的,這與圖像在人們?nèi)粘I钪谐尸F(xiàn)出日益強化的趨勢相關。這里所說的圖像,自然不是以往時代藝術家們創(chuàng)作出來的視覺藝術作品,而是憑借當代的大眾傳媒,通過電子等高科技手段大批復制生產(chǎn)出來的虛擬性形象。[1]在日常生活中,圖像越發(fā)地突顯出其重要位置,成為消費文化發(fā)展的中心。
所謂“審美化”,德國的韋爾施講它源于人類的形式感覺和形式情愫,指的是用審美因素來裝扮現(xiàn)實。隨著傳媒技術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審美化發(fā)生了改變,由物質的審美化轉向了非物質審美化。因此,審美化具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首先,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層的審美化;其次,更深一層的技術和傳媒對我們物質和社會現(xiàn)實的審美化;其三,同樣深入的我們生活實踐態(tài)度和道德方向的審美化;最后,彼此相關聯(lián)的認識論的審美化。[2](P.40)
在韋爾施看來,審美化最終的結果是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新的認知,技術和傳媒所帶來的審美化在這一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此時所言的審美化,歸根到底是指虛擬性。韋爾施注意到圖像的產(chǎn)生是有選擇性地采取素材,而非現(xiàn)實的紀實見證,因此,現(xiàn)實是圖像的供應商,圖像呈現(xiàn)的是虛擬性的現(xiàn)實。所謂虛擬性,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特定的審美把握。正是由于虛擬性,人們對于現(xiàn)實的單純建構、現(xiàn)實的存在模式及現(xiàn)實的認知發(fā)生了改變。這種意識的建構,已經(jīng)遠離了現(xiàn)實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真實狀態(tài)并不等同,這也正是博德里亞所言的“超真實”。
但是,不同于博德里亞,韋爾施為圖像的虛擬性進行了辯護。他指出,真正審美化的文化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它對差異和被排斥的事物是很敏感的。“首先,(真正的審美化,筆者注)不是光沉浸在藝術形式和設計的關系之中,而是同樣關注日常生活,關注生活的社會形式……不是那種藝術的愉悅,而只是契合當今現(xiàn)實的一種反思的審美意識,才提供了同樣也能具有社會內(nèi)涵的情感性潛質。其次,它的結果不是被直接理解,而是被間接理解的。但是,通過藝術條件和生活條件的相似性,有可能發(fā)生的是審美情感向社會問題的轉化。”[2](P.43)能夠對審美化做出如此判斷,在于韋爾施對認知的審美化并沒有持消極的態(tài)度。他承認相對于現(xiàn)實世界,審美世界是一種特定的懸置狀態(tài)。可對此他又進行了恰當?shù)男拚谒磥恚覀兊恼J知和我們的現(xiàn)實在最初就含有審美成分,沒有審美化就沒有我們的認知和現(xiàn)實,這是它們本來的存在模式。麥克盧漢講“媒介即信息”,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對此解釋,認為信息在此應理解為隱喻,即媒介是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定義現(xiàn)實的。就韋爾施的分析,認知也是隱喻,從認知的隱喻再轉向圖像的虛擬性,這一角度并不新鮮,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也有相似觀點。但韋爾施的不同在于,他將圖像的審美化提升到一定高度,是“反思的審美意識”,關注的是與受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而且審美化通過審美情感影響受眾,提出“審美化通過它的情感化效應,可以干預社會過程”的命題。技術與傳媒審美化的這一潛能,促使信息和行動之間的關系不再抽象而疏遠,信息-行動比*“信息-行動比”,參見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書中他談到當電報出現(xiàn)后,大量的信息便隨之產(chǎn)生,人們了解的信息不再具有影響行動的價值,不同于口頭文化及印刷術文化盛行的時代,所以信息-行動比失衡。可趨向于平衡。所以,韋爾施對審美化并不持批判的態(tài)度,核心就在于情感化效應。
情感化效應的出現(xiàn),在于在影視劇的觀賞過程中,人們不再采取傳統(tǒng)藝術所具有的觀照的審美態(tài)度,虛擬性消解了欣賞者與審美對象之間的距離感,欣賞者融入到對象中。就此,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中有詳細地闡述:
夢境最值得注意的外在特征就是作夢的人總是居于夢境的中心……可以說,他與各個事件的距離都相等。各種事件也許就發(fā)生在他的周圍,也許就出現(xiàn)在眼前,他參與或打算參與活動,或者痛苦或是沉思,但是,夢境中每件事物對他來說都同樣有直接的關系。
這種美學特征、與我們所觀察的事物之間的這種關系構成了夢的方式的幾個特點,電影采用的恰恰是這種方式,并依靠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虛幻的現(xiàn)在。就其與形象、動作、事件以及情節(jié)等因素的關系而言,可以說,攝影機所處的位置與作夢者所處的位置是相同的。[3]
在蘇珊·朗格看來,在拍攝中,攝像機是導演的眼睛,而到影片觀賞階段,攝影機又成為了觀眾的眼睛,觀眾變成為作夢者,觀賞如同做夢。蘇珊·朗格對此看得十分透徹,電影之所以能比喻為夢境,在于逼真性,二者在時空的表現(xiàn)方式上很相似:在空間上,電影不同于舞臺上的戲劇,沒有固定的空間框架,它是從屬性的幻覺,忽隱忽現(xiàn),是隨事件的發(fā)展而變化的;在時間上,影片中鏡頭閃回的節(jié)奏絲毫不輸于我們的思維,意象的展示便是思維在銀幕上的投射,呈現(xiàn)的是我們內(nèi)心的生活。無論是做夢還是觀影,眼前的一切都是如此逼真,仿佛置身于現(xiàn)實之中。
但是,盡管逼真性的存在,蘇珊·朗格仍明確地指出電影的觀賞不等同于做夢,或者稱之為“客觀化的夢”。這是因為情感在電影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與夢境有所不同。就創(chuàng)作上來講,電影是情感的符號,畫面、音樂、聲音等手段都圍繞著情感,巧妙地安排在一起,保持故事的連續(xù)性。如電影鏡頭的剪輯,有學者在研究香港動作片的剪輯方式時提出“三鏡頭法”,就是演員在打斗過程中,當身體觸碰時一定要完整地呈現(xiàn)在畫面,從而保持畫面的真實,成功地調動觀眾的情緒。這自然有利于整部影片的欣賞,如影片《葉問2》中葉問與洪震南的圓桌對決,觀眾看得目瞪口呆,全身心地投入,并成功地進入故事中,追隨故事的發(fā)展。在觀賞中,審美對象是自主的,觀賞者能夠意識到情感被左右,蘇珊·朗格早于韋爾施關注到情感化效應,只不過她僅僅將電影作為了研究對象。
對于情感化效應的大段闡述,目的是說明影視劇,作為大眾的主要娛樂方式,是如何作用于觀賞者的。從這一角度而言,我們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應該是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受眾獲得心靈的震撼和凈化為追求的。通過影視劇的觀賞,受眾會在審美愉悅的過程中得到情感的感染和向上的力量。而這種效果不是通過理性的方式,而是以滿足受眾的審美需要的方式產(chǎn)生的。這就需要創(chuàng)作者很好地處理影視劇作品中的藝術性與娛樂性。若作品僅僅追求藝術性,那就曲高和寡,沒有收視率或票房,在傳播過程中也不會產(chǎn)生效應。若作品以放棄藝術性為代價,一味偏向娛樂,或許贏得收視率或票房,但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自然招來批判。
作品中藝術性與娛樂性二者的平衡,直接關系著美育的發(fā)展水平。從社會學上講,當民眾擺脫了過去普遍存在的生存壓力后,每個個體便面臨著行為抉擇,而這時沒有選擇的模范或規(guī)則可依,內(nèi)心體驗便成為選擇依據(jù)的首要因素。娛樂成分是內(nèi)心體驗的需要,費斯克就指出,“快樂之所以是有快感可言的,只是因為它是由體驗到快樂的大眾生產(chǎn)出來的,它不是從外部傳送給人民的”。[4]優(yōu)秀的影視劇作品都會順應觀眾的需求,滿足大眾的娛樂欲望。如像《媳婦的美好時代》《幸福來敲門》《喜耕田的故事》,對于普通老百姓家長里短、爭風吃醋、油鹽醬醋的世俗生活描述,在電視劇《永不磨滅的番號》《亮劍》《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男主人公自身行為霸道、言語粗俗等缺點的展示。然而,這些作品在娛樂觀眾的同時,或是傳遞出積極向上、樂觀昂揚的生活態(tài)度,使欣賞者感受到平淡生活中最樸實真摯的人情美;或是通過塑造的真性情英雄,激發(fā)觀眾自身對國家、對人民的熱愛及奉獻精神。這些作品中的娛樂,我們不妨看作是藝術欲望,它不是專為觀眾的消遣而設置,是為了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呈現(xiàn)出生活的多面性,使作品意義更豐富。可見,娛樂性與藝術性的和諧融洽,是影視劇藝術在當下發(fā)展的時代特征。
美育作為特殊的教育方式,當然是以人們樂于投入的心情和對愉悅的渴求來進行的。當代的影視劇通過大眾傳媒的渠道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人群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因而是當代美育最為便捷的、也頗為有效的方式。在于受眾本身來說,觀賞也許更多的是一種自發(fā)的或者是休閑的狀態(tài),不同于政治學習和科學研究的理性和自覺的狀態(tài),然而唯其如此,觀賞活動才能獲得最佳的效果;而對于社會性的美育來說,影視劇觀賞也成為最為方便、也最為有效的途徑。因此,重視影視劇觀賞和當代美育的關系,是美育理論的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內(nèi)容。
[1]張晶.圖像的審美價值考察[J].文學評論,2006,(4).
[2][德]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M].陸揚,張巖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3][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傅志強,周發(fā)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480.
[4][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王曉玨,宋偉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57.
EmotionandTaste:TheCoreoftheFilmandTVDramaAppreciationForAestheticEducationoftheAudience
MENG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lm and TV drama’s appreciatio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authenticity in images results in a “super-real” appearance, which is to bring people a false sense of what the life is. Therefore, film and TV drama can make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dience’s behavior, especially through emotional effect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the influence of the appreciation of film and TV drama.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make the appreciation an appropriate wa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watching-appreciation civilization; film and TV drama appreciation; emotional effects;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society
2013-03-29
孟麗(1983-),女,山東曲阜人,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
I01
A
1674-2338(2013)04-0092-04
(責任編輯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