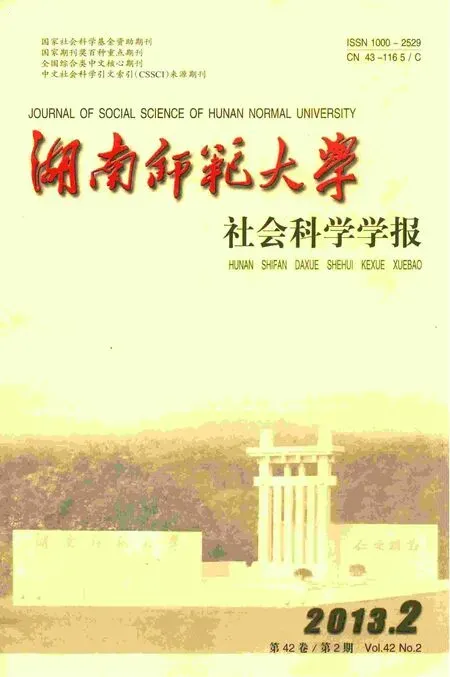鴉片戰爭中漢奸作用問題研究
陳偉明,金 峰
在鴉片戰爭的相關史料中,“夷人犬羊之性”是一句習見之語,反映了戰事之初乃至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由于昧于形勢,清廷上下對英人發動戰爭的目的及作戰能力等仍惘然無知,只得以此來強加解釋。尤其是清人最初對英人具有強大的陸戰能力而肆虐于沿海大為詫異,也難于相信粗鄙無文的蠻夷能夠熟練運用高超的戰略戰術,以至對于漢奸的作用也產生了一種錯誤認識,即將其視為英人侵略行動的主謀,并將英軍在陸戰中所取得的勝利“歸功”于漢奸。如梁章鉅稱:“風聞英夷在廣東洋面,肆其鴟張,若非有漢奸為之主謀,斷不能長驅直入。”①道光也稱:“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②隨著戰事發展,清人對英國了解加深,這一認識逐漸得到修正,如裕謙即指出:“現在逆夷在粵,通共不過六七千人,除水手而外,戰兵不過三四千人,全賴漢奸為耳目伙黨。”③祁貢也稱:“漢奸以外夷為護符,外夷以漢奸為爪牙。”④均將漢奸定位為“耳目爪牙”這一角色。在鴉片戰爭期間,清人對于漢奸作用問題的認識,固然出于親歷親見,但更多則不乏浮夸扭曲,甚至是故為諱飾的言辭,其真相如何,尚待依據史料訂證。至于漢奸之作用對戰事的影響和意義所在,尤須根據史料作更加客觀、細致的分析。
一、清人對于漢奸作用的認識
鴉片戰爭中,清人對于漢奸的具體作用有諸番描述,茲羅列于下:
接濟,即向英軍提供生活物資。如杜彥士稱:“更有一種奸民,與營弁通同一氣,接濟水米,多方獻媚。”⑤林則徐也稱:“臣等于前次燒毀接濟匪船二十三只之后,仍嚴飭水陸文武,力拿通夷匪犯。”⑥為英軍提供食物給養是最常見的對漢奸行為的指控。
煽惑,即散布謠言。如奕經指出:“惟查逆夷每到之處,必先暗遣漢奸,多方探聽,布散謠言,煽惑人心。”⑦吳其濬則稱:“據英俊遠探。有英夷遣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⑧
通事,系指充當語言文字翻譯。如唐鑒提到:“臣聞英夷前到天津,遣有兩通事上岸與琦善傳話,一系紹興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為漢奸無疑。”⑨又如奕經稱:“又(漢奸)方錫洪即王一成,因貪夷人財賄,即自行投教夷人書寫漢字。”⑩
紅毛鄉勇,系為在寧波等英軍占領區出現的偽治安機構服役的人員。如奕經曾談及:“該處人情險惡,半系漢奸,……受夷人暗雇充當紅毛鄉勇。”[11]漢奸虞得倡也供稱:“夷官郭士立,即甲士立,點撥我充當巡捕總頭,……又另外招募五十人,幫同辦事。”[12]
間諜,即為英軍搜集、提供中方的軍政情報。如齊慎曾提及:“奴才訪得英夷猖獗,實由漢奸為之耳目,我兵舉動,彼皆先知。”[13]而奕經在浙東作戰不利時則稱:“自兵過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為漢奸逐隊細數,官兵虛實,逆夷無不盡知。”
向導,系指為英軍的軍事行動向導引路。如琦善曾稱:“又有漢奸為之導引,抄擊營盤,水陸交攻。”而王廉訪則稱:“夷船之進內河,其初并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
后勤服務,即為英軍提供勞役服務。奕山曾奏稱:“該犯(漢奸溫東幅)供認,因投入英夷船內工作,代逆夷轉招漢奸屬實。”另如漢奸布定邦供詞也稱:“船內漢人只有廣東南海、番禺縣人,其余都系作跟班管家及廚子等類,無作官的。”
放火,在清軍前線官員奏折中大量出現的漢奸“放火”一詞,系指漢奸為配合英軍作戰而進行的牽制性、騷擾性的縱火行為。如奕山聲稱:“且漢奸到處竊伏,乘機放火,……漢奸又擲火罐火球,焚燒臨水房屋。”奕經則同樣提及“乃山勢彎曲,其前路狹窄之處,已為漢奸暗中焚燒”等情形。
戰斗人員,有關漢奸參與英軍作戰的情況可見于諸多戰役的報告。如琦善曾提及:“至漢奸人面獸心,……臨陣則仿造號衣,又與營兵無別,往往混入軍中,真偽莫辨。”楊芳也描述了“漢奸小艇千余只,遠近巡邏五六里”的情形。另如裕謙奏報定海失守情況時,同稱:“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系閩、廣亡命,夷匪隨后指揮……約計總有萬余人。”[14]奕經有關乍浦交戰及收復寧波、鎮海戰役情況的報告中,均有漢奸參戰的記述,對長溪嶺一戰的描述尤為生動。
二、鴉片戰爭中漢奸作用考實
上文羅列了清人關于漢奸作用的種種描述,涉及到戰事的方方面面,然依據史料詳加考證,事實真相卻未必如此。
就后勤補給而言,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極少提及給養補充方面遇到的困難,其根本原因在于英軍控制了制海權,補給路線安全暢通,軍火、糧食等物資并不依賴于戰地供應。當然英軍在占領后掠取公私財物進行補充[15],以及通過戰地補給獲取生活物資如新鮮果蔬、家禽食物等,顯然也有一定意義。漢奸在提供此類物資接濟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布定邦即是在為英軍搜尋給養的過程中被清軍捕獲,對此賓漢曾指出:“買辦(即布定邦)已經在十七日被中國人擒獲……在他被擒以前,由于他的緣故,糧食的供給是很充裕的。”可見布定邦的被捕在一定時間內也給英軍食物補給造成了困難。從林則徐在廣東大張旗鼓地懲治辦艇、扒艇、雜貨料仔艇、賣果子糕餅的扁艇等等的舉措來看,戰時同英人進行物資交易的現象相當普遍。這一現象在其他戰場上也屢見不鮮,如端華在奏報廈門失守的情況時談到:“(逆夷)曾出重價買豬羊牛只,圖利奸民及貧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筍等,向鼓浪嶼岸邊昂價售賣。”英人對此類交易的評價是:“一切都很平靜,中國商人已開始信賴他們的新主人,供應很充足。”[16]端華雖區別了“圖利奸民”和“貧苦之人”,然而在整體上,清廷上下普遍未能有意區分如布定邦這樣為英人服務、專門從事物資征集的漢奸與同英人交易的一般民眾之間的差別。應當指出,盡管此類交易的資敵性質顯而易見,但對被占領區民眾而言,由于其時大多數人并無民族、國家意識,又因英軍占領而清軍無力提供必要的軍事保護,將其行為一概視為通敵賣國并不妥當。如果考察布定邦一類漢奸的作用,則雖能為英軍提供一定幫助,但對其物資供給而言并無決定性的意義。
關于煽惑,清人提及的漢奸所散布的謠言,其內容和用意均不明確,大意當指出于擾亂民心和破壞社會秩序。然而英國發動戰爭的目的主要在于迫使清統治者屈服,并無傳播戰爭謠言以恐嚇一般民眾的必要。在鴉片戰爭中,各地普遍出現了與戰事有關的謠言,內容相當雜蕪,而謠言的傳播者則多為一般民眾,并非負有使命的漢奸。就這些謠言傳播的后果而言,也并未對清政府的軍事部署造成實際影響。值得注意的反倒是林則徐所指出的:“該夷義律在粵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探聽揣摩,并習聞有邊釁二字,藉此暗為恫嚇……且密囑漢奸,播散謠言,皆其慣技。”[17]即英人因掌握道光帝無意為禁煙而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政治情報后,通過制造禁煙將引發“邊釁”的輿論來影響清廷決策。林則徐對此十分警惕,他將散布此類言論者稱為漢奸,用意在于對“勿啟邊釁”的輿論作出回應,以塞反對禁煙的廷臣之口,以期鞏固道光支持其禁煙事業的政治決心。道光最終摒逐林則徐,恰恰是因其認為林氏禁煙舉止失措而“輕啟邊釁”,引發戰事,正反映出此類輿論的作用所在。然而清廷對于此種并非在一般民眾中傳播,而是以影響清帝及官僚政治態度的輿論暗流,始終未予足夠重視。
清廷出于防范中外“勾串”的用心,對通事的作用尤加重視。戰前即存在對夷人使用漢字、漢語的擔憂,如道光十二年關于胡夏米船案的奏折中即提到:“先因查閱夷書紙片字畫,似系內地樣式,恐有內地奸民,為之翻刻。”道光則一口咬定:“何似之有,直系內地手筆,無非上下朦混規避而已。”隨著戰事發展,清人認識到久居中國的夷人完全可能熟悉漢字、漢語,這一疑惑逐漸消除。但漢奸為英人從事語言文字翻譯工作的情況則顯系事實。如林則徐曾提及的英人以木片“寫明鴉片一個洋銀幾圓字樣。隨潮流入口內,以賤價誘人售買”[18],此項工作即應由漢奸承擔。在整個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收集、翻譯情報以及向導、探路等侵略行動并未受到語言文字方面的困擾,漢奸通事的作用不可替代。
史料中關于“紅毛鄉勇”的記載,反映了英軍在占領區建立偽行政機關、使用偽警察等情形。如同在強占香港后很快建立殖民政府一樣,英軍在占領定海、寧波、鎮海等地期間,也均有建立偽行政機關的舉措,其目的在于幫助英軍維護占領區的社會穩定和便于其掠奪物資。這些偽行政機關主要負責維持社會治安、主持司法審判、征稅等活動。這些偽機關確有征招華人充任“警察”亦即“紅毛鄉勇”的事實,如奕經曾奏稱:“據查寧波向系郭士立管理,今易以漢奸梁仁,凡一切悉為所主。”英人也稱:“在(舟山)全島建立警察的打算被證實是不成功的,要享受這種崇高榮譽的候選者其實都是些大流氓……還有一些受人敬重的當地人被推選出來擔任了同樣的職務,他們一聲不吭地接過了印刷的委任書,但卻一點也沒把它放在心上。”[19]
有關間諜的情況,楊殿邦在禁煙運動中即曾指出:“聞有英吉利國夷民顛地及鐵頭老鼠(即查頓)兩名……該夷民常與漢人往來,傳習夷字,學寫訟詞,購閱邸鈔,探聽官事,不惜重資。”反映出英人在戰前即已開始對中國各方面情報進行收集,這些獲取情報的渠道被英軍用于為戰事服務。因此,當英人說出“我們在這里要提及的是所有有關那些可憐的夷人的重要國家文件都是很細心地傳到了內閣成員的手里,但是由誰傳遞的我們不能說出來。這些先生們給我們的情報是如此之精確,后來我們與廣州獲得的各種文件相比較,竟發現沒有一絲一毫的出入”[20]這一大段話時,我們絲毫不應感到奇怪。在軍事情報方面,如駱秉章所言:“乃英夷窺探,……賄賂廣州府幕,囑其從中設法,……故軍營之法制,逆夷無不盡知;軍營之籌備,逆夷無不盡曉也。”這種情形在浙東戰區也同樣存在。如賓漢曾描述道:“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的夜間,是中國人所擇定的同時向我們進攻的‘吉日’,進攻的信號是燃點幾只火筏。……我方獲悉敵人在慈溪大舉集合,又據報告,在慈溪以北半哩的地方,施公山(Segaon)上,在兩個有壕塹的軍營中,集中著一支很強大的中國軍隊。”在整個戰爭期間,英軍間諜工作卓有成效,其所獲得的軍政情報達到了相當高的級別且準確可靠。英軍在鴉片戰爭中占盡優勢,軍事實力相對強大固然是主要原因,而其自始至終掌握精準的情報,也為其制訂作戰計劃或調整戰略部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至于向導,英軍在作戰中熟諗水陸路徑的現象在戰爭中屢見不鮮,其主因即系有地方居民為英軍引路。如奕經報告浙東戰況時甚至稱:“各逆每日領帶夷兵,駛駕火輪船,漢奸為之導引,在寧波、慈溪地界數十里內外,各路搜查,……而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21]奕經所述雖不無夸大,但英軍熟知戰場地理的情況顯然也是實情。如賓漢描寫英軍進攻廣州城的情況時也稱:“黎明時分,復仇神號又起錨了……該輪找到六個領港,用以領過所要經過的不同支流。”早有論者指出清人因“意識不到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存在”而與英軍合作的情況。清統治者將這些“一時圖利”而為英軍帶路的民眾視作漢奸雖并無不妥。此外,《壬寅聞見記略》中還有“(英夷)擄民人王在坤,使為導引”[46]一類的記述,可以發現一些充當向導的民眾系因受英軍脅迫,未必盡屬漢奸。
有關漢奸為英軍提供勞役服務的情況同樣復雜,如林則徐曾稱“獲夷船上廚工梁亞次等六名”,牛鑒也提及:“(逆夷)驅使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下船”。鴉片戰爭中清人對英軍戰艦和商船往往不加區分,林、牛二人均未確指是漢奸在為英軍服務。從鄧廷楨《與張預佑》一詩所反映的英軍俘獲綠營兵斷其辮而役使的情況來看,英軍存在著強迫華人為其提供后勤服務的情況。英人在談及此事時則稱:“犯罪者普遍要求使用打板子和囚禁的辦法來促使他們悔悟,假如他們是重罪犯,那就剪掉他們的辮子。”[22]亦即剪辮子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目的是為了懲戒犯罪。當然,英軍并不憚于強迫華人為其提供勞役,如占領定海后因人力不足,即出現“對苦力的招用現在已經開始了,假如要抓任何苦力,那么只有正規部隊才能進行”的情況。英軍作戰期間因勞役人手不足,曾雇用了大量華人以為補充,而當能夠提供此類服務的漢奸不能滿足需要時,武力征招一般民眾的情況也并不鮮見。
至于漢奸縱火,與前文所述“煽惑”問題相類,因英軍較為明確地無意使戰火延及平民,且因相對而言英軍在武力上居絕對優勢,并無在戰斗中以縱火制造騷亂或社會恐慌的必要。當然在各地戰場上均確實存在著火災蔓延的情況,但縱火者屬誰則尚難明確。以1841年5月英軍進攻廣州時珠江沿岸碼頭大火為例,除有漢奸縱火的記錄外,清人還稱:“探得四月初三日,我兵先放草船三只,火物齊發,因風不順,延燒潮音馬頭鋪戶數十間。”存在諸多不同的說法。在混亂的戰場情況下,似已難以分清究竟是漢奸、綠營兵,抑或英軍炮火制造了火災。需要指出的是,英軍在當時有意攻擊非軍事目標的可能性很小,而考察《粵東紀事》中“陸路之兵圍住夷館、公司館,打毀館內洋貨,盡行搶入城內分賣,滿街洋貨”的記載,聯系到浙江戰場上出現的大量亂民在戰后放火搶劫的記錄,亂兵、亂民縱火搶劫應是戰亂中火災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軍武裝漢奸參與對清軍作戰的可能性是難以設想的,盡管英軍在總人數上不占優勢,然而通過武裝漢奸以彌補士兵數量不足,則更會帶來指揮、協同乃至裝備供應等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問題。盡管有材料稱:“用滑膛槍、火藥和彈丸武裝起來的走私者并不在少數,這些武器皆為外國人所提供,使得他們能以此抵御他們自己政府的官員。”[23]但由鴉片商武裝煙販進行走私是一回事,由英軍武裝煙販參與戰斗又是另一回事。在此必須指出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四關于查拿漢奸的一道上諭的作用,該上諭稱:“且夷船多只闖入內洋,若無漢奸接引,逆夷豈識路途?以食毛踐土之民,敢于自外生成,為夷匪主謀向導,實屬罪不容誅,至沿海弁兵,疏于防范,已非尋常失察可比,若竟勾通接引,尤堪痛恨……若有內地奸民,潛蹤出入,一經獲察,嚴究有無通夷等逆情事,從重懲辦。其疏防縱奸弁兵,亦著一體嚴拿,加等治罪。”[24]道光此諭顯然出于滿漢民族猜疑的心理來看待漢奸問題。在此諭之前,林則徐、鄧廷楨等前線大員奏折內所稱漢奸,均是指煙販、接濟者及通事等類,并無漢奸參戰的記錄,其他前線官員如顏伯燾關于廈門失守的戰報,亦均未見漢奸參戰的記載。而此諭發布之后,不僅隨即出現大量討論防范處理漢奸問題的奏折,前線戰報中漢奸的地位、作用也開始凸顯,并且如裕謙等人對漢奸是參與作戰還是為英軍提供后勤服務也不加區分,漢奸人數動輒“數千”、“萬余”,漢奸也就逐漸變成前線官員掩飾其作戰不力、腐敗無能的渾然天成的借口了。而在英軍的記載中,賓漢對廣州之戰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在這地方,江中很堅固地設著椿柱,船隊花了四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才開辟了一條水道。大約有二百個農民協同工作。”[25]可見確實存在著漢奸參加作戰行動的事實,然其主要作用是從事河道清理一類工兵工作。關于此類漢奸的人數問題,從前文所引材料來看,虎門戰役的一次戰斗即達二百余人,而英軍由四方炮臺撤出時也使用了八百余名“苦力”運輸軍火物資。盡管這些人是英軍以戰勝者的姿態進行脅迫,也是廣州文武官員迫不及待要將英軍送出虎門的情形之下產生的,其規模也相當可觀。總之,漢奸以戰斗人員參加作戰的情況并不存在,然英軍役使華人提供后勤服務甚至工兵作業的情況則屬事實。因戰役規模不同,此類“漢奸”有時的確可能多達數百人。
三、漢奸作用對于鴉片戰爭的影響
在討論鴉片戰爭中的漢奸問題時,有論者以為“漢奸是一個最不確定的稱謂”,從而將漢奸視為“一切不便解釋或難以解釋的事由、責任、后果”的承擔者,也有人指出清人常將漢奸當作“模糊不清又無處不在”的“替罪羊”。從清廷對待漢奸問題的態度以及處理該問題的應對措施來看,這些評價并無不妥,然就漢奸的戰場作用而言,則此類評價未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漢奸作用對于鴉片戰爭中所產生的影響。
筆者曾撰文指出:清廷在討論漢奸人員構成問題時,采取了概而論之的做法,以整體利害關系的分析替代了對個體行為的考察,將一些社會階層如行商、買辦等全體視作漢奸。同時,清廷所討論的“漢奸”并無明確定義,“漢奸”稱謂的使用具有相當的隨意性,這就使得漢奸問題更加復雜,其嚴重性也被顯著夸大。清廷上下在分析漢奸作用問題時,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各類關于漢奸作用的描述均不乏夸張的不實之詞。如有關漢奸在戰時縱火、以戰斗人員身份協同英軍作戰、散布意旨不明的謠言,以及動輒成千上萬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等,有些出自傳聞,有些則顯系前線官員藉以掩飾其無能昏聵,就此而言,漢奸顯然就是“替罪羊”;此外,清廷出于無知自大及民族防范心理,一直禁止漢文書籍流向海外,也始終關注外人掌握使用漢語、漢字的問題,因此對通事的作用給予了不應有的重視。而在鴉片戰爭中,盡管存在著漢奸為英人承擔語言、文字翻譯,亦即通事工作的現象,他們對于戰事卻并無實際意義;有關漢奸為英軍服役的問題同樣如此,即使可以證明有著大量被英軍雇用、為英軍提供勞役服務的漢奸,為英軍行動提供了便利,但其軍事價值實屬有限,對戰爭進程的影響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當我們分析漢奸在為英軍提供后勤補給、充當軍事行動向導,特別是提供情報以及為偽行政機關服務等方面的作用時,對其影響則不可小視: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英軍在后勤給養方面沒有遇到大的問題,漢奸“接濟”顯然“功不可沒”;英軍“反較我軍熟悉”路徑怪誕局面,一方面說明清軍不得民心,另一方面也證明充當“向導”的漢奸為英軍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就漢奸提供情報問題而言,以清軍的組織能力和戰斗力能否在戰場上擊敗英軍是一回事,英軍因獲取準確的情報而進行充分的戰斗準備和有針對性的軍事布署又是另一回事;服務于英軍所建偽行政機關的“紅毛鄉勇”等漢奸,在為英軍穩定占領區社會秩序、有效征集物資等方面,也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一些漢奸直接參與英軍作戰,執行清理河道、搬運軍火等工兵或后勤保障任務,更是為其軍事行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也就是說,雖然相對于中英雙方國力、軍事技術、軍隊戰斗力、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決策和組織能力等更為重要的戰爭要素而言,漢奸作用這類居于次要地位的要素對于鴉片戰爭的勝負并無決定性意義,清人對于漢奸的作用給予了不應有的重視并進行了夸張的描述,但對于戰爭的進程和形態而言,其影響仍不容小視。在鴉片戰爭中,英軍之所以能順利完成諸多具體作戰任務,并以英國政府能夠接受的極小代價達成其軍事行動的目標,漢奸活動在許多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有時甚至是難以替代的作用。
總之,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英國,加上英國軍事技術發達、國力強盛、英軍有著豐富的殖民作戰經驗,而中國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國內社會矛盾尖銳等多種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漢奸問題只不過是這些復雜因素中的一個小小要素。而在戰爭中,或因認知局限,或因利害相關,或出于滿漢間的民族猜疑,清政府對于漢奸作用的描述存在諸多曲筆諱飾和夸張不實之處,既使一些漢奸問題的嚴重性被過分夸大,也使一些應予關注的問題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清人完全不能正確、清醒地討論和處理漢奸問題,也從這個小小要素方面為清軍的戰敗添一注腳。
注釋
①③④⑧⑨[13][22]《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二》,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908頁、第870頁、第1106頁、第907頁、第661頁、第1038頁、第270頁。
②⑤⑥[18][24]《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一》,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353頁、第253頁、第316頁、第214頁、第328頁。
⑦⑩[11][21]《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四》,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017頁、第1708頁、第1691頁、第1667頁。
[12]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4頁。
[14]《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44頁。
[15][25]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9頁、第195頁。
[16]廣東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6頁。
[17]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全集:三》,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8頁。
[19][20][23]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3 頁、第 267 頁、第 13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