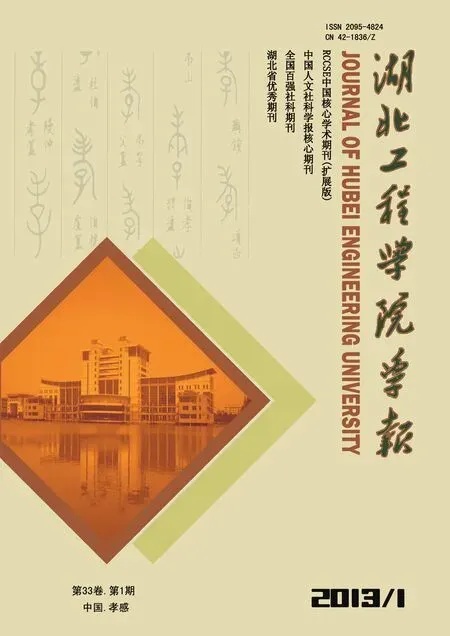民國《孝經》學研究略論
張付東
(西華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晚清民國,時局動蕩,政府更迭,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進入了一個急劇轉型的關鍵時期。伴隨著政府廢科舉、禁讀經的法令和一批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破除家庭”,“解放婦女”等社會思潮的興起,曾一度被尊奉為封建政府“官學”的儒家學說在與西學激烈的沖擊、碰撞、交融中漸趨衰敗,而作為儒學一個重要分支的經學也由沒落走向了滅亡。在倡導“科學”、“民主”、“新道德”的革命浪潮中,封建社會里維系宗法家庭、綱常倫理的孝道首當其沖,成為眾矢之的,而其文本表現形式的《孝經》也為人們所批判、唾棄。但文化的發展存在著一定的慣性,新與舊的交替總需一個較長的過程。因而,在文化轉型的民國時期,學術思想上更多地表現出的是一種新舊交織的局面。在反對《孝經》、孝道的浪潮中,亦有一些人在固守著,維護著。他們或是頑固守舊的前清遺老,或是接受新思想的一代教育家,或是保存國粹的社團成員等等。作為這一時期政治、文化領域不同身份的他們,雖在性格氣質上有著很大的差別,但其在學術思想上對傳統文化的保守傾向卻存在著某種一致性。另外,由于印刷技術的不斷改進,民國間出版了一些前代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孝經》學著作,這為《孝經》文獻的保存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更為綜合研究《孝經》者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材料。而北洋軍閥政府“尊孔復古”的“逆流”與倡導恢復讀經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孝經》的研究和《孝經》類著述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有鑒于此,在民國復雜的學術環境下,經過新舊學人的不懈努力,仍然出現了不少的《孝經》學佳作。本文試著對此作簡要的梳理并分類研究,以期拋磚引玉,為深入研究者作一鋪墊。
一、傳統《孝經》學的紹述與流別
《孝經》一書宣明孝道,古人奉之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鄭玄《六藝論》),為歷來學者所重視。進入民國以后,傳統意義上的《孝經》學伴隨著經學的滅亡,也漸次走向了終結。面對社會轉型中倫理道德的重構,一部分新式知識青年主張放棄傳統孝道,破壞宗法家庭,全盤西化。而另一部分有著深厚國學積淀,受傳統倫理綱常影響較大的人士則選擇了從故書雅記中尋求出路。他們在故國覆亡、彝倫斁敗的情勢下,或閉門謝客,專事疏證傳統儒家經典;或繼續堅守在教育一線,保存國粹,培養國學人才;或兩相兼顧,表現為雙重乃至多重的學術人格。基于他們的學行操守、性格氣質不盡相同,故而其在《孝經》學著述中所表現出的對綱常倫理的維護力度,以及在疏釋經文大義時,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程度都有著較大的差異。現擇其要者,略述如下:
1.“漢宋調和”派后勁之《孝經》學。四庫館臣謂:“漢京以后,垂兩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要其歸,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1]49漢學重考據,宋學長義理,兩家之爭難分軒輊,利弊互見。迨至晚清,又出現了一派“漢宋調和”的學術力量,其典型代表是“東塾學派”和“九江學派”。兩派學者不立門戶之見,各取漢宋所長,通經同時,力求實用。民國后,兩派后勁對《孝經》的研究最杰出者當推簡朝亮與陳伯陶二人。
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一卷,有民國間讀書堂校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收錄,另有臺北世界書局清人《十四經新疏》影印本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整理標點本。簡朝亮(1852-1933),字季紀,號竹居,廣東順德簡岸鄉人,學者稱簡岸先生。師從九江朱次琦,讀書“以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2],不立漢宋門戶。修身同時,力主通經以致用,窮畢生精力疏證傳統儒家經典,以求“正人心,挽世風”,為“九江學派”后勁。當丁巳歲(1917)季冬,《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完成后,簡朝亮乃思《孝經》為諸經之導,當集而述之,于是考于古義,酌于當時,徹夜不寐,越歲季秋,述草而成。其體式為疏體,書成后一度作為簡氏課徒時的講稿。是書首列今文《孝經》十八章經文,前有章名,后依次為簡氏注及述疏。縱觀全卷,注則集眾家舊注及經史可會通者,疏亦如是。“義蘊典制逐一詮釋,訓辨其得失,推究其所從出,他存疑正誤,補阮元《校記》之遺。”[3]837書末附有《讀書堂答問》一卷,計有88條,為簡氏授徒開講《孝經》時,答諸生問,辨舊說之匯編。其對《述疏》中所征引的舊注疏和涉及的名物典制,反復論證,詳加辯解,補之不足。檢覈全卷,尤多精妙之言。倫明說:“精粹尤在《答問》諸條,反復援證,務得其安”[3]837,充分肯定了該編的價值。簡氏推崇《孝經》為“導善救亂之書”,“立漢、唐良制”,有著明顯的階級考量。至于他所指出的《孝經》家舊說所失者,持論較為允當,多為可取。有關簡氏生平及著述的思想脈絡,《孝經集注述疏》的編纂、特色、影響等方面,拙作《論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一文已詳之,此不多述。
陳伯陶《孝經說》三卷,1927 年香港奇雅鉛印本,臺灣《民國時期經學叢書》收錄。伯陶(1854-1930),字子礪,廣東東莞人。早年拜粵中大儒陳澧為師,好學多才,精通經學、詞翰、書畫、地理等。宣統辛亥(1911)后,為避戰亂,攜眷移居九龍,屏絕人事,專心著述,以此終老。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論《孝經》與《春秋》相表里。陳氏認為《孝經》是“孔子成《春秋》后,因為曾子陳孝道,而曾子之徒記述之”[4],而《孝經》中稱述《詩》、《書》者,正是《孝經》與《春秋》相表里之證。所謂的孔子《春秋》為亂賊作,實為魯國作。他說:“魯之君被弒者四,被戕者一。魯史緯國惡,書薨書卒,亂賊之罪不明,孔子以屬詞比事明之。夫大孝尊親莫過于舜,而《孝經》不稱舜而稱周公,則為魯作可知也。”[4]中篇言曾子學行傳授皆本《孝經》。他認為曾子畢生謹守《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數語,三省其身,并教之弟子。曾子著《大學》,子思受其業作《中庸》,兩書皆本“忠恕”一貫之道。下篇論《孟子》本《孝經》以辟楊、墨。此篇承襲其師陳澧“《孟子》于《孝經》多所發明”一說,并多作演繹。陳伯陶認為“孟子言楊、墨無君無父,蓋實有所見。雖楊、墨書亦言仁義忠孝,要皆诐淫邪遁之辭,奈何以《孝經》之義附會之乎”[4]。全篇繁征博引,駁斥了《墨子》中的“三日之喪”、“薄葬”、“兼愛”諸說。篇末陳氏又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非孝”思潮,大加訓斥并寄以深慨。吳道镕在《孝經說·序》評論該書為“博而實,辨而覈。以閑圣道,如棄鱗爪而得元珠;以辟诐淫,如懷重寶而與環敵相抵柱也”[5]。所論可謂中肯。
2.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近代教育家對《孝經》的紹述與研究。辛亥革命后,清廷覆亡。一部分晚清學界功名在身的遺老們接受不了社會巨變的現實,屏絕人事,閉門著述,過起了隱居的生活。而另一部分感時憂世之人,則選擇了繼續堅守教育陣地,由舊式的封建“學究”蛻變為新時代的教育大家。由于他們受傳統的倫理綱常影響較大,故而在其授徒與講學中亦過多地包含一些傳統的甚至是保守的思想成分。
民國初年,施氏(肇曾)醒園刊刻的《十三經讀本》中收錄了明代黃道周的《孝經集傳》,書后附有唐文治的《孝經大義》一卷。唐文治(1865-1954),號蔚芝,江蘇太倉人。幼稟家學,熟通性理、訓詁之學及文章義法。曾歷任清廷要職,并造訪過日、英、比諸國,對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有較深的認識。民國后繼任南洋大學、無錫國專校長,對保存國粹,培養人才做了較大的貢獻,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孝經大義序》中說:“家庭之間一愛情而已矣,一和氣而已矣。和于家庭而后能和于社會,和于社會而后能和于政治,和于政治而后能和于光天之下,到于海隅蒼生。”[6]闡明了家庭和睦與政治安定、社會和諧相輔相成的關系,這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非孝”、“家庭革命”等思潮作了有力的回擊。書中唐文治釋“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的“則”字為模范、人格;闡釋“養則致其樂”為“父母之壽否,系于心境之郁舒。為人子者,不可不隨時加省也”[7]。這些都表明唐氏在對《孝經》做傳統意義上的研究的同時,更多地包含了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他還撰《孝經救世篇》(又名《孝經翼》)一書,以期救世。其在序言中說:“惟天下多無本忘恩之徒,于是意氣紛呶,爭奪相殺,倒戈相向,而生民實受其殃,吾為此懼,爰作《孝經翼》以諗來茲。《孝經》載其綱,而此則及于節目;《孝經》言其大,而此則涉于淺近者也。”[8]可知,唐氏著是書作為《孝經》宏綱的羽翼,全篇貫通《論語》、《孟子》、《禮記》、《呂氏春秋》、《論衡》等經子書中的孝論尤多。另外,1944至1945年間,他還在《大眾》上分期刊登過《孝經講義》的部分內容,所論淺易明白,要之為課訓童蒙之講稿。
陳柱師從唐文治問學,于經學、文學、書法皆有較深的造詣,著《孝經要義》一書。書中列今文《孝經》十八章原文,后集丁晏《孝經征文》、阮元《孝經校勘記》、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唐文治《孝經大義》等各家釋義并稍加按語。書前有《大綱》一文,分述《孝經》傳授,《孝經》今文之古,古文經傳之偽,《孝經》鄭注,《孝經》為六經之本,《孝經》與《論語》并重,《孝經》之學在明順逆,《孝經》之學在培養生機等。縱觀全書,所論平平,大致為陳氏課徒時的講義。此外,佐藤廣治作《孝經在經學上地位之考察》一文,乃綴拾宋儒以來疑《孝經》之說匯集而成。陳柱撰《孝經辨》針鋒相對地對佐氏之疑加以駁斥。如佐氏文中申述了《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與《左傳》中語句類似,并說“(釋此句)不是附會,則不能得妥當之解釋”。[9]陳柱辯論道:“此古之公言……簡朝亮曰:昭十六年《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今《論語》皆述之,其例也。然則《論語》亦剽竊《左傳》而成者耶?”[10]諸如此例,陳氏之文皆有理有據地反駁了佐氏所論。
此外,諸如廖平《孝經學凡例》,列二十七條研究《孝經》的凡例,分節設目,俱關切要;馬其昶《孝經誼詁》,解經廣征博引,不分門戶,誼求其是;曹元弼《孝經學》、《孝經鄭氏注箋釋》、《孝經集注》、《孝經校釋》,以禮解經,于《孝經》一編反復申述,闡明經文大旨的同時,又力求便于訓教童蒙,還身體力行踐履忠孝仁義等等。要之,與上述各家所論相差不大,皆為新時期傳統《孝經》學的紹述與流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實現了從資產階級革命派到保存國學的國粹派轉變的章太炎,在其《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一文中說:“《孝經》為經中之綱領,句句系自天性中來,非空泛者可比。”故而,他認為那些講新道德者和提倡家庭革命者反對《孝經》無論如何激烈,都毫無效用。而他的《孝經本夏法說》一文,則著重探討并證明了《孝經》所述典實皆為夏制。如其所論,可為判斷《孝經》的成書年代提供有力的參考。
二、“后經學時代”的《孝經》綜合研究
馮友蘭曾把中國的傳統學術分為兩個時期,他說:“就歷史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11]若依馮氏所言,那么自漢至清就是中國學術史上的“經學時代”。辛亥革命后,帝制被廢除,經學的合法性依據蕩然無存,面臨官學失位的處境,但其在學術思想上仍具有一定影響,學者習慣稱這一時期為“后經學時代”。所謂的“后經學時代”,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社會政治層面上,“經學失卻其合法性依據的地位,中國社會形式上走向法理化的時代”;學術文化層面上,“對經的研究不必站在宗經的立場上,同時,任何學術文化的見解,都不能通過政治手段來定于一尊,也即走向思想多元化的時代”。[12]
探討經學離開了傳統的經典文獻,無疑如“樹失本、水失源”。故而,在探討“后經學時代”的《孝經》綜合研究之前,對這一時期《孝經》文獻的著述與出版情況作一簡要的考察就顯得非常必要。《民國時期總書目》雖著錄了鄔慶時《孝經通論》、蔡汝堃《孝經通考》、沈顏閔《孝經講疏》等十五家民國間出版的《孝經》類著作,但仍存在較多的漏略,如簡朝亮《孝經集注述》、馬其昶《孝經誼詁》、宋育仁《孝經正義》、張栩《孝經淺釋》等等皆未著錄。另外,民國年間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大系統編輯出版的諸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等大部頭的叢書,亦收錄了不少前代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孝經》類著述,這些都為學者系統、綜合研究《孝經》提供了翔實的原始資料。當然,民國間學者對《孝經》的研究,也因派別、立場、學術導向等方面的不同,呈現出一種各家“爭鳴”的現象。
1.尊孔組織的《孝經》綜合研究。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的飛躍。但革命成果旋即被袁世凱竊取,中國進入了外有列強侵略,內有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而社會上中西、新舊各種思潮的碰撞、交融,又造成了國民信仰危機和社會道德失范的局面。面對這種狀況,安定社會秩序,重新構建道德、價值規范,樹立國人信仰,成為了社會的當務之急。不少民眾認為只有回歸傳統的倫理道德,才是救治社會弊病最有效的途徑。為此,在康有為等人的倡導下,各地以“讀經尊孔”為宗旨的“尊經會”、“讀經會”、“孔教會”等尊孔組織紛紛建立。因孝道是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支柱,故而《孝經》無疑是這些尊孔組織最熱衷宣揚的。
姚明輝(1881-1961),號孟塤,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民國間上海孔教會成員。1906年他與友人開創上海西成小學,任讀經之課,授學童《孝經》。民國建立后,頒令廢除讀經,西成亦終止向孩童授《孝經》。姚氏認為長此以往“教育浮偽,教化衰微,民俗將不可問”[13]。遂與西成小學校長凌樹燾相議恢復向學童授《孝經》,并校印《石臺孝經》作為教材,記《孝經》源流、版本、章句、音義諸端成《校印孝經讀本序例》列于書前,且制定詳密的授課計劃。他曾輯有《孝經鄭注考實》二卷、《孝經音義考補正》一卷,后又著《孝經讀本姚氏學》一書,以闡發精微。如謂“人之性命,一受于天,再受于父,三受于母。母最后最親,天最先最尊,父不先不后,故尊而兼親。鳥獸第知所最親者,而圣人能知所最尊者,故鳥獸僅得為母之子,而圣人乃得為天之子”[14]32。發明生三事一之道,以闡釋資愛、資敬之義。又謂“《天子章》所稱者,唯天子一人所當盡之孝,而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所共由之孝未及焉。《諸侯章》所稱者,為諸侯以上所當盡之孝,而諸侯與卿大夫、士、庶人所共由之孝未及焉。卿大夫、士章所稱者,亦為卿大夫、士以上所當盡之孝,而與庶人共由之孝不與焉”[14]21。以別“五等之孝”。另外,他還特別指明圣人之教優于一切宗教,圣人之政優于一切政治學說等等。他處處以“尊孔”、“復古”、“讀經”為旨,動輒以言階級差別、綱常名教,悍然以衛道自任,所持論調具有強烈的時代性。
鄔慶時《孝經通論》四卷,有南村草堂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鄔慶時(1882-1968),字伯健,號白堅、楷才,廣東番禺人。辛亥革命后,曾在民國政府、大元帥大本營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任職。他是陳煥章的弟子,孔教會成員之一,且對地方史志的研究和編纂有獨到創見。鄔氏在《孝經通論序》中闡述了他作書的經過:“民國十八年,大病幾殆,足不良行,以讀書自遣,偶讀《孝經》,頗有所得,遂節搜集古來孝經家言。及步履稍健,復至京內各圖書館讀所未見者。其所未盡,復向南京國學圖書館借抄。因總括所見,本諸心得,摘其大要,厘為十篇,顏曰孝經通論。”[15]是書四卷,分為十篇。作者第一,論《孝經》為孔子所作;時代第二,論孔子作《孝經》的時代背景;經文第三,論今古文《孝經》各本在經文與字數上的異同;章名第四,論《孝經》之分章;條理第五,論孝道之外延;大義第六,條列《孝經》倫理、政治方面之大義;會通第七,論《孝經》與群經的關系;批評第八,雜引古今褒貶《孝經》者;表章第九,謂《孝經》之義不為庶人而發,討論歷代表章《孝經》之故事;傳述第十,敘傳授《孝經》之經師及其著述。縱觀全書,“議論雖平平無奇,而引證頗詳,最便參考”[3]837。
還有一部《孝經通論》是羅功武寫的。羅功武(1878-1935),別號勇忠,高明荷城街道羅岸村人,民國時期廣西著名教育人士。全書列《孝經》之旨、《孝經》稱經、《孝經》非孔子親筆所作、《孝經》之藏與傳述、《孝經》今古文之異、主孔鄭注之爭、《孝經鄭注》非鄭玄、《閨門章》非后人偽造亦非司馬貞所削、隋出《古文孝經》非劉炫所偽造、章次分析之始、宋儒刪引《詩》《書》分析經傳及疑經之非、《孝經》非襲用《左傳》、《孝經》與群經大義相通等十六目。相比而言,此書較之鄔氏《通論》成書時間稍晚,內容略顯粗糙,雖有蟄廬刻本,但雕工不細,且存在一些訛誤,因而其流傳不廣,影響也很有限。1949年以后,該書在大陸很少見到,有臺灣《民國時期經學叢書》影印的民國二十二年蟄廬刻本。
如上所述,姚明輝的《孝經讀本姚氏學》仍沿用傳統的研究方法,注重對《孝經》逐句逐條的詮釋。而鄔氏、羅氏兩《孝經通論》則更傾向于對《孝經》作整體、系統的研究。這反映了“后經學時代”《孝經》研究的一個趨向,而尊經會的《孝經救世》把《孝經》研究神學化則代表了另一種趨向,將于下文詳述。
2.古史辨派對《孝經》的懷疑與批判。晚清今文經學盛行,引發了今、古文間的激烈爭辯,在雙方的論戰中,疑經辨偽的精神得以光大。在以后的發展中,這種疑辨的風氣又逐漸從經學研究范疇擴展到了史學研究領域,學界達成了重新審查古書與古史的共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直接促進了20世紀初古史辨派的興起。古史辨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研究史學與經學的學術流派。該派發揚了實用主義所包含的懷疑和實證精神,以“辨偽”、“考信”為務,是“五四”以來激進的反傳統意識在純學術研究領域內的反映。疑《孝經》者,前已有宋之朱子,其作《孝經刊誤》一書,率意割裂、刪削舊文,為后代學者所效。待至清初,姚際恒作《古今偽書考》,則直列《孝經》入偽書。學者喧喧,莫衷一是。古史辨派的代表性著作《古史辨》中,亦有不少疑《孝經》的論斷。
《古史辨》中收錄了王正己的《孝經今考》一文。王氏認為“清代考據精詳,堪稱造極,可是《孝經》一書,所考不是失于紛雜混亂,就是犯了囫圇吞棗的毛病”[16]141。因此,他撰此文希冀用科學的方法,分條別項地逐條批駁,理出《孝經》的源流及偽跡,給《孝經》作個總賬。文中他在考察今古文《孝經》的沿革,對比兩者經文、字數差異的基礎上,引用鄭珍駁日本回傳《古文孝經孔傳》之偽的十證,來判定日本傳來的《古文孔傳》是偽中之偽。接著他又從文字、引書例證、漢初知識界的趨勢等幾方面證明《古文孝經》是依今文偽造的。有關偽造者為誰,因《隋書·經籍志》云:“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王氏認為劉向校經籍時,《古文孝經》已經存在了,當為劉向之前無名氏托文而作的。《孝經》的作者問題,之前已有孔子說、七十子之徒說、曾子說、曾子門人說、子思說、齊魯間陋儒及漢儒說,王氏對以上諸說各個駁斥并予以排除。他結合陳澧“《孟子》多與《孝經》相發明者甚多”的觀點,又條舉他例加以論證,認定《孝經》的內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作《孝經》者當為孟子門人。當然對于《孟子·離婁篇》中父子間“不責善”與《孝經》中“當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的經義相違處,他猜測道:“《韓非子·五蠹篇》里有個故事‘楚人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很像《孝經》中父子諫諍的主張。大概這個故事流行于戰國末年,孟子門徒因思想不穩固而受渲染了。”[16]171王正己還認為稱經始自《莊子》,而《呂氏春秋》也曾引用過《孝經》,這都證明了《孝經》成于莊子之后,且不會晚于《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綜合而言,王正己疑《孝經》者論證牽強,且有太過之嫌,那么他給《孝經》作出的“總賬”中就難免有偏頗之處。
民國間,蔡汝堃對《孝經》的研究可算是蔚為大宗,其著《孝經通考》一書,收入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小叢書》之中,《古史辨》亦收錄了該書的部分章節。該書詳細考證了《孝經》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孝經》之古今文異同、今文《鄭注》與古文《孔傳》的真偽、《孝經》的批判等問題。他綜合分析了歷來有關《孝經》作者之爭的八說,如孔子說、曾子說、曾子門人說等,認真考量各說的來源和理由,條分縷析地加以駁斥和否定。他認為之所以有這么多的分歧原因有二:在觀念上總喜歡托之于圣賢;在論證上或失于空壑,或失于孤證。有鑒于此,他宣稱用探源的方法,察其所由,究其始末,析其客觀事實,驗以精確證據。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因《呂覽》曾引《孝經》語,故先秦時確有《孝經》,但《孝經》文簡義少,傳誦不多,秦焚書遂致亡佚。漢初儒者乃襲《呂覽》及《左傳》、《韓詩外傳》、《孟子》等書編纂而成今日所傳之《孝經》。蔡汝堃還對較了今、古文《孝經》在分章、文字上的不同,認為兩者僅為部分文字改頭換面而已,意義絕無相異,他還判定古文《孝經》實為西漢末年之人依照今文《孝經》偽作的。最后,他還條舉了歷代帝王及學者對《孝經》的批判,認為“《孝經》講孝,完全站在統治階級之立場,對象非在事親,而在忠君。此種思想,在宗法社會,固無不可;而當今思想開放,學術求真之時,殊不可迷信此書崇為圣經法典”[17]。可見,蔡氏想通過綜合客觀地研究《孝經》,撥開其神秘的面紗,給當時倡導讀經、神化《孝經》的舉動以迎頭之擊。蔡汝堃還作了《孝經》流傳圖和集目考略表,對歷代《孝經》的流傳和著述作了詳細、直觀的介紹。
此外《古史辨》中還收錄了周予同的《孝與生殖器崇拜》一文,主要探討“孝”思想的來源,以斥責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倡“孝”風氣。周予同亦是疑史派學者之一,他不從迷信的角度去弘揚經學,而是從史的角度去研究經學,并把它確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為中國經學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強迫各級學校恢復讀《孝經》的做法,他又作《孝經新論》,深層次地剖析了《孝經》與孔子思想無關聯及其在封建社會備受歡迎的經濟、階級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根本性地否定了《孝經》。他說:“《孝經》的思想并不是現代中國所需要,要將中國從危險的局勢中拯救出來,非先打破中國宗法制度和家族道德的保護論的《孝經》不可。”[18]
總之,古史辨派對《孝經》的研究,在承襲宋以來疑《孝經》者論題的基礎上,或稍加修飾,或資以新證,或為了立論不惜免為曲說。這為針砭時弊,破除舊道德,推動社會思想的進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因他們所疑過甚,某些論點有偏激失實之嫌,不免為后人詬病。
3.現代新儒家對《孝經》的弘揚與研究。現代新儒家與上述的古史辨派一樣,都是“后經學時代”學術思想逐步走向多元化的趨勢下,從傳統學術內部蛻變而來的學派。具體指,“20世紀20年代產生的,以接續儒學‘道統’為己任、服膺宋明理學為主要特征,力圖用傳統儒家學說融合、會通西學,從文化上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思想流派”[19]。因而,該派學者對“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的《孝經》及儒家文化原發性起源的孝道,則不可不予以重視和弘揚。
馬一浮(1863-1967),是現代新儒家學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治學本程朱而通陸王。他研求六藝,以為六藝統攝一切學術而自身又統攝于一心,孔圣之學,博說有六藝,約說則有《孝經》。在他看來,自漢代以來,先儒雖對《孝經》有不少的疏釋,但“于根本大義,似猶有引而未發,郁而未宣者”[20]212,于是作《孝經大義》一卷以明之。卷首有《序說》以明作書之由,《略辨今古文疑義》則辨析了《孝經》文獻及今古文流傳過程中的諸多疑案,其后依次分釋“至德要道”、“五孝”、“三才”、“明堂”、“原刑”,對孝道的“本能性、自然性、至善性、至美性、普適性、制度性,都進行了深刻的哲學思考和理論闡述”。[21]364-365馬一浮認為《六藝》皆以明性道,陳德行,而《孝經》實為之總會。他說:“《詩》、《書》之用,《禮》、《樂》之原,《易》、《春秋》之旨,并為《孝經》所攝,義無可疑。故曰:‘孝,德之本也。’舉本而言,則攝一切德;‘人之行,莫大于孝’,則攝一切行;‘教之所由生’,則攝一切教;‘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則攝一切政;五等之孝,無患不及,則攝一切人;‘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則攝一切處。《孝經》之義,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六藝》之宗,無有過于此者。故曰:‘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20]212另外,他釋“至德要道”、“五孝”、“三才”諸論皆“鞭辟入里,發人深省,前無古人,后無來者”[21]365。
新儒家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謝幼偉曾作《孝與中國文化》一文,以明孝在中國文化上的作用與地位,并探討今后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提倡孝之必要和價值。該文主要從道德、宗教、政治等方面來考察傳統意義的孝,謝幼偉提出了“中國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孝的文化”[22]67的主張。具體而言,道德方面,他認為孝雖與家族本位有關,但不僅僅局限于此,實際上它已超出了家庭、宗族本位之上。先儒提倡孝的用意,實在于“認孝為道德之本、道德起點、道德之訓諫”[22]68三方面,數千年來所以維系國家道德者,一孝字而已。宗教方面,謝氏指出孝具有構成宗教三要素(對超人或超自然勢力之崇拜,得救之希望,情志之慰勉)的特質,《孝經》中的孝思追遠、以父配天的思想就充分體現了宗教的思想。雖然中國的儒者表面上不談宗教,實則孝完全可作為宗教的代替品。政治方面,謝幼偉反對某些學者認為《孝經》所提倡的孝是封建帝王鞏固自身地位的工具的觀點。他認為《孝經》之孝絕不僅為帝王設想,而是儒家用孝以“感化君上,破除階級之分,成立鄉治”[22]75-76。如《孝經·天子章》即告誡君主要行孝愛民,而“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說法,明顯地帶有不以階級限制人民進身的意味等等。最后,謝幼偉又進一步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實質性區別在于西洋文化忽視了內發之愛,這樣勢必會造成父子寡恩、交征以利的后果,而《孝經》所倡之孝正可以來彌補其不足。因而,在今后的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發展中提倡孝是非常有必要的。
此外,新儒家學派的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等人,或把孝看成是孔教的要旨,或在“非孝”浪潮中竭力維護孝道在傳統倫理中的地位,或宣揚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教的、社會的意義。要之,皆極力推崇《孝經》與孝道,此不贅述。
三、《孝經》學發展中的“異端”及其他
清末以來,隨著西方宗教思想的不斷傳入,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在與之激烈的碰撞、沖突的同時,對其教旨、教義亦有所吸收。民國間,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不少憂時之士都從本階級的立場出發尋求救國救民之道。部分孔教會的成員為了維護舊的傳統與制度,極力推崇并神化《孝經》,以期用《孝經》來救世,這就使傳統的《孝經》研究走向了“異端”,像《孝經救世》一類的著述便應時而出。此外,這期間有關《孝經》的目錄學著作《續修四庫全書·孝經類提要》以及學界對敦煌新出土的《孝經》文獻的研究等方面都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1.神化《孝經》的《孝經救世》。濟南伏志先署《孝經救世》(又名《孝經德教》)是尊經會的一批遺老宿儒在1944年-1947年編輯出版的,全書分9冊共20卷,通篇以“不孝子”加按語來發表議論。尊經會是民國間尊孔組織之一,其成員尊崇孔子,并尊奉孔學為孔教,且認為孔教優于世界一切宗教。《孝經救世》中處處體現這種思想主張,“不孝子”認為讀經首須尊經,而尊經則首先應該尊孔。他們認為孔子有立萬世之法的功勞,雖生前未得爵位,實乃被代代尊奉為王,謂“由受命言之,孔子為素王;由繼周言之,孔子為新王;由作經言之,孔子為今王;由立教言之,孔子為先王”[23]13。
他們夸大孔子并尊奉他為萬世之王的同時,還不斷地神秘化孔子與《孝經》。如謂“孔子以口舌流通藏元,如澤之夾于天矣,而作《孝經》以救萬世,法施大矣”[23]7。四庫館臣認為《孝經》一書“文義顯明,篇帙簡少,注釋者最易成書”[1]846,多為學者贊同,但《孝經救世》中“不孝子”則不這么認為,他說:“《孝經》全篇,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海流淺,風雨烏能亂其波濤哉!”[23]卷首11“《孝經》之文合天地中和之聲,先得(夫)〔天〕下萬世人心之所同然,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天地之元音也。然其義蘊宏深,難于知盡。”[23]4即“不孝子”認為《孝經》雖表面通俗易懂,實則義蘊宏深難于盡知,故而“兩千四百二十一年來注解四五百部,皆管窺耳”[23]17,這樣就給言簡意賅的《孝經》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孝經救世》之所以顏其名為“救世”,這在近代史上自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考核全書,我們不難發現其所救之“世”并非僅指狹義上的中國,而是指全世界。“不孝子”謂:“《孝經》之義,現在猶未大明,必俟其義至于大明,乃因書同文,而行同倫;乃以先進大明之中國,教化后進之各國;漸訖四海,明照萬國,大同天下,致治太平;及夫天竺、猶太、伊斯蘭三流,亦既被化,則亦謂《孝經》不難知也。”[23]4由此可知,“不孝子”極力宣揚孔教與《孝經》,其目的是讓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不論種族、宗教信仰、文化思想同否都能披化《孝經》之義。該論希冀建立一個“書同文”、“行同倫”整齊劃一的世界,卻忽視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注定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
另外,“不孝子”在疏釋經文時,動輒以引緯書之言,并雜糅佛、道所論。如釋“仲尼居,曾子侍”謂:“‘仲尼居’三字,義如夬卦見。釋迦摩尼佛說《楞嚴經》,佛弟子稱曰‘大佛頂’義類此。佛托阿難而說,亦類至圣托曾子而語矣。”[23]6凡此種種,在儒、釋、道各家討論優劣之時,雜糅三家之說于一編,有一定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但從單純的研究儒家經典方面,這樣不擇優劣,不分派別,雜糅眾家之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且在那個對《孝經》、“孝道”激烈批判的時代,這樣不倫不類的著述,不但起不了弘揚《孝經》的作用,反而更加重了人們對它的厭惡之情。
2.《孝經》目錄學著作《續修四庫全書·孝經類提要》。清光緒年間,就有大臣上疏請求續修《四庫全書》,但因時局動蕩,經費無著落,所議未果。入民國后,仍有一批學者議修此事。倫明即為其中之一,他言其書齋為續書樓,并廣為購書訪遺匯集資料,并撰寫了不少的《提要》。1927年,日本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經費,籌措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聘請海內外專家碩學撰寫《提要》。《孝經》類提要主要由倫明寫成,據中國科學院整理本《續修四庫提要·孝經類》統計,其收錄的《孝經》類著述(含緯書)約150部。倫氏對各書所評多客觀精當,但因當時復雜的社會局勢,《續修四庫提要》成稿后未經嚴格的審訂去取,保存下來的亦僅為當時的稿本,故其中存在訛誤也在所難免。隨著學界對《孝經》學系統研究的加深,《提要》中存在的不當地方越來越多地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如臺灣學者陳鴻森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辯證》一文,對《提要》中說有可議者提出商榷,并訂訛補闕,多所創獲。現據淺顯的認識再補正一二條于下:
《孝經集解》條:清桂文燦撰,文燦字星垣,又字子白,廣東南海人……按陳澧《東塾讀書記》,言《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今按書中未及闡發此意,特為補入。[3]829-830
由所引可知,倫明認為桂文燦字星垣,又字子白,且把陳澧與桂星垣所論者補入《孝經集解》條下。考之史書,桂文燦之兄桂文耀字星垣,因而倫明混淆了兩人字號,并把陳澧與星垣所論《孝經》者補于《孝經集解》條下就不恰當了。又如倫明在評價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時說“曰集注述疏者,注為唐明皇《御注》,疏則邢昺疏”,檢核全書,注則匯集了《孝經》鄭氏解、韋昭《孝經注》、唐玄宗《孝經御注》、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等眾家舊注及經史可會通者,疏亦如是。故而,筆者以為認定該書為簡朝亮“自注自疏”[24]較為妥當。
3.《孝經》出土文獻的研究。清末以來,敦煌《孝經》殘卷等文獻的發現,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孝經》學上一些前人所遺留下的問題或不太確定的觀點,都多多少少能找到直接或間接證據。蘇瑩輝《敦煌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敦煌新出北魏寫本毛詩孝經合考》,王利器《敦煌本孝經義疏》、《敦煌本孝經義疏跋》等文章對敦煌本《孝經》作了考證、補校與初步的研究。這些成果都為此后的陳鐵凡等學者對敦煌《孝經》抄本、殘卷的研究作了充分的鋪墊,也為傳統的《孝經》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北洋軍閥對《孝經》的提倡。他們或指定一些《孝經》方面的著述為教科書,并制定詳密的授課計劃;或資助再版一些已刊刻的《孝經》專著;或斥巨資雕版精印《孝經》,以貽戚友與幕僚等等。在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成為社會發展必然的趨勢之際,北洋軍閥出于對自己統治有用的目的,濫用民脂民膏來刊刻經書,大肆宣揚恢復封建倫理綱常的說教,必定會引起人們的反對與唾罵。但從保存傳統典籍這個角度上講,他們的行為又有著積極的一面。
四、結 語
經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略明民國時期《孝經》學發展之梗概。綜合而論,這一時期《孝經》學發展的社會背景是復雜多變的,且面臨著由傳統轉向現代的艱難處境。它在“中”與“西”、“新”與“舊”、“變”與“不變”、“孝”與“非孝”等社會思潮的激烈碰撞和融合中走過了近代。回顧這段風雨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孝經》學在文化轉型的民國時期發展的一些獨到的特征:(1)《孝經》所宣揚的“孝道”在社會倫理道德上失位,《孝經》多為時人唾棄,“非孝”思潮抬頭;(2)《孝經》的研究范圍從傳統的疏釋經文大義方面,逐步擴展到對整個《孝經》學綜合而系統的探討,且學者不必站在宗“經”的立場上去研究《孝經》,可以對它進行史的研究;(3)《孝經》學著述的現實針對性特別強,多涵抒時救世之憂;(4)《孝經》的研究有神學化的傾向;(5)出土文獻為傳統的《孝經》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6)在提倡白話文的潮流中,出現了一些白話文的《孝經》學著述;(7)部分北洋軍閥提倡《孝經》的政令也為《孝經》學的發展提供了某種程度的便利。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種內襲性的特點,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王權政治的世襲”,二是“家族倫理的孝道思想”。[25]民國以來,王權政治的世襲制度被廢除,而家族倫理的孝道思想也在“非孝”、“家庭革命”等反對浪潮中漸次式微。實踐已經證明,新中國文化的建設不能對傳統的東西一概否定,全盤西化,亦不可毫無別擇地去復古。站在時代發展的今天,要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倡孝道仍是題中之義。在倫理道德艱難重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強,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太成熟的情勢下,如何處理好現代家庭關系和親子關系,如何重構與和諧社會建設相適應的倫理道德規范,以上對文化轉型關鍵期的民國間的《孝經》學研究,或許能為我們找到合理答案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反思。
[參 考 文 獻]
[1] 紀昀,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孝經類[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任元熙.清征士簡竹居先生事略[M]//汪兆鏞.清代傳記叢刊·碑傳集三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183.
[3]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小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孝經類[M].北京:中華書局,1993.
[4] 陳伯陶.孝經說[M].香港:香港奇雅鉛印本,1927.
[5] 吳道镕.孝經說序[M]//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澹盦文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1.
[6] 唐文治.孝經大義·序[M].刻本.江蘇:吳江施氏醒園刊刻,1917:1.
[7] 唐文治.孝經大義[M].刻本.江蘇:吳江施氏醒園刊刻,1917:26.
[8] 唐文治.孝經翼序[J].學術世界,1936,2(2):80.
[9] 佐藤廣治.孝經在經學上地位之考察[J].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4,3(1):152.
[10] 陳柱.孝經辨[J].國學論衡,1936,(5):80.
[1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4:485.
[12] 陳少明,單世聯,張永義.近代中國思想史略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96.
[13] 姚明輝.孝經讀本序例[M]//尊經會.孝經讀本.上海:春江書局,1938:1.
[14] 姚明輝.孝經讀本姚氏學[M].上海:春江書局,1938.
[15] 鄔慶時.孝經通論·序[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1.
[16] 王正己.孝經今考[M]//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北京:樸社,1933.
[17] 蔡汝堃.孝經通考[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98.
[18] 周予同.孝經新論[M]//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42.
[19]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831.
[20] 馬一浮.孝經大義[M]//虞萬里,點校.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21] 舒大剛.讀馬一浮先生孝經大義二題[M]//吳光.馬一浮思想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2] 謝幼偉.孝與中國文化[M]//賀麟.儒家思想新論.南京:正中書局,1948.
[23] 濟南伏志先署.孝經救世[M].上海:尊經堂印,1944-1947.
[24] 張付東.論簡朝亮孝經集注述疏[J].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29(2):81.
[25] 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第4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