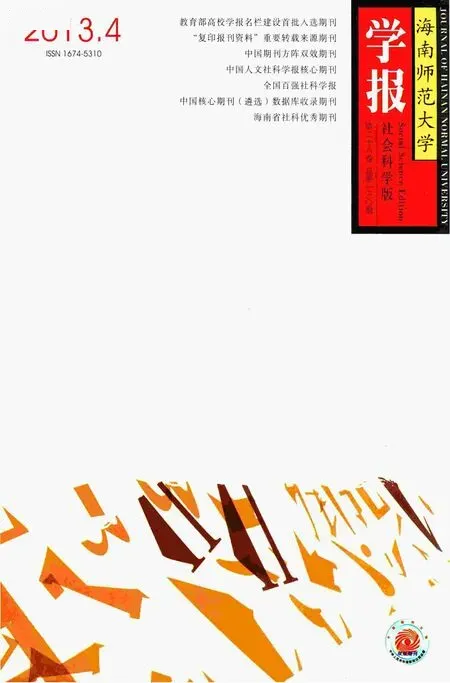論嚴歌苓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中的家庭倫理書寫
劉 云
(安徽大學 學報編輯部,安徽 合肥230039)
《第九個寡婦》在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又不斷再版,好評如潮。小說主要描述了一個叫王葡萄的女子,在土改中把被打成地主惡霸的公公孫懷清藏匿在自家紅薯窖內前后二十幾年的故事。這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寫的小說,具有強烈的傳奇色彩。在這部小說中,王葡萄在7 歲那年因為家鄉鬧災荒父母雙亡,在乞討路上被孫懷清買下做了孫家的童養媳,14 歲和孫家第三個兒子鐵腦成了親,結婚不久丈夫即亡故,在此之前婆婆已經去世,孫家其他兩個兒子都在外鬧革命,家中只剩下她和公公,共同經營一家小店鋪,還種著幾十畝地。因為孫家在當地算是家底比較殷實的,在土改時孫懷清被劃為地主惡霸要槍斃,在同一批被槍斃的地主惡霸里只有孫懷清僥幸存活,被王葡萄背回家中仔細調養并藏匿了二十多年直至壽終而亡。這部小說有著濃厚的儒家傳統文化色彩,尤其是對于家庭倫理關系的表現,更是顯示出儒家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家傳統文化是一種以家庭(族) 、血緣關系為中心而后推衍至全社會的文化,對于家庭倫理的建構成為其社會倫理的基石。家庭倫理關系在儒家文化中地位非常重要,“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中就有兩“綱”涉及家庭倫理,而君臣、朋友之間的關系也成為家庭關系在社會中的一種延伸。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觀念之后,經孟子的“五倫”之說再至董仲舒確立所謂的“三綱五常”,建立起一套完整嚴密的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體系。《第九個寡婦》在講述故事、塑造人物的過程中注重營造傳統家庭倫理的氛圍,比如王葡萄對家庭、對親人都極為重視與維護,具有鮮明的中華傳統美德,但是在此之外我們又能夠感受到一些與儒家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很不相同的現代思想因子,使這部小說顯現出較為復雜的思想文化底色。因此,本文試從家庭倫理中父子、夫妻這兩種最基本的關系出發來考察這部小說中的家庭倫理書寫,以期對嚴歌苓的創作特色進行深入把握。
一 父子
在這里出現的父子實際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相當于一個家庭中的長輩與晚輩的關系,不只局限于父子關系,也包含父女關系。父子關系是儒家傳統家庭倫理的核心,儒家理想的父子關系形態是所謂“父慈子孝”,這其中又格外強調孝,把孝視作一切德性的根本。為了履行孝道,孔子甚至主張“子為父隱”(《論語·子路》) ,孟子則不惜“竊負而逃”(《孟子·盡心上》) ,①關于這一點,學界存在較大爭議,具體可參見郭齊勇《儒家倫理爭鳴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鄧曉芒《儒家倫理新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郭齊勇《〈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可見孝在儒家傳統家庭倫理中的重要性。
在《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藏匿孫懷清的根本出發點即是孝。在當時極為嚴峻的政治背景下,王葡萄的行為屬于藏匿死刑犯,且是地主惡霸死刑犯,若被發現也是要被處以死刑的,但是她一點都不畏懼,她腦子里只有一個想法,這個人雖然不是他親生的爹,但是若沒有他,就沒有現在的自己;這個人不壞,不該被判死刑,若是這個人死了,她便再也沒有爹了。因此在后來的二十幾年里,無論中國社會發生怎樣的動蕩、經歷怎樣的政治風波,無論生活如何艱難,她都一如既往地用自己柔弱的肩扛起孫懷清的生命。她把這視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當她發現孫家二兒子也即她的情人少勇為了個人前途竟然主動向上級請求槍決自己的父親時,她便決定離開這個“不孝子”,甚至為此隱瞞了她已懷孕的事實。為了養活孫懷清,她狠狠心把剛滿月的孩子送了人,因為這個孩子會占用本已少得可憐的口糧。她把家里最好的東西留給孫懷清吃,寧愿自己忍饑挨餓,這與二十四孝中漢朝郭巨為母埋兒的故事何其相似。
但是我們再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孫懷清與王葡萄這對父女關系,實際上已經打破了儒家父子關系的傳統模式。
這首先在于孫懷清與王葡萄的關系是對儒家傳統家庭倫理中重男輕女模式的反撥。儒家傳統家庭關系中強調父子關系,因為女兒總是要嫁入別家跟人家的姓,只有兒子可以子承父業,因此,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出現的都是孝“子”,而無孝“女”。嚴歌苓在這部小說中卻顛覆了儒家家庭倫理中以男子為中心的傳統,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可以媲美二十四孝子的孝女形象。尤其是孫懷清與王葡萄之間的關系既非真正的父女,他們無血緣關系,也已沒有法律上的必然聯系,公媳關系隨著鐵腦的死亡自然解體,但是當孫懷清被劃為地主惡霸的情況下,連他自己的兒子都要與他撇清關系,這時王葡萄對于孫懷清的“孝”就顯示出不同于儒家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色彩。王葡萄的孝行在某種程度上更類似于《圣經·舊約》中出現的路德的形象。路德是拿俄米兩個兒媳中的一個,在拿俄米的丈夫和兩個兒子相繼去世之后,年老的拿俄米希望回到自己的故鄉伯利恒,她覺得沒有理由要求兩個兒媳與自己同行,大兒媳俄珥巴也更愿意留在娘家,而小兒媳路德卻決定跟隨老人,她認為自己既然嫁給了丈夫,就應該照顧好他的家人,這是自己的責任,況且拿俄米是那么慈善的老人,所以路德陪伴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但是這時他們已身無分文,連買面包的錢也沒有,路德就到田地里去撿麥穗。田地的主人波阿斯知道了路德的事情,就請路德吃飯,路德只吃一點點,把剩下的都拿給了拿俄米。拿俄米希望路德能夠幸福,就積極撮合了她與波阿斯的婚姻,路德與波阿斯仍然繼續奉養拿俄米直至去世。王葡萄與路德都是以兒媳的身份孝敬丈夫的父親,且始終以父親為第一位,奉養到去世,不離不棄。王葡萄與孫懷清沒有血緣關系,但是在對于孝的履行上,王葡萄卻比與孫懷清有血緣關系的孫少勇更為純粹,這不能不說是對儒家傳統男性話語的有力反撥。
其次,孫懷清與王葡萄之間不是儒家傳統中強調的尊卑有序的家庭關系,而是一種平等和諧的家庭模式。自王葡萄來到孫家,孫懷清對葡萄就非常關心、愛護,但這種關心又是非常有節制的,非常注意保護葡萄的自尊心,他們二人一直以一種平等的、像朋友一樣的關系相處。在這個家里葡萄是最能干的,也最能幫上孫懷清的忙,她收賬、打理店鋪,做各種活計,都是一把好手,他們又是合作者。孫懷清對待葡萄的方式也是形成葡萄自信、樂觀性格的主要因素。這有別于儒家父子關系中以父為綱,長輩與兒女之間命令與被命令、管教與被管教的上下關系。這一點在孫懷清對于葡萄情感問題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到。在鐵腦死后,王葡萄又經歷了幾段情感,孫懷清從沒有橫加干涉,甚至還為她的終身大事考慮、謀劃,王葡萄也絲毫沒有因為自己的情欲而對孫懷清有任何羞怯之意。王葡萄在情感問題上的獨立自主與任性而為都與儒家以夫為綱的倫理道德有悖,但孫懷清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一直很開明,他希望葡萄能夠擁有幸福的生活,這一點他很像拿俄米,顯示出對于葡萄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人格的尊重與關愛。這正是儒家傳統家庭倫理中嚴重缺失的。儒家的“孝”是與“敬”、“順”并置的,“敬”、“順”都會導致對于個人主體性的漠視,乃至最終喪失獨立思想與反抗精神。對于“順”的過分強調使儒家傳統文化缺少現代文化中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觀念,缺少對于個體人格的尊重,最終演變為魯迅筆下的“吃人”的封建禮教。但是在孫懷清與王葡萄的關系中,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反而對他們之間那種平等和諧的相處模式印象深刻,這種模式顯然不是儒家傳統家庭倫理所能涵蓋的,而是現代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思想對儒家傳統倫理規范的補充與修復。
再次,小說通過孫少勇的行為對儒家傳統孝悌思想進行了深刻反思。與王葡萄不顧生命危險全心全意照顧孫懷清的行為相比,孫少勇放棄老父、只為自己前途著想的行為則顯示出儒家所謂“孝”的局限性——儒家強調的孝悌之道往往成為社會倫理關系的縮影。《論語·學而》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也就是說,一個孝敬長輩的人,很少會冒犯上司,一個不會也不敢冒犯上司的人,則基本就不會作亂了。經過有子的這番論述,孝悌這一家庭倫理觀念的社會政治意義便一覽無余了。《孝經》中更是把孝敬父母與忠君直接聯系起來:“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在這里,“孝”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淪為一種政治工具,部分喪失了其本應發自于內心的人性之美。另外,儒家傳統的孝悌思想其實隱含著一個潛在的矛盾難以解決,那就是當孝與忠,也就是親情與國法發生矛盾、忠孝難以兩全的時候應該怎么辦。這一矛盾在實際生活中發展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孝”的心理與行為容易受環境影響發生變化。尤其是當“忠孝不能兩全”時,忠往往占據主導地位,孝退避三舍。如孫少勇對父親孫懷清的感情,隨著政治環境的不斷變化,其實質往往淪為不同情況下對自身利益的權衡。另外一個傾向則是為一己之私情無視他人權益或國家利益與法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以及“竊負而逃”都是這種情況的典型表現。儒家的孝悌思想經過兩千余年的發展變化,逐漸僵化,至宋明理學走向極端,終于成為嚴重束縛中國人思想文化發展的沉重鐐銬,也就是新文化的干將們極力要打倒的“吃人”的封建禮教。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說:“孝弟的范圍太狹了。說什么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滑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1]他之所以會這樣說,也就是看到了儒家孝悌思想對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王葡萄之于孫懷清,實際上就是孟子所謂“竊負而逃”這種思想的現實翻版。在王葡萄心中沒有關于政治、法律等等其他復雜的想法,她本著最基本的人倫思想對待孫懷清,把他藏匿于地窖,供養侍奉,外界種種國家、政治話語均與她無干。在這部小說所表現的當時中國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王葡萄的行為并沒有妨礙國家利益與他人利益,反而以堅守個人道德戰勝國家政治強權的行為使人性之美得以彰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對于私情的關照往往會超越道德、法律的界限,成為建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嚴重羈絆。
二 夫妻/男女
儒家對夫婦/男女之關系向來都很重視,孟子言“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孟子·萬章上》) ,可見這種倫理關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夫與妻這二者之間,儒家文化又講究男女的尊卑秩序。《周易》中以乾坤陰陽之說來為男女定位,《詩經》中的弄璋、弄瓦之說,都帶有明顯的男尊女卑的觀念。卑弱、順從、依附于男性是儒家文化對女性人格的要求。所謂“夫為妻綱”、“三從四德”更是強化了社會對于女性的這一要求,使女性完全成為男性的附屬品。“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伴隨著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傳播,女性解放也成為時代潮流,許多女性勇敢沖出封建大家庭的牢籠,尋求個人解放。新中國成立之后,男女在政治、經濟上的平等得到法律確認,可說是女性解放的重大勝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男性乃至整個社會對于女性的理想人格的期待仍沒有多大改變,溫柔賢惠的賢妻良母仍然是社會對于女性的身份定位與角色期待,也是絕大多數中國女性的自我要求。“溫柔賢惠”的背后隱含著怎樣的要求呢?首先是性格和順,其次是在工作與家庭二者之間要以家庭為重點、為中心,三是要吃苦耐勞,也就是要能夠成為男人的賢內助。這實際上仍然是儒家文化對當代女性的潛在影響。
閱讀《第九個寡婦》,我們可以發現王葡萄是個極為賢惠的女人,她有能力、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她還非常有女人味,是那種能把男人的生活照料得非常舒服的女人。因此,小說中的男人只要是和葡萄親近過,就都會深深地愛上她。在王葡萄身上,嚴歌苓表達了她對于傳統女性美的理解與向往。在她看來,女人美與不美,不在于外貌,而在于能不能以自己的女性魅力留住男人的心。小說中王葡萄是一個地道的農家女子,但她卻總是會用她充滿女性氣息的關愛使她身邊的男子不自覺地感受到成為她的男人是怎樣一種幸福。她勤快麻利又體貼,做家務是一把好手,她總是能給男人營造出溫暖的舒適感,讓男人可以身心都得到放松與休憩。這是對中國傳統理想女性形象的繼承。但是嚴歌苓筆下的王葡萄又不是一個依附于男性、沒有獨立人格的所謂“第二性”,這首先表現在王葡萄在守寡后并沒有恪守所謂婦德,而是勇敢追求自己的愛情。她先是愛上了戲班的琴師朱梅,并與之私定終身,但是身體孱弱的朱梅還是在動蕩的生活中早逝了,這段感情無疾而終。之后她又與自己原來丈夫的哥哥孫少勇產生愛情,但因為孫少勇的不孝行為,王葡萄忍痛離開了他。后來她愛上了有婦之夫冬喜,兩個人愛得熱烈纏綿,沒有因為寡婦或者有婦之夫的身份而受絲毫影響,就在冬喜決定要離婚娶她之后,一次災難使冬喜驟然離世。再后來,她又愛上了樸同志,一個來村里參加四清運動的干部,這次愛情像溪流潺潺,雖然后來二人沒有走到一起,樸同志也娶妻生子,但是感情已然在兩人心里扎根。最后,王葡萄仍然和孫少勇走到了一起。用王葡萄自己的話說,就是她的心可以分成好幾瓣,這些男人在她心里都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這與儒家傳統家庭倫理中對女性從一而終的要求背道而馳。不僅如此,對于葡萄來說,重要的是生命的實質,連婚姻之名也不那么重要了。
其次,在王葡萄對于性的主動迎合的態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她的獨立自主與反傳統特性。儒家傳統家庭倫理對女性舉止行為有明確要求,即要“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專心正色”(班昭《女誡》) 等等,總而言之,是要求女性壓抑自己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排斥外界一切聲色的誘惑與干擾,以合乎“婦德”。但是王葡萄顯然與儒家倫理所強調的婦德格格不入,她的身體豐腴充盈,處處都散發著雌性的誘惑,她對于性并不感到羞恥,也不拒斥身體的歡愉,而是陶醉其中。這在她與春喜的關系中表現得格外明顯。春喜是冬喜的弟弟,他與冬喜有點相像,王葡萄愛的是冬喜,不是春喜,這一點她自己非常清醒,但是她并不拒絕與春喜交歡。在她看來,她的身體是身體、心是心,她的身體和心是可以分開的。她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身體,也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心。這樣一種對待男女情事的態度已然與儒家傳統家庭倫理中以男性為中心、女人總是被動順從男性的狀態完全不同,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對于生命過程與生命本質的主動取舍,所表現的是一種非常純粹的現代女性觀念。
再次,王葡萄對待孫少勇的態度也明顯表現出她的自主性。王葡萄與孫少勇相愛后不久,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少勇的父親孫懷清被劃為地主惡霸,少勇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請求上級槍決自己的父親,王葡萄得知這一情況后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少勇,甚至隱瞞了自己已經懷孕的事實。她寧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跟著那個“不孝子”過所謂好日子。這就是葡萄,果敢、堅強又不失女性的溫柔賢惠,她從不懼怕生活的艱難、環境的險惡,以樸實的信念堅守著自己內心深處的道義,以自己的大智若愚顛覆了儒家傳統文化中男性智、女性順的倫理規范,守護與滋養著身邊的男性。王葡萄的形象與嚴歌苓之前塑造的小漁、扶桑等女性形象一脈相承,都是一種“包容的、豁達的、以柔克剛的性格”。嚴歌苓反對把女人作為第二性,而是強調女性精神與身體的主動性,并且認為女性的性感不單單在于外貌,女性的賢惠本身也是一種性感,[2]對男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這也是她筆下的小漁、王葡萄等等女性共同具有的特征。這樣,嚴歌苓既使她塑造的女性形象與儒家傳統文化中的理想女性有相契合的一面,又賦予其新的特質,實現了新舊兩種文化的水乳交融。
綜上所述,小說圍繞王葡萄這個形象衍生的故事情節,承載著嚴歌苓對于儒家傳統家庭倫理的深刻思考,這其中既有對傳統倫理的維護與繼承,比如對于孝行的倡導與贊頌,對于女性無私、賢惠特質的張揚等等,都滲透了濃厚的傳統色彩,使這部小說洋溢著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氣息,但是,在傳統的表象中我們又能夠發現作者對于儒家傳統家庭倫理的反思與超越,使這部小說對于家庭倫理的書寫顯得斑駁復雜。應該說,經歷了晚清民國思想的動蕩,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已漸入人心,對中國傳統的儒家家庭倫理觀念造成很大沖擊,時至今日,中國的家庭倫理基本參照西方社會的標準來執行,比如一夫一妻制,比如對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提倡等等。《第九個寡婦》的時空背景是上世紀40-70年代的中國農村社會,那個時候的中國雖然已經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但是在廣大農村社會,儒家傳統倫理規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這也成為嚴歌苓小說中家庭倫理書寫的背景,也是她在塑造人物時不能脫離的思想主線。但是多年的異域生活經驗使嚴歌苓得以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和思考。她曾經說過,到美國生活之后,她的思想觀念有一個“顛覆”的過程,她對于所有傳統的東西都開始質疑,不是“直接接受一些世俗的觀念再轉換成文字”,而是從一個“新的角度用含蓄的語言把道德仲裁權留給讀者”[2]。嚴歌苓對于傳統文化的這種態度與現代新儒家們有異曲同工之處。現代新儒家致力于以儒家文化為本,融合西方文化以改造儒家文化,使之更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第九個寡婦》中對于儒家家庭倫理的繼承、反思與超越,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現代新儒家們對中西文化互補、融通的思考,以文學的方式展現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與儒家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的可能性并使之在文學中落實到世俗生活中去,為現代儒家文化如何融入現實生活描繪了一幅可以想見的圖景,開拓出藝術創造的新生面。
[1]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 [J].新青年,1920,7(5) .
[2]方樂鶯.嚴歌苓:對所有傳統的東西都開始質疑[N].中華合作時報,2004 -11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