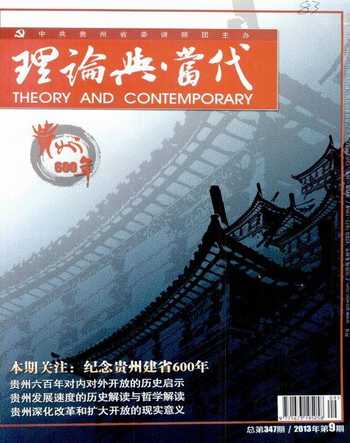“臨時工”——偽命題下的法律認知誤區
劉琴
一、“臨時工”用語的起源及發展
我國新中國成立后至1980年前,用工形式以“固定制”為主,國家按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把勞動者分配到用人單位,用人單位的用工數量、用工形式、用工辦法均由行政手段控制。除極特殊的情況和行政調配外,職工基本上是一次分配定終身,生老病死也完全由國家和用人單位包下來,勞動者得以分配后,即捧上了那個時期令人羨慕的“鐵飯碗”。這種用工無須簽訂合同,俗稱“固定工”或“正式工”,簽訂合同的一般是私營企業或是公有制企業的臨時工、季節工、輪換工等。“臨時工”一詞在國家正式文件中出現是在1954年5月勞動部頒發的《關于建筑工程單位赴外地招用建筑工作訂立勞動合同辦法》,其中規定“建筑工程單位至外地招用臨時工,不論招用期限長短,均應由招工單位(簡稱甲方)與工人或工人代表(簡稱乙方)按照工程所在地區勞動行政部門招工的規定簽訂勞動合同,并應嚴格遵守”。196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改進對臨時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暫行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因生產、工作需要,必須從社會上招用職工時,凡是臨時性、季節性的工作,都應當使用臨時工(包括季節工,下同);已經使用固定工的臨時性工作,應當逐步地改用臨時工。……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企業、事業單位,在國家下達的固定工年末人數和工資總額計劃指標以內,有權減少固定工,多用臨時工。在當時的用工體制下,“臨時工”作為“固定工”的有益補充,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但不可回避的是待遇身份上的差別巨大。當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后,這種矛盾日益激烈,對于用工制度的改革也就勢在必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一些地方開始試行勞動合同制。1983年2月《關于積極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提出:今后無論全民所有制單位還是縣、區以上集體所有制單位,在招收普通工種或技術工種的工人的時候,用工單位與被招用人員都要訂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勞動合同,規定雙方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1986年7月12日國務院發布勞動制度改革“四項暫行規定”,明確企業在國家勞動工資計劃指標內招用常年性工作崗位上的工人,除國家另有特別規定者外,統一實行勞動合同制;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在常年性崗位上招用的工人,應當比照該規定執行。同時細化了工人的招錄、待遇及勞動合同的訂立、變更、終止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伴隨著政策的出臺和指引,勞動用工制轉向以合同制用工為主發展,和企業原有的固定工制度并存,但這種“并軌制”也帶來了用工管理的困難。
1995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勞動法》頒布并施行,明確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期限分為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為期限”。各級政府也都根據《勞動法》的規定發布了勞動合同制度的實施方案,壟斷行業國有企業與地方企業同步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并得到了迅速推進,臨時工在新的用工關系中退出了歷史舞臺。1996年勞動部在對《關于臨時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問題的請示》的復函中明確:<勞動法>實施后,所有用人單位與職工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在用人單位各類職工享有的權利是一樣的,因此,過去意義上相對于“正式工”(固定工)而言的臨時工已經不復存在。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延續《勞動法》的規定,并進一步對勞動合同簽訂、解除等事項進行了補充細化。
二、“臨時工”詞匯在當今一再錯用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臨時工”這一用工形式早已淪為歷史,依照現行法律規定,根本就不存在此種用工形式,而囿于固有意識的干擾,“臨時工”一詞仍舊頻繁出現,用者行業各異、文化各異、表述各異,但實質所指已非原意。筆者認為面對這種現象,要樹立正確勞動法律意識,需對其中二個重要誤區明晰。
其一,對用工形式的認知不清。我國現存的用工形式依照最新勞動法規《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包括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工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合同工。此外還有派遣工及非全日制用工。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都是正式工作人員,不存在正式與臨時之分,只有期限的長短之別。前三種合同工均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直接簽訂用工合同,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如無法律規定的情形,則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論期限長短,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勞動者均依法享有法律規定的勞動權利,用人單位解除合同均須具備法定事由和遵循法定程序。勞務派遣指勞務派遣公司收集社會剩余勞動力,用人單位通過支付勞動報酬向勞務派遣公司租賃勞動力的一種就業模式,用人單位與勞務派遣公司的關系是勞務關系,勞務人員與勞務派遣公司的關系是勞動關系,與用人單位的關系是有償使用關系。2012年12月28日勞動合同法修改,明確勞務派遣用工不能成為用工主渠道,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時計酬為主,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累計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的用工形式,該種用工形式可以口頭協議建立。《勞動合同法》的規定除了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組織外,也同樣適用于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因此,現在社會上將通過聘用合同與企業、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稱為“臨時工”是不準確的,這些勞動者實質上都是該單位的正式員工,只是期限和形式上存在不同,并不是傳統意識中“想用就用,想不用就不用,沒有任何保障”的“臨時工”。
其二,對工作內容和職務行為責任承擔的認識不清。無論長期或短期用工,用人單位都要按照法律的規定,與勞動者簽訂規范的合同,明確各自的權利義務,同工同酬,為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從業培訓和安全生產條件,并依法為其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用,同類用工應適用相同的獎懲晉升機制。勞動者在履行職務活動時對外代表著單位,其所行使的權力來自于單位的授權,類似于民法中的代理。勞動者履行職務過程中存在錯誤或侵權,由此產生的責任應首先由單位承擔,其次再由單位按相關法規及單位規章向具體工作人員追責。因此文首所舉各類事件中,無論人員身份如何?單位依法應負的責任不可推卸。對于國家機關及事業單位,其用人程序與企業不同,公務員編或事業編人員是由編辦確定人員,每年通過公務員考試及事業單位人員招考錄用,福利待遇執行國家標準,經費大多由國家財政撥付,相應的解除、爭議解決等事項的規定也不同于勞動用工,而在此類單位中,通過簽訂合同聘用的其他勞動者則應適用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不同形式的勞動者在此類單位中的工作崗位會有所區分,大多從事一些輔助性工作,特別是一些有行政執法權的部門中,聘用合同制勞動者就不能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由行政機關具備資格的行政執法人員實施,因此在工作安排上不能混淆不清,既有違法之嫌,更會帶來編內人員不干活的負面影響。對職務行為中個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責任承擔中,在單位向外承擔責任后對內追責中,公務員編或事業編人員和合同制勞動者責任同一,而前二者同時還會受到黨紀政紀的處分。
三、“臨時工”事件矛盾發酵的內因及對策
近幾年發生的“臨時工”相關事件中,用人單位對于事件的處理通報往往會起反作用,不但不足以平息事件,反而導致群眾質疑不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單位在對相關用語概念混淆不清的前提下,做了各種不當的工作安排或處理。如有的行政單位在人員的工作內容安排上,不區分公務員編人員和合同制人員,將二者權能混一,社會公眾就當然會認為這類人員是替人干活但又無法“同工同酬”,情感因素會產生偏向,而二類人員的進入機制不同,合同制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培訓機會均無法與在編人員相比,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大。但基于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旦出現問題,如沒有更令人信服的事實和理由,公眾往往會先入為主地同情合同制勞動者,苛責編制內人員。所以當負面事件發生時,處理人員如果反應過慢或由于法律知識的欠缺,只是簡單通報一個原因或結果,反而激化了矛盾。而另一方面,一般民眾的法律知識也極為欠缺,對于不同用工形式沒有了解或知之甚少,先入為主地將“臨時工”作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以致在對事件的關注中往往因為情感取向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內容,僅憑幾個詞就去判斷事件中各方人員的是非曲直,這雖然可以促使相關單位、部門看到自身錯誤,但無形中也放縱或弱化了某些責任人。筆者認為在此類事件處理中,法律意識是首當其沖應該完善的,可運用各種現代媒介傳播相關法律規定,特別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尤其需要;公布涉事人員情況及處理意見,不瞞不躲,措辭嚴謹,合法合情,有理有據,才能有效化解民眾之疑;而民眾也不能盲從和無根據地懷疑,無論何種用工形式,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內運行,行為者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擔責,監督的對象不只是編內人員也包括編外人員,監督的標準是法律,不以法律為基礎的情感性主觀偏移無益于法制社會的健康構建。
(作者單位:六盤水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