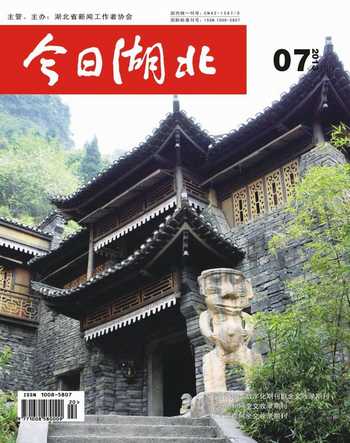我國違約金制度的完善
張倞
我國《合同法》對于違約金責(zé)任規(guī)定過于籠統(tǒng),且對兩種性質(zhì)的違約金沒有作出明確的區(qū)分,對約定違約金與其他違約責(zé)任形式能否并用的問題也規(guī)定得不明確,使司法實踐中產(chǎn)生很多問題。針對這種情況,筆者認(rèn)為,應(yīng)參照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做法,對合同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進(jìn)行完善,使之更加明確具體,準(zhǔn)確地區(qū)分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違約金,減少在法律適用上面臨的困境。
一、對約定違約金與約定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分別規(guī)定
既然法律規(guī)定了兩種不同的方式,就應(yīng)該有其實際的意義,如果能夠相互替代,則完全沒有必要規(guī)定兩種方式,因此,應(yīng)該在法律規(guī)定上對這兩種不同的責(zé)任形式作出分別的規(guī)定,進(jìn)一步厘清此二者的關(guān)系,明確其具體的適用范圍,以及在適用上有重合的矛盾應(yīng)如何解決。因為單純懲罰性質(zhì)的違約金和約定的損害賠償金,二者在目的、性質(zhì)上均有不同,在作用上也有所區(qū)別,因此可以相互補(bǔ)充,同時存在。但是賠償性的違約金在性質(zhì)上則與約定的損失賠償金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在作用上也幾乎沒有區(qū)別,實在沒有必要同時存在,作重復(fù)的規(guī)定,二者選擇其中一種適用即能解決問題,而我國法律對于違約金責(zé)任的規(guī)定有過于籠統(tǒng)之嫌,容易引起適用上的困難和理解上的差異。因此,要對這兩者作分別規(guī)定,以明晰相關(guān)法律關(guān)系,更有利地指導(dǎo)實踐。
二、明確違約金的參照標(biāo)準(zhǔn)
違約金既然是當(dāng)事人為違約行為而專門設(shè)定的一種制度,它的目的就在于預(yù)防違約行為的發(fā)生,使得當(dāng)事人自覺履約,以確保訂立合同的目的得以實現(xiàn),所以它不應(yīng)該以實際損失的發(fā)生為必要條件,那應(yīng)該是賠償損失或者解除合同等救濟(jì)方式來解決的問題,它的發(fā)生就應(yīng)當(dāng)以約定的違約行為出現(xiàn)為必要,一旦出現(xiàn)了合同中所規(guī)定的違約行為就應(yīng)當(dāng)適用違約金責(zé)任,而是否造成了實際損失則在所不論,這樣才與當(dāng)初設(shè)立該責(zé)任形式的初衷相吻合,也能更好地發(fā)揮各種違約責(zé)任形式的不同功能與作用。另外,對于懲罰性違約金而言,實際損失并不是其主要的調(diào)整標(biāo)準(zhǔn)。而《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也沒有對賠償性違約金和懲罰性違約金加以區(qū)別規(guī)定,籠統(tǒng)地說以違約造成的實際損失為標(biāo)準(zhǔn)明顯不合理。我們可以對其他立法關(guān)于違約金調(diào)整問題的一些規(guī)定加以靈活借鑒,如我國臺灣民法第252條規(guī)定的“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dāng)之?dāng)?shù)額”,而不再用“損失”一詞,從而可以將懲罰性違約金也納入到該法條的調(diào)整范圍中來,對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違約金進(jìn)行統(tǒng)一的規(guī)制。
三、對懲罰性違約金進(jìn)行合理規(guī)制
合理規(guī)制懲罰性違約金,首先,應(yīng)對懲罰性違約金作出一個最高限額的強(qiáng)制規(guī)定。在實踐中,允許當(dāng)事人任意約定懲罰性質(zhì)的違約金是否可行,是否要訂立一個標(biāo)準(zhǔn)或上限加以約束呢,對此,筆者持肯定的態(tài)度。因為自由總是相對的,在合同法上也是如此,雖然私法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法律一般不進(jìn)行干涉,但是過分的自由帶來的往往是負(fù)面的效果,如果對當(dāng)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數(shù)額不加以任何干涉,則約定過高的違約金很有可能面臨嚴(yán)重的道德風(fēng)險,既限制了債務(wù)人某些正常的民事權(quán)利,也可能引發(fā)債權(quán)人一方為追求高額的違約金而故意制造機(jī)會促成債務(wù)人違約,如此一來,則與法律規(guī)定違約金責(zé)任的本旨完全背道而馳。對于賠償性質(zhì)的違約金來說,由于其是對未來損害賠償額的預(yù)定,對其則有了一個相對明確的調(diào)整標(biāo)準(zhǔn),法院及仲裁部門可以依照實際損失的大小對它作出相應(yīng)調(diào)整,而對于單純懲罰性質(zhì)的違約金來說,因為它注重對違約方的制裁,與實際損失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所以對它就缺乏一個合理與否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所以,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對其規(guī)定一個合理的上限,允許當(dāng)事人在該規(guī)定內(nèi)充分自由地協(xié)商,自主決定違約金的數(shù)額,這將可以避免上述不利情況的出現(xiàn),有利于保護(hù)當(dāng)事人雙方的利益和合同的履行。具體可參照我國《擔(dān)保法》中關(guān)于定金適用的規(guī)定,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合同當(dāng)事人明確約定懲罰性違約金的,以不超過主合同標(biāo)的額的百分之二十為限。其次,明確規(guī)定對于懲罰性違約金的數(shù)額違約方不能申請有權(quán)機(jī)關(guān)進(jìn)行調(diào)整。因為懲罰性違約金的適用不以實際損害的發(fā)生為前提,不管損害是否發(fā)生,只要具備了相關(guān)責(zé)任構(gòu)成要件,違約方都應(yīng)當(dāng)向?qū)Ψ街Ц哆`約金。因而筆者認(rèn)為,法律或司法解釋應(yīng)明文規(guī)定:如果當(dāng)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是懲罰性違約金時,在違約行為發(fā)生后,無論違約是否造成了實際損害也不論造成損害的大小,違約方均應(yīng)按照約定支付違約金,違約方不能依《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jī)構(gòu)提出減少違約金數(shù)額的請求。
四、完善違約金調(diào)整的相關(guān)規(guī)定
針對《合同法》關(guān)于違約金調(diào)整規(guī)定存在的缺陷,完善違約金調(diào)整的法律規(guī)定,應(yīng)從以下方面著手:
首先,要明確調(diào)整違約金請求權(quán)的行使期限。鑒于前文所述,由于合同法中缺少對調(diào)整違約金請求權(quán)行使期限的規(guī)定,而引發(fā)一審、二審、再審過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矛盾,應(yīng)在我國立法中對該項權(quán)利的行使期限作出規(guī)定,以避免裁判結(jié)果無所適從的尷尬。筆者認(rèn)為,當(dāng)事人請求變更違約金數(shù)額的權(quán)利應(yīng)當(dāng)自簽訂合同之日起一年內(nèi)行使,以此來敦促合同當(dāng)事人在約定違約金條款時要謹(jǐn)慎行事,法定期限即一年后不得再提出變更違約金數(shù)額的請求,從而維護(hù)財產(chǎn)關(guān)系的穩(wěn)定性。
其次,對增加或者減少違約金的數(shù)額問題作出更加明確的規(guī)定。根據(jù)違約金的性質(zhì)不同,法律對于能否增加或減少違約金的數(shù)額應(yīng)作出不同的規(guī)定。對于單純懲罰性質(zhì)的違約金,因為其與實際造成的損失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所以不能因與實際損失的比較而加以增減,此種違約金的適用并不以實際損失的發(fā)生為必要條件,所以不論是否真的發(fā)生了實際損害,均不能被免除。由此種性質(zhì)所定,其能與其他的違約責(zé)任形式并用,但是與定金并用卻不行,因為他們二者具有相同的性質(zhì)。法院或者仲裁機(jī)構(gòu)可以決定對單純賠償性質(zhì)的違約金予以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賠償性質(zhì)的違約金一般不能與其他違約責(zé)任承擔(dān)形式同時適用,以免引起沖突與重復(fù)。
(作者單位: 國家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xié)作北京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