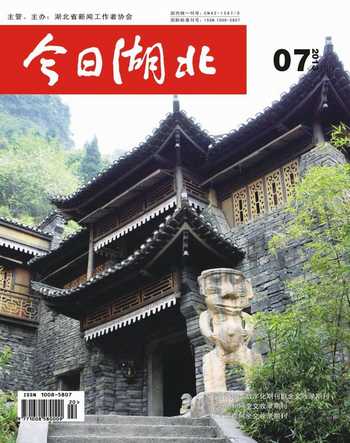中國民族音樂教育的主體建設與整合意識
楊亞麗
面對21世紀,該體系的建設是否可進入整合性的研究和實踐,以使體系的建設逐步呈現完整清晰的中華主體風格,使其與其他異文化共同體的教育體系有母語文化實質的區別?在長期的教學、研究中,根據觀察、參與和思考得出的經驗教訓,越來越感覺到,孤立地關注民族音樂教育的某一方面,對建設一個主體性完善的體系、提高民族的綜合素質的目的總有較大距離甚至偏離其目的。
在關于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建設中,目前有三個層面尤其要強化整合意識:
1、民族音樂教育模式與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基礎層面的整合;
2、民族音樂教育體系中“學校規范教育”與“民間自我傳承教育”——結構層面的整合;
3、民族音樂教育與中華母語文化以及與全球一體化——終極目標的整合。
強化這三個層面的整合意識,對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母語文化主體風格的建立可能產生根本性的推動。
一、民族音樂教育模式與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基礎層面的整合
民族音樂教育模式的形成,有賴于民族音樂教育系統理論的形成。沒有深厚、系統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成果,辦民族音樂教育需要的民族音樂教材、民族音樂課程和民族音樂學科三大系統的建立就沒有堅實的主體文化依托。反之,這三大系統如果不是建立在堅實的母語文化之上,其母語文化教育體系的建立只可能是相距遙遠的理想。要在根本上改變依托在異文化教育模式之上的中國音樂教育現狀,首先要高度重視中國民族音樂理論成果在各專業、各學科中向教材體系、課程體系和學科體系的轉化,從根本上改造目前音樂教育的“單語化”、“外語化”為主的傾向,走出中國音樂教育以母語文化為主體語言的第一步。
二、民族音樂教育體系中“學校規范教育”與“民間自我傳承教育”——結構層面的整合
這里的結構,不僅指政府辦的“學校教育”這單一系統結構。這里提出的教育結構是“學校規范教育”與“民間自我傳承教育”合二為一的雙系統整合結構,這種整合結構才是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完全結構。各民族不同形式的民俗活動、信仰活動的客觀存在是不爭的事實,而民俗活動全民性的號召力是不以任何意志為轉移的自我傳承方式的頑強存在。當然如果用西洋學校教育的教化手段標準來衡量這種傳承事實,可能得出另外的結論。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自己特定的生態環境中,遵循著自身的傳統和當下存在的需求,不斷進行著自我認同的發展和變化,并根據這樣的變化調整著該傳統文化的存在方式和傳承方式,無論使用當代高科技方式或是“古老”的口傳心授方式,原理一樣。
中國教育學要研究的課題,除學堂教育外,真是要切實關注各民族文化傳統如何在今天的復雜文化生態中、在課堂之外以何種傳承方式頑強地存活著。因為,這一存在是學校規范教育所需要的民族民間鄉土教材最根本的源泉,沒有對這一存在的有意識關注、支持和研究,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所依托的母語文化土壤就將大量浪費和流失;反之,不吸收、體現中華民族固有的、獨有的各種傳承方式,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區別于異文化教育體系的主體風格始終難以確立。因此,無論從那個角度,我們都不可再忽視民間自我傳承方式這一帶根本性的教育資源,以整合的眼光,將學校規范教育與民間自我傳承教育兩大系統均視為中國民族教育體系有機的基本結構去研究和建設,這是我們在跨世紀的音樂教育研究中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戰略性選擇之一。
三、民族音樂教育與母語文化以及與全球一體化———終極目標的整合
中國音樂文化如何在21世紀“全球一體化”的新型文明中堅持和強化其主體地位,是21世紀擺在所有中國音樂教育學者面前的重大問題,之所以重大,是因為她實質上面臨的是中國音樂主體文化在當代文明轉型中的價值重建問題。從中國音樂史教科書上記錄的自西樂東漸“學堂樂歌”以來的當代音樂史,與民族民間集成考察中發現的中華民族的當代史實還存在巨大差異這一事實來看,中國傳統價值取向的歷史局限應該引起音樂學者和教育者高度警醒。學科立足點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調整:(1)無論是對歐洲或非歐世界的經典文化和科學經驗,應一律予以同等尊重并兼收并蓄,廣泛吸納;(2)在高度尊重世界經典的前提下,根本目的是建設、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母語體系。因此,音樂歷史、音樂教育和母語文化的價值重建任務十分艱巨。
(作者單位:河南駐馬店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