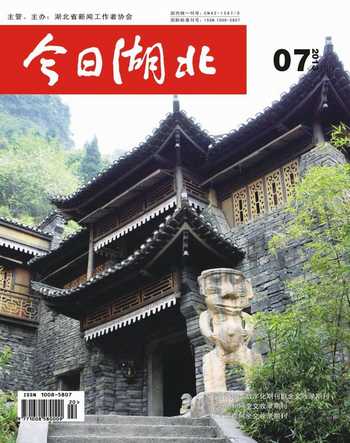微觀史特征淺析
陳兵
摘 要 《馬丁·蓋爾歸來》、《奶酪與蛆蟲》、《蒙塔尤》一起號稱微觀史學的“三大代表作”,在現代社會,微觀史學蓬勃發展,蔚為大觀,已經成為史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微觀史學最大的兩個特點就是文學性和史學性的結合,本文將以《馬丁·蓋爾歸來》中的貝特朗一角為例,進行分析,來印證這種特點。
關鍵詞 微觀史 文學敘事 史學敘事
《馬丁·蓋爾歸來》大約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大約1540年,年僅十四歲的馬丁·蓋爾和進入青春期的貝特朗·德羅爾斯成婚。可是,直達1548年他們才育有一子,不久馬丁離家出走。1556年,一個自稱馬丁的人來到貝特朗面前,她“摟著他的脖子親他”,開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因為財產繼承問題,新馬丁與他的叔叔皮埃爾·蓋爾發生爭執,皮埃爾由此懷疑新馬丁的身份,慫恿貝特朗把這個騙子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就在法院即將確認新馬丁是真實的丈夫的時候,一個裝著木腿的人出現在法院大樓前,他說他的名字叫馬丁·蓋爾。故事由此進入高潮。
這則事件最早的來源于一位法國圖盧茲法官科拉斯寫的《一次難忘的審判》中,在他的描述之中,他把貝特朗之所以會上當受騙歸結為“女性自身固有的弱點,很容易被男人的狡詐和心計所欺騙”。
而在《馬丁·蓋爾歸來》作者戴維斯的描述中,貝特朗幾乎從一開始就識破了阿諾的偽裝。但她卻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她可以借助他擺脫自己作為一個棄婦(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婦)的不穩定、不愉快的角色。相對于馬丁而言,阿諾更溫柔,更體貼,因而他“是她可以與之安度今生、相濡以沫的人……他也給了她愛的激情”。因此,貝特朗把阿諾需要知道的關于馬丁生平的所有細節都告訴了他,并且讓村里的其他人也相信這個人無疑就是她的丈夫。然而,當皮埃爾要控告阿諾時,貝特朗的地位重又變得岌岌可危了,因此她采取了一種很微妙的戰略。她假裝支持皮埃爾,和他一起起草了對阿諾的訴訟狀。這樣,如果皮埃爾贏了官司的話,他就不會報復她。同時,她又對皮埃爾的活動進行暗中破壞——當然這非常隱蔽,以致皮埃爾根本覺察不到——即在法庭上拒絕發誓說被告不是她丈夫。皮埃爾像科拉斯一樣,也將她的反復無常歸結為女人的弱點,但實際上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聰明的表演。
戴維斯這種打破傳統的寫法,顯然不是傳統史書寫作應該有的筆法。傳統史書不會大量描寫人物心態,也不會把人物的感情變化帶入書中。傳統寫作史書的方法講究實證,講究分析,追求盡可能高的客觀性。而在戴維斯的筆下,可以說貝特朗是一個完完全全活生生的女性,她就是她,獨一無二,與任何人都不同,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意志。可以說戴維斯并不是在記敘一個事實,而是在創造一個故事。這種完全偏向描寫的敘事手法,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歷史寫作的筆法,我們也就稱之為“文學上的貝特朗”。但是,如果微觀史只具有“文學上的貝特朗”的話,它自然不能被稱之為史學。而之所以稱之為史學,是因為它還有一個“史學上的貝特朗”。《馬丁·蓋爾歸來》通過講述一個離奇的故事,向我們傳達了許多當時社會的信息。就貝特朗而言,她之所以接受假馬丁·蓋爾作為自己的丈夫,有其作為女性的本性要求,欲望和依靠。但是,同時也有深層次的社會因素。當時新教教義正在法國廣為傳播,雖然阿爾蒂加的農民仍是天主教徒,但貝特朗可能已在內心接受了新教教義,認為“妻子在遭丈夫拋棄一年后就有了重婚的自由”。當然,在法庭上她不能明目張膽地這么說,她只能一口咬定阿諾就是馬丁·蓋爾。但私下里,她和阿諾可能都會根據新教的教義,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這就反映了當時歐洲正在流行的宗教改革對普通民眾的影響,相對于那些大部頭的宏觀史而言,微觀史來的更具體、更真實,而且由于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可能會得到與宏觀史不同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微觀史大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而且,就連極力批評微觀史的論者,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研究史學的方式為我們增添了數量可觀的歷史素材,豐富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這也是微觀史的最大可取之處了。正是基于微觀史這種既文學又史學特征,所以,它擁有不同于一般史學優勢。也正是由于這種優勢,我們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微觀史將會在史學領域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江政寬譯.馬丹·蓋赫返鄉記[M].聯經出版公司,2000.
[2]福柯著, 李猛譯.無名者的生活[J].國外社會學,第4 期.
[3]楊念群.新史學: 多學科對話的圖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修訂譯本)[M].三聯書店,2012.
[5]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劉永華譯.馬丁·蓋爾歸來[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10級人文科學試驗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