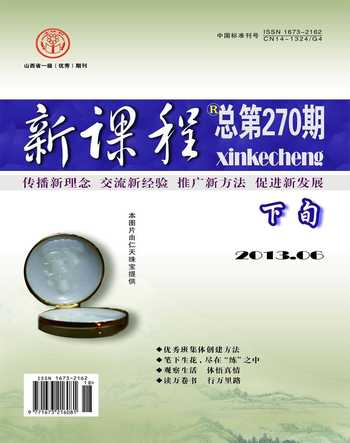保護,還是傷害
譚永利
摘 要:中國的女性主義,或者說性別研究,經歷了二、三十年的發展,對于提倡女性平等還是強調女性差異的問題上一直沒能達成共識。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在全世界女性主義理論體系中,彼此觀點相異,看法不一,甚至完全相左、南轅北轍的情況也比比皆是。但不得不承認,在經歷了西方如火如荼的女性主義運動和東方與階級斗爭相一致的婦女解放運動之后,男權社會的本質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從親身經歷的一件小事談起,從女性的角度發出的困惑和男性的角度存在的偏見兩部分解剖性別差異對女性的影響問題,并以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為啟示,提出一種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雙性同體從神話走向生活,成為解決男女矛盾的一種策略。
關鍵詞:性別差異;困惑;偏見;雙性同體
一、導論:從拒絕的理由談起
在中國,大多數女性很少加入各種純屬興趣愛好,與家庭、工作或個人發展無關的團體(牌局除外),女性由于家庭責任、生育小孩、工作職責而花費掉了本來就不如男性的大部分精力和體力,因此缺乏參與很多事件的原動力。我喜愛戶外旅游,在一次單位組織的戶外探險攝影活動中,我提前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把手頭的工作挪開,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把該做的準備做好,卻在臨行前一天的傍晚接到電話,由于這次活動只有我一個女性,不好安排住宿,請我放棄這次活動。活動的組織者是出于保護女性的初衷,拒絕的理由是性別差異,這樣的拒絕,對于女性來說,是一種保護?還是一種傷害?活動的組織者是為了免除潛在的危險,這當然是一種保護。同時,由于這樣的決定違背了我的意愿,它可以說,又是一種傷害。
二、女性性別的困惑
我引用這個小事件,并非出于情緒流露,而是為了引出問題。對于生理性別的差異,很少有人提出異議,因為即使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改變生理性別成為可能,但也只是外形的改變,并不能改變其功能性。這里的性別,當然指的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理論最為大家所熟知的表述,是西蒙·波娃所說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養成的。”這里的“后天”,包含了家庭、社會、教育、際遇等諸多因素。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有自己的性別意識,任何人的性別意識都離不開社會的賦予,但較之男性,女性從小受到的“約束”和“保護”更多,已根深蒂固地影響了對自身的性別意識。對于男性而言,整個家庭和社會對他的期望是大同小異的;而對于女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活圈子或階層,則有著很大的差異。這構成了女性對自己的性別角色產生困惑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近一兩百年來風云突變,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對于女性的社會期待,也經歷了非常大的改變。從先秦直至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時,對于女性的定位是處于家庭內部,“一個女性的性別意識更可能是父權社會的賦予,讓她順服和接受相夫教子的母親和妻子的角色”。辛亥革命以后,各種西方思潮對中國的女性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都產生了影響,“女性意識到男性在現實的社會體系和語言體系中對她們的壓迫,或歧視和排擠,對接受這種安排產生懷疑和幻滅的感覺,對規定的性別角色有拋棄和叛逆的念頭”。而到了毛澤東時代,他的性別理論是男女平等,表述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因此,產生了很多與傳統不同的硬朗的“鐵姑娘”形象。這時主要是淡化性別差異,強調其一致性。轉眼到了新世紀,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使女性的性別差異又重新變得鮮明起來,對于“美女”的欣賞也不再是難以啟齒的事情,女性對于外表和物質的追求變得越來越外露,而對于女性的培養,很多人贊成“男孩兒要窮養,女孩兒要富養”的觀點。
在短短一百多年時間里,社會對于女性的期待發生了如此多、如此大的變化,這對于女性自身的性別意識來講,自然是困惑大于明朗。
三、男性對性別的偏見
翻開歷史,我們雖然不可否認女性和男性一樣曾經生存過、活動過,但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卻沒能留下太多的足跡。女性并非沒有歷史,但“缺席”了,“沉默”了,失去“話語權”了。長期以來,女性被寫作著,被閱讀著,被批評著,被引導著,但在此語境下少有自己主動的參與。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蘇珊·格巴就把傳統文學中的女性寫作比喻成“空白之頁”。“此外的作者,如果她的生活沒有受過不幸的詛咒……她們不過是些效舌的鸚鵡,搖尾的叭狗,一方面把她們當作閑逸生活的消遣,一方面使愛好文藝的男性拜倒在石榴裙下,增加他們玩狎女性的情緒。”
在歷史上女性的境遇取決于父權制下男性對女性的偏見,日積月累,已然堅不可摧。戴爾·斯彭德(Dale Spender)命名的術語“守門人”(gate-keepers)和守門人理論(gatekeeping theory)也指出,在父權制的社會里,是男性決定了各個領域什么是重要的、有價值的,女性沒有話語權。
我們所說的男性對女性的偏見,在事實上一直存在,當然并不意味著每個女性都苦大仇深。中國的社會環境一直以來包容性很強,女性,和許多生活在底層的勞動人民一樣,可以被壓到很大的程度而不會反彈,所以,中國不太容易制造出憤世嫉俗的女性主義者,加之新中國“男女平等”的口號已深入人心,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也在表面上保障了女性一定的權利,再加之各人所處的社會層級和家庭環境不同,即使是受過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也不一定能對當前社會的性別問題有太多的認識,如,張抗抗說:“我從未經歷過性別歧視,所以,覺得男女平等是天經地義的。”即使發生離婚事件,“我仍然沒有受到一種根本的女性傷害。”所以,“女性在生活中受男性壓迫而產生的那種明確的性別反抗意識,我一直是很淡的。”
回到一開始提出來的問題,以性別為由拒絕我參加戶外旅游活動,這到底是一種保護,還是一種傷害?恐怕從男性的角度,有一大部分人都認為是前者,在女性中也有不少人作此想法。在中國,不僅是男性,也有不少女性并不認同和接受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她們對此有固化的感覺,就是持女性主義觀點的是“女強人”,她們會對此竊竊私語、嗤之以鼻,甚至認為這是女人中的異類,是對她們所過的正常生活的一種妨害。這樣的觀點,個人認為,即使是女性所持有的,但它屬于一種男性視野的或男性范疇的觀點。
當然,也不能忽視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于一些模糊問題的理解和尊重,遠不及為中國的女性解決受教育、就業、生育、家庭暴力等問題實際得多,這和西方注重討論女性的發展,多元生存境況,同性戀、異裝癖等傳統視野中的邊緣人問題不同,這取決于經濟基礎和話題慣性等。所以,要想轉變男性視野中的女性形象,仍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四、理想策略:雙性同體
雙性同體(androgyny)本來是用于表達生物意義上的雌雄同體或者雌雄同株,但是從柏拉圖開始,就具有一種精神和文化上的意義,它代表著性別的超越,而生物學上的雌雄同體反而更多地使用hermaphroditism一詞。作為男女兩性共存的一個理想模式,它最早在文學層面上應用者是英國女性主義文學先驅弗吉尼亞·伍爾芙。她在《一間自己的屋子》里說:“任何人若想寫作而想到自己的性別就無救了。……一個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一個女人若稍微看重什么不滿意的事,或是要求公平待遇,總之只要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在那里說話,那她就無救了。……在腦子里,男女之間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創作的藝術才能完成。”雙性同體并不是指要消除性別差異,達到一種“中性”,相反,它鼓勵差異,強調男性從思想上有女性的一面,女性從思想上也存在男性的一面。
在《美杜莎的笑聲》中,西蘇認為,“每個人在自身中找到兩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依據男女個人,其明顯與堅決的程度是多種多樣的,既不排除差別也不排除其中一性。”也就是說,“這種雙性并不消滅差別,而是鼓動差別,追求差別,并增大其數量。”雙性同體這一概念,在當代更加強調女性的氣質和愿望,把它提升到與男性平等的地位,性別的生理特點得以弱化,而精神層面的文化得以提升。
雙性同體的觀點,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因為在全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話中,都有雙性同體的原型或圖騰,同時具有女性的胸部和男性的生殖器的雕塑或器具在世界各地都有出土,而根據法國社會學派的杜爾克姆(Durkheim)的觀點,“不是自然,而是社會才是神話的原型。神話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會生活的投影。”因此無論是在遠古,還是在近年來女性主義理論界對“雙性同體”理論的再闡釋,都反映了人類社會中一脈相承的對男女之理想模式的關注。雙性同體的理論,可以讓男性和女性分別成為更完整的人,站得更高,能相互以對方的視角和感受來理解對方,這是可以實現的,有其現實依據。“宋朝女詩詞家李清照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的豪邁詩句,從女性狹窄題材中開拓出去,逼近了男性文學的世界。清周穎芳積28年心血寫就的彈詞《精忠傳》,脫離了女彈詞寫才子佳人的老套,為女性寫作歷史題材留下了僅有的例子。”而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唐朝詩人張籍的《節婦吟》,花間派詞人韋莊的《思帝鄉》,南唐后主李煜的《菩薩蠻》等等大量的詩詞作品,詩人都是以女性的視角和筆觸,來惟妙惟肖地刻畫了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和心理特點。因此,盡管不能有生理上的體驗,但男女之間視角的互換,感受的交融,是可以實現的。做到這一點,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平等和對話就會更進一步。
對性別差異的闡釋和歸納沒有盡頭,也無法達到一個完全一致的共識。再次回到文章一開頭提出的問題,以女性的生理原因為由對女性的優待和限制,是一種保護,還是傷害?周樂詩認為:“通達保護和補償婦女的權益來達到目的是有代價的,因為保護意味著性別差異中的等級差異。正因為女性是次一等的等級,才需要保護。”轉變男性對女性的固有認識,把女性看做是獨立的,可以對自我的選擇負責任的個體,動態地調整在社會發展歷程中對于女性的尊重和對女性權利的認識。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是一種傷害。
參考文獻:
[1]周樂詩.筆尖的舞蹈:女性文學和女性批評策略.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2][美]蘇珊·格巴.“空白之頁”與女性創造力問題//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3]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4]張抗抗,李小江.女性身份:研究與寫作//李小江,等.文學、藝術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5][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屋子.王還,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
[6][法]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7][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