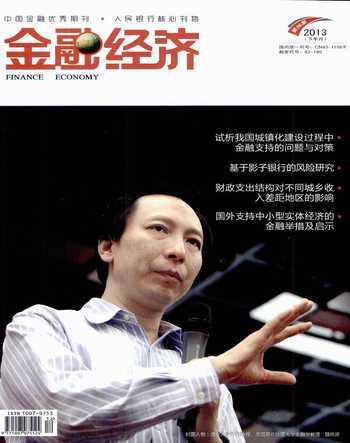危機后的金融監管協調:國際比較及經驗借鑒
蔣達 劉凡璠
摘要: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對當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反思,構建完善的監管協調機制已成為混業經營背景下維護金融穩定的必然趨勢。本文基于對危機后不同監管模式下各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對比分析,總結各國監管協調機制的改革經驗,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金融監管;協調監管;金融危機
一、引言
放眼國內,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和金融改革不斷深化,金融業綜合經營已初具規模,綜合經營與我國機構監管模式之間的矛盾勢必導致監管的真空和重復。在當下,采取徹底的改革實行統一監管所帶來的轉換成本是巨大的,且各監管模式本身并沒孰優孰劣的比較,采取哪一種監管模式,在一定程度取決于某國的偏好[1]。因此,在當前我國監管框架下,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是解決綜合經營趨勢與監管模式間的矛盾的現實選擇。
目前發達國家大都從三個層面上構建監管協調機制[2],第一層面是從法律層面,直接規定監管協調合作的內容或原則性要求,諸如美國、英國、德國;第二層面是制度層面,對法律所規定監管協調合作框架和內容等難以細化的事項明確化和制度化。如具體信息溝通機制、爭議解決機制等;第三層面是操作層面,即對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實際運作作出一系列安排。本文在這三個層次基礎上,分析危機后不同監管模式下典型國家監管協調機制的改革,通過這種橫向比較,試圖總結出危機后各國監管協調機制的發展趨勢。最后,結合我國具體實踐,剖析我國監管協調機制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危機后典型國家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改革分析
根據G30的報告,國際上現行的金融監管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四種模式[3],第一種模式是通過法定單位對機構進行監管,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采用這種模式。第二種模式是對個體機構的功能進行監管。很多國家都或多或少采用這種模式,1999年頒布的《金融服務現代法案》后,美國的監管模式就具有較鮮明的功能監管特點,德國金融監管局根據金融機構的業務和功能設立下屬機構,也是一種典型的功能性監管[4]。第三種模式是由超級監管者執行,像日本和英國就采取此種模式。第四種模式將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者區分開來,即“雙峰監管”模式,而前者主要依靠信息披露和市場行為,其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亞和荷蘭。無論采取哪種監管架構,不同監管領域之間的協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5]。
危機后,各國紛紛出臺了監管改革方案完善監管協調機制以適應金融危機后的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如美國在2010年7月正式出臺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英國的《2009年銀行法》、《金融服務法案》,德國政府于2008 年頒布了《金融市場穩定法》等。 本文選取美、英、德、澳四國作為不同監管模式的典型國家,分析危機后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發展動向,如下表所示。
資料來源:根據參考文獻[11]、[12]、[13]與[14]整理而成
通過深入的比較發現,這些改善措施在很多層面都體現著某些共性。具體表現在:首先,擴大央行的監管權限,高度重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美英德在危機后的監管改革方案中都將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責交付給央行,針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問題,美英兩國在各自的監管協調機制中分別建立了特殊清算機制和特別處理機制。澳大利亞則是由審慎監管局將被監管機構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實施不同的監管標準;其次,從立法上完善監管協調機制。危機后,四國分別頒布了相關法律,進一步明確各監管部門在監管協調機制的職責分工;再者,成立新的監管協調委員會并賦予其新的職能。危機后,美國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管協調,并承擔部分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英國則是建立新的金融穩定理事會(CFS),替代了原有的財政部、英格蘭銀行和金融服務局聯合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澳大利亞則是擴大了審慎監管局的監管范圍。最后,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保護消費者一直是監管機構的職能目標之一。危機后,各國在完善監管協調的政策規定中都將保護消費者權益放在突出位置,美國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將目前分散在美聯儲、證券交易委員會等的監管權集中起來,改善了之前多個機構共同承擔卻無人承擔的局面。德國的第二跨業部、澳大利亞的金融督查服務機構都承擔了與之類似的職責。
三、各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設計的共同經驗
(一)明確監管協調機制中央行牽頭人地位的法律依據。
金融監管機構的分工或職責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此次危機后,各國根據監管領域的實際變化對金融監管法律進行了修訂,明確了央行在監管協調機制中的牽頭人地位。2010年7月美國頒布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將美聯儲打造成對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超級監督者”,進一步擴大其監管權限,賦予其系統性風險監管職能。而在此之前,出于監管協調成本的考慮,美聯儲的監管職能在直接行動、間接行動和授權行動等方面都受到各功能監管者(functional regulator)或多或少的限制。類似的是,英國在《2009年銀行法》中進一步明確了英格蘭銀行在監管協調機制的定位與職責。
(二)暢通的信息共享是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的基礎
信息的收集與共享不僅能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而且能解決因信息不對稱引發的監管沖突。危機前澳大利亞聯邦儲備銀行委托監督局、證券投資委員會相互收集與其職能有關的信息,建立信息共享安排。而危機后,澳大利亞監管機構下定決心開放信息交流、加強協調溝通,澳洲金融監管委員會發布一份聯合諒解備忘錄(簡稱“MOU”),形成了充分的信息交流機制。美國由聯邦金融檢查委員會制定統一的報表格式的標準。英國在FSA和英格蘭銀行之間建立暢通的信息共享途徑,雙方可以完全、自由共享另一方收集的與其職責有關的信息。德國信息共享機制則明確規定央行是唯一負有對金融機構行使統計權力的機構,監管當局不再單獨向其征集任何形式的統計信息,必要的信息由央行提供。
(三)構建有效的事前協商和緊急、沖突協調機制
有效的協調機制應包括事前協商和緊急、沖突協調機制,確保監管各方在監管過程中一旦出現沖突或者漏洞,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如2008年英國抵押貸款機構諾森羅克銀行擠兌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就是英格蘭銀行和金融監管局缺乏必要的溝通。德國政府在2008年底創建的特殊金融市場穩定基金(Soffin),能夠在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面臨威脅時采取行動,而不是僅當銀行的存續面臨風險時才出手干預。美國則在危機后設立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解決不同監管成員之間的爭議。
(四)成立單一機構專司監管協調職能
成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協調職能是保持協調機制高效運轉的重要前提。針對危機所暴露出的監管協調不暢,各國進一步強化了監管協調機構的職權。以美國為例,《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要求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以強化監管機構間的協調合作,從而控制系統性風險。同時,為避免美聯儲權利過于膨脹,法案還賦予委員會監督、指導美聯儲進行監管的權利。
四、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存在的對策
對照危機后國外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設計的經驗,從我國監管協調機制的具體實踐來看,應從以下方面完善我國監管協調機制。
1.健全相關監管法律。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監管協調機制運行的基礎。我國只在《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規定了一些條款,并沒有專門法律明確監管協調內容或作原則性規定,對監管主體的約束力不夠。如果沒有立法層面的強制約束,目前建立的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和經常聯席機制的約束力就無從談起。實際上監管聯席會議至今只在2004年召開過兩次,雖在此期間確立了金融控股公司主監管人原則,但并沒有很好地發揮應有作用。
2.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實現信息完全共享是提高協調監管有效性的必然選擇。我國相關法律的缺失致使各監管主體在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機制中職責不明確,各監管部門利己心態導致各方對監管信息存在認識偏差。信息共享機制不健全直接導致監管數據重復收集,增大了被監管者的負擔與協調成本,導致我國監管協調效率均衡點難以達到[6](李成等,2009)。
3.建立監管協調部門。聯席會議機制和經常聯席機制本質是現有法律體系下的一種信息溝通交流機制,聯席會議機制無權解決監管部門之間發生的爭議和沖突。因而,急需專業監管協調部門開展監管協調機制中其他功能。對比發現,國外監管協調機制中都設有專門負責監管協調的部門,且危機后其職能有擴大的趨勢。如美國的監管穩定委員會和英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不僅承擔著監管協調的職責,還擔負防范系統性風險的部分職能。
參考文獻:
1]吳風云, 趙靜梅. 統一監管與多邊監管的悖論:金融監管組 織結構理論初探[J].金融研究,2002(9):80-87
[2]李文泓. 國際經驗: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合作機制[J].中國金融,2003(15):21-25
[3]G30.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Approaches and Challenges in a Global Marketplace[R]. Washington DC,2008:10-70
[4]馬德功, 臧敦剛. 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比較與借鑒——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與啟示[J].金融論壇,2010(9):83-87
[5]巴曙松. 金融監管機構是分是合:這并不關鍵——談當前監管框架下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J].西部論叢,2006(11):38-40
[6]李成,馬國校,李佳.基于進化博弈論對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解讀[J].金融研究,2009,(5): 186-193
[7]郭春松.中國銀行業監管協調與合作的成本收益與博弈分析[J].金融研究,2008,(7):145-153
[8]宋清華. 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國際經驗與中國的選擇[J].武漢金融,2007,(12):18-20
[9]孫濤. 實現信息共享是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的必然選擇[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6(3):39-41
[10]文洪武. 基于現行法律框架的中國金融監管協調合作研究[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11,(7): 1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