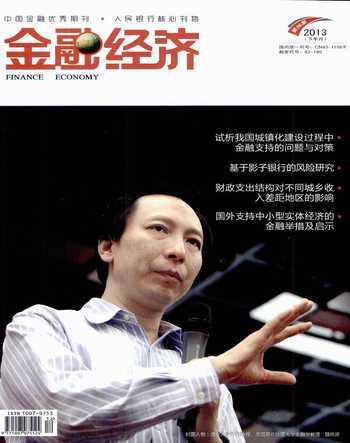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郭亞娟
摘要:隨著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越來越多。本文本文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基于VAR模型,通過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脈沖響應等分析,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金融發展分別以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明顯的影響經濟的增長。
關鍵字: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向量自回歸
1.引言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了快速穩定的勢頭,GDP從1978年的3624.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322億元。同期,我國金融從改革初期幾乎為零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斷提高,到2012年的金融總資產平均值(包括M2,股市值,債券余額)已達5643647.65億元,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倍還多。下圖是2001至2012年我國金融發展的概況。
原則上金融資產還包括保險及特別提款權,由于數據不易獲得本文沒有考慮。按照戈德史密斯的思想,金融相關比率在快速上升一段時間后應該趨于某一穩定值,但是我國的金融相關比率目前一直處于上升態勢,說明我國的金融還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金融的發展空間還很大。
國內外大量的理論推演與經驗數據都顯示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但不同環境下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不完全相同,作用方式也有所差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引導,而且目前經濟系統正處于轉型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關系和因果方向都很難直接進行定性分析,需要借助實際數據深層次分析兩者的關聯程度和變化趨勢,最終目的是為了找到金融能夠更有效服務于經濟的途徑,實現金融和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這無疑對促進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文獻綜述
相對于國外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和實證研究,國內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而且大都是運用既有理論對我國金融和經濟關系進行一些實證檢驗,很少有理論研究;此外,國內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對于經濟增長量的方面研究上,而對于金融對經濟增長質的研究少,且研究不夠全面。既便如此,很多學者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的實證研究,對了解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依然重大的借鑒意義,以下綜述這些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賓國強(1999)在其文章《實際利率、金融深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分別用回歸分析法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并且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在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談儒勇(1999)對我國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結果證實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之間有相關關系,但是股票市場與經濟的相關關系不十分顯著。他得出結論是:我國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所以金融中介至少應該與經濟增長同步;我國的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僅很有限,而且不利;我國金融中介體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韓延春(2001)基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他的結論是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有限。
李廣眾(2002)利用我國1952~1999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三變量VAR模型,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而金融中介效率指標不僅與經濟增長之間有雙向的因果關系,與國有、非國有工業的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規模可通過促進投資規模的增長促進經濟增長。
譚艷芝等(2003)利用中國1978~2001年的數據對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他們將引起經濟增長的因素分為量的因素包括儲蓄、投資、資本積累和質的因素包括資本邊際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檢驗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量的因素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對經濟增長的質的因素的影響作用要么顯著為負要么不顯著,金融發展對總的經濟增長率沒有顯著影響。
趙振全等(2004)利用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2年第四季度的指標數據,檢驗了我國信貸市場的發展和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分析的結果是:信貸市場通過信貸比重的增加的效應對經濟增長起作用,而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作用。文章指出出現這一實證結果的原因是國內較高的儲蓄率使得信貸市場的資金充足,能夠確保信貸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相對于信貸市場,股票市場的融資利用效率較低,資源的逆配置導致了我國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弱。
盧峰等(2004)利用中國28個省1991~2001年的數據檢驗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提出我國金融部門存在“漏損”效應,即金融資源從享有特權的國有部門流向受到信貸歧視的私人部門的過程,“漏損”效應有助于私人部門獲得稀缺的金融資源,進而有助于經濟增長。
陳剛等(2006)考慮了我國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聯結機制的影響。他們在標準的關于經濟增長的回歸方程中加入金融發展和資本形成的交叉乘積項、金融發展變量和1994年虛擬變量的交叉乘積項,分別對1979~2003年、1979~1993年和1994~2003年三個時間段的相關數據進行回顧估計。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我國金融發展主要通過發揮動員儲蓄、加速資本積累等功能來促進經濟增長。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惡化了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關系,主要原因是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加強了對銀行信貸流向的干預,導致了金融功能的財政化,降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劉潔(2008)本文對1980—2007年農村經濟和金融發展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我國總體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發展規模與農村GDP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農村經濟增長是總體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是農村經濟的格蘭杰原因,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與農村GDP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阮敏(2010)文章運用生產函數加入金融脫媒變量構造的模型,通過1991到2008年的數據協整、回歸分析和因果檢驗,發現經濟增長與企業股票和債券融資的比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不過經濟增長是促進企業股票和債券融資的比重變化的原因,反之則不是;由中國的數據說明經濟發展是金融深化的動力。
馬穎(2011)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過程置于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之下,探討經濟體制改革何以使分權化體制下的金融資源得以釋放的同時,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形成了市場導向的金融體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驗證了經濟體制改革、金融發展與長期增長之間的正向關系。
綜上所述,大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國的金融系統中金融中介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而金融市場如股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較小。但是不同的文獻因指標的選取、數據區間的選取以及中國不同地區的選取而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
3.研究方法和模型
3.1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
向量自回歸(VAR)是基于數據的統計特性建立模型,它把系統中的每一個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常用于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自1980年希姆斯將VAR模型引入到經濟學中后,它在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分析中得到廣泛應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又分為簡單向量自回歸模型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本文采用簡單向量自回歸模型,也只介紹這一種。
一個n維隨機向量Yt服從P階向量自回歸過程的模型記為VAR(P),數學表達式是:
其中,Yt是n維內生變量,Xt是k維外生變量的向量,A和B是要估計的系數,ut是隨機影響變量,ut不能自項相關,也能不與其他的內生變量有相關性。
3.2協整檢驗
(1)協整的定義
如果兩個趨勢大致相同的時間序列線性回歸的擬合結果很好,但實際上兩者之間沒有經濟聯系,擬合結果的殘差沒有滿足平穩性的要求,那么這兩個變量就出現了“偽回歸”。1987年恩格爾和格蘭杰提出了協整理論,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平穩的序列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它們之間就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不再是“偽回歸”。協整的定義如下:
對于n維向量Yt滿足如果滿足:
(1)Yt~I(d),要求Yt的每個分量Yit~I(d);
(2)協整檢驗方法和過程
目前協整檢驗主要有兩種方法:EG兩步法和JJ(Johansen-Juselius)檢驗法,下面主要介紹JJ檢驗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
JJ檢驗是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與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種以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為基礎的、基于回歸系數的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的方法。
首先建立一個p階的VAR模型
4.實證分析
4.1 變量的選擇、定義和計算
1.經濟增長指標
本文主要是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以選擇了人均實際GDP來衡量我國經濟增長,意在排除人口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時剔除物價變動因素以更加真實地反映我國實際的經濟增長。
人均gdp用PGDP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PGDP=GDP/總人口
本文在實際分析中采用的是PGDP的自然對數值,表示為LNPGDP。
2.金融發展指標
(1)金融發展規模指標
衡量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有金融相關比率和金融深化指標。
金融相關比率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由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它是指某一時點一國金融產品的市場總值與實物形式的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常以GDP來表示)的比。一國的金融資產存量一般是M2與證券(包括債券、股票、保險等)的和,而一國的實物資產總量常用該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近似表示。
鑒于金融相關比率很強的綜合性,本文采用金融相關比率作為金融發展規模的衡量指標。此外,本文還選擇了廣義貨幣指標與GDP的比,用來反映金融中介的規模,金融相關比率用FIR表示,金融中介規模用BANK表示,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FIR=(M2+股市市值平均值+債券余額平均值)/名義GDP
BANK=M2/名義GDP
因為公式中股票市值和債券余額是存量指標,而M2和GDP是流量指標,為了可比性,本文對股市市值和債券余額取的都是計算期的簡單平均數。
(2)金融發展結構指標
金融結構指標反映了金融市場在全社會資本資源配置中相對地位,等于債券和股票這兩類非貨幣金融資產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重,用STR表示。
STR=(股市市值平均值+債券余額平均值)/金融資產
其中金融資產= M2+股市市值平均值+債券余額平均值
(3)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金融發展效率是指以最可能低的成本盡可能最優地配置有限的金融資源以實現其盡可能有效的利用,由于目前還沒有哪個指標能夠代表整個金融系統的發展效率,本文選擇金融中介效率計算。
用儲蓄與貸款之比SLR表示,應該說儲蓄貸款比率SLR描述的是金融中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計算公式如下:
SLR=存款/貸款
4.2 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2001年~2012年的季度數據,共48組數據,來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4.2.1 經濟增長與金融各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
上表顯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總體規模指標金融相關比率FIR、金融中介規模BANK、金融發展結構指標STR、金融發展效率指標都具有顯著的正的相關關系,但是相關性的強弱不同,其中FIR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大,BACK和STR相關系數均小于0.8,是中度相關。SLR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最小。
4.2.2 平穩性檢驗
平穩性檢驗,使用ADF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4-2:
檢驗結果顯示,序列LNPGDP、FIR、BANK、SZH、STR、SLR都含有單位根,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ΔLNPGDP、ΔFIR、ΔBANK、ΔSZH、ΔSTR、ΔSLR都拒絕了原假設,均為平穩序列。可見他們都是一階單整序列,為I(1)過程,可以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
其中c,t,k分別表示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后階數,臨界值默認是在5%顯著水平下得到的。
4.2.3 Johansen協整檢驗
約翰森協整檢驗與EG協整檢驗的比較:(1)約翰森協整檢驗不必劃分內生、外生變量,而基于單一方程的EG協整檢驗則須進行內生、外生變量的劃分;(2)約翰森協整檢驗可給出全部協整關系,而EG則不能;(3)約翰森協整檢驗的功效更穩定。故約翰森協整檢驗優于EG檢驗。當變量個數多于2時,最好用Jonhamson協整檢驗方法。
由表3可知,狹義貨幣需求LNPGDP與其他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并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3個協整向量,說明變量LNPGDP、FIR、BANK、STR、SLR之間具有共同的隨機趨勢,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標準化的協整系數見表4。
將第一個協整關系寫成協整方程可以表示為:
應用AR根的圖表驗證協整關系的正確性,如圖2,圖顯示所有單位根的倒數的模均落在了單位圓之內,因此,協整關系是穩定的。
4.2.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本文先對金融發展相關變量與經濟增長建立VAR模型,以便后續的檢驗和分析。首先檢驗LNPGDP與FIR、BANK、STR、SLR之間是否有格蘭杰因果關系。(置信水平0.1)
鑒于本文是季度數據,我們可以把滯后4階以內看作是短期,滯后8階看做是中期,滯后10看做是長期。對表5的解讀如下:
由表4-7可以看出,變量FIR對短期和中期是LNPGDP的格蘭杰因果原因,說明金融相關比FIR在短中期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BANK是LNGDP的短期格蘭杰因果關系,說明金融中介規模BANK只在短期影響經濟增長。STR無論是短期、中期和長期都是LNP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金融結構STR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久的。STR只在長期是LNP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金融效率只在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4.2.5 脈沖響應分析
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分析可知,變量之間有些關系在長期后才能顯現,所以本小節脈沖響應的滯后期選擇滯后15期,以期能看的更遠、更全面。基于VAR(2)得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如圖3。
由圖3可知,響應的方向都是正負交替的,說明金融發展各變量對LNGDP的作用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方向,有正向的,有負向的。LNGDP對FIR、BANK和STR的脈沖在有明顯的響應,而且響應的方向正負交替,對SLR的響應一直都是正向的。說明對經濟增長來說,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均對經濟增長有明顯影響。
5. 結論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兩者由長期均衡的關系,金融系統與經濟增長有均衡關系,即便短期有所偏離,兩者組成的系統也能夠自行調整到均衡狀態。
從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看出,金融發展各變量均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金融相關比例對經濟增長是中短期影響,金融中介規模指標在短期影響經濟增長,可見金融規模短期或中期影響經濟增長;金融結構長久的影響經濟增長,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金融效率只在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從脈沖響應來看,當本期給金融相關比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后,LNPGDP在短期內反應均為正向的,后來由正轉為負向反應,過段時間由最終轉為正向,說明短期內,金融相關比的提高,會促進經濟的增長。而LNPGDP在短期內對金融中介規模是反映方向反映,而后轉為正向。LNPGDP對金融結構的反映方向有正有負,在長期雖然是負向的,但是從第九期開始達到谷底,轉為上升,延長滯后期可以得出,LNPGDP對金融結構的反映又變為正向的。LNPGDP對金融效率的反映一直都有波動,但都是正向的波動。
參考文獻:
[1]賓國強.實際利率、金融深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J]. 經濟科學,1999,03
[2]李廣眾.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多變量VAR系統研究[J].管理世界,2002,03
[3]譚艷芝.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3,10
[4]趙振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J]. 2004,08
[5]盧峰.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J]. 2004,01
[6]陳剛.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區域差異分析——兼論分稅制改革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J].金融論壇,2006,07
[7]劉潔.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基于1980—2007年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8,S1
[8]阮敏. 金融體制、金融脫媒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研究[J]. 金融縱橫,2010,08
[9]馬穎.中國分權化改革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J].發展經濟學研究,2011,00
[10]黃晶. 地區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基于江蘇省的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教學,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