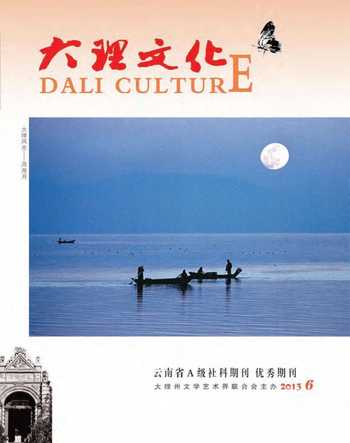母土博南(組詩)
趙振王
木蓮花
蓮花,被撐天的樹
托出一種高度
寶臺山。每朵蓮花上
都坐著一個佛
蓮瓣。像暖暖的冬陽
照著進出不輟的人
我在佛之下緩緩穿行
佛看著我。我卻看不見佛
每逢閏年。異常的十三個蓮瓣
驗證了植物的靈性
蓮花開過。就要凋零
佛卻永恒地活著
雖然,我看不見佛
佛卻活在我心里
山風。在金光寺的屋檐
推著風鈴。虔誠念佛
故事在鈴聲里開始
也在風中結束
百丈冷門庭橫開豎劈
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
佛看得見一切
一樹樹蓮花綻放
為佛提供一個個打坐的靈臺
我的淚水,是佛的汗珠
沿著故事的流向
講述人間喜怒哀樂
太多彎路。紛囂的凡塵
在寶臺山。卻遇到了
屬于自己的那尊佛
繞行在洗身池畔
僅僅用了瞬間的功夫
佛就舉過手臂
為兩手空空的我放行
只要呼吸著。我必行走
絕不放棄……
古道
古道,是漢代
扔過來的一顆石子
留在滇西大地的拋弧線
血汗的顏色和質地
構成弧線的基本元素
這顆石子,飄落在
我的目光前。上千年的馬幫
就在視線里來來往往
浩浩蕩蕩,大聲大氣地說笑
蓋世的勇氣。就把粗糙的石板
打磨成一面面銅鏡
悠然的馬尾。搖來擺去
那是馬鍋頭爺爺,爺爺的爺爺
微笑的一種樣式
留給子孫的不動產
在世襲的精神脈道里
均勻地傳接
汗水,灰漿狀地落入石縫
粘結著石板與石板
至今,絲毫不松動和脫落
石頭緊抱著石頭
言說古道的堅韌與不朽
我的詩歌,屬于馬尾巴上
跟隨著的一只蒼蠅
或者蚊子。之于祖先
與古道無與媲美
僅此一滴汗,一支小曲
一滴鮮血。或是
熟睡中,震天的鼾聲
花橋
花橋。在人們的遺忘中
被一面斑駁而立的墻
把高齡的博南縣
用緩慢泛香的稻花
留在古驛站,蒼老的瓦當上
指點比自己年輕的元梅
博南的縣址,活成千歲老翁
以遺址的方式
在南方絲綢之路
打更報曉,讓馬鈴聲
具有秩序感
古道。雖然殘破不堪了
縱向地端詳和品味
卻安然無恙
花橋,把史書中
關于博南的那些章節
記錄在竹簡以外的冊子里
寫得像詩。更像長長的馬隊
頭騾的頭頂上
那個艷麗可以辟邪的花籠
在千年古道上
不甘示弱
馬鍋頭。和他們的馬幫
不知疲倦地行走
來來回回走著的路
留下的遺跡,成了耐讀的風景
漢代到民國
熱氣騰騰的古驛站
在花橋。顯著人脈力量
古道。斷裂過
斑駁得像一塊塊傷疤
辨認不清哪是刀傷
哪是槍傷,哪是被虎狼撕咬過
已經無法復位的齒痕
古道,有太多的傷痛
讓子孫們痛哭流涕
哭聲。成為懷念的音符
在花橋回放,任何的模仿
都是蹩腳的作秀行為
萬馬歸槽。才是原唱的歌星
元梅樹下,傾聽陽光
經久不息地吟誦聲
飛躍而來的梅影
標出六百年壽辰的亮度
我在元梅脈脈含情的雙眼里
讀懂了博南縣
千年常勝的驕人業績
杉陽
杉陽,被千年馬蹄子
緊緊擁抱著,透不過氣
柔言細語。讓人臉紅心跳
不知所措之中
閉上雙眼,猜想愛的過程
側耳,聆聽古鎮的氣息
瀾滄江的濤聲
成為杉陽的呼吸
博南山。擋不住這種氣勢
勢如破竹地前行
可以斷言,馬尾巴上的蒼蠅
是馬鍋頭留下的伏筆
高速發展的運輸業
讓馬們散失了
長途馱運的功能
它們依然活著,三三兩兩
盡情地吃瘋長的青草
古鎮的石板
透亮得可以做鏡子
遙遠的馬蹄聲,響在鏡面上
羞羞答答地微笑著
多像馬鍋頭爺爺的夫人
我奶奶低頭掩面時的樣子
鏡面里,領舞的人
哼著彝族風味的小調
調子的所有元素
被馬糞、馬尿浸泡過
保留下來,古樸而抒情
杉陽。站在馬蹄聲前
無言以對。高速公路上
我扔筆潛行,張口結舌
悄悄到達某地,有話想說
可我是晚輩。晚的不是朝夕
晚了好多個年代
銀江河
曾經的銀龍江
流淌在徐霞客游記里
流域。超不過一百公里
冒了幾百年的熱氣
依依不舍,注入瀾滄江
何年、何月,被易名銀江河
查不到。不知是誰的主意
很笨。把“龍”削去
這理由,強詞奪理
何時的縣人大的某次會議
能夠為一條龍
恢復名義
從江到河,氣勢減弱
流水卻不枯。我從小的水性
就靠銀江河漂洗、打磨
忽隱忽現中。就成一條魚
在河里,不知深淺地游
順流或逆流。直線或拐彎
難不住一條或一群魚
水勢。漸次強大
截流了的瀾滄江
伸出巨大手掌
堵住銀龍江的嘴
不讓爽朗地說話。開心地唱歌
銀龍江。款款流著
流在徐霞客曠世的游記里
不改奔涌的性格
文字間,從小溪到小河
再到江的樣式
一直在漢字的凝固狀態里
奔騰了四百多年
曲硐
曲。是形式
硐。是真實存在
曲硐,是一個民族
實際的存在
靈魂的存在
小獅山頂。透亮地寫著
有關曲硐的來歷
拜塔腳下。暗藏玄機
神秘的洞穴,猶如臍帶
連著博南與永平
曲硐,溫泉氤氳
一個民族蒸蒸日上
在幾度成為縣城的邊地
不用查籍閱典
徐霞客游記里的曲硐
水霧般彌漫
曲硐。用質地極好的絲綢
纏繞住古道,讓博南這個段落
用馬鈴聲,溫暖史冊里
所有死去活來的文字
汽車喇叭,激活千年驛站
等待火車汽笛
進入永平,抬高由來已久的音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