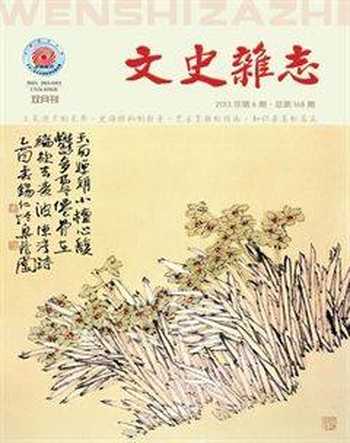感佩于大禹的科學行動和言論
馮廣宏
自從上世紀疑古浪潮興起,大禹就在人與神之間徘徊;影響所及,至今文化界仍然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如果大禹是在天上布土阻洪的大仙,或者能像夸蛾氏之子那樣背起大山,放到合適位置上去,那么今天就不必研究什么大禹文化了。所以,恢復大禹的人格,承認他是有血有肉的偉人,乃是一樁急務。由于他功高萬世,才被民眾奉之為神。這種由人到神的變化是正向的,并不是由神轉化成人那種逆向。
自從殷墟出土甲骨卜辭,歷史上殷商這個朝代才被嚴謹的史家所認同,同時也肯定了《史記》所記殷商世系的確實性。由于《史記》同樣記錄了夏后氏世系,雖然夏墟還沒有文字性器物出土,但根據邏輯推理,也應該同樣肯定。夏后氏世系頭一代是啟,他該是人而不是神,神怎么會創建王朝呢?既然是人,總有父親和祖父,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史記》依《世本》之說,記述啟的父親是禹,祖父是鯀。《國語》上魯國著名學者展禽指出:“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禮記·祭法》同樣說:“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與《世本》之說一致。既然如此,作為啟的父親,禹就不能不是個肉身的凡人了。
科學的行動
凡人身份的大禹,在中華歷史上最大功勛是平治水土,所有古文獻上一條聲。但這件事是不是神話?需要考察一下它的科學合理性。如果現存的《尚書·虞夏書》里,完全沒有治水內容,那么這件事便可能屬于虛構;反之,要是記有那些內容,而且科學合理,就沒有理由懷疑那是神話。神話與史跡畢竟不是一個氣味。
《虞夏書》里三段,構成治水前期三部曲。
《禹貢》載“禹敷土,隨山刊木” 。第一步,用土填高積水的道路,沿著高地砍伐密林(同時建立標志),恢復交通。
《皋陶謨》載禹說“予乘四載” 。第二步,解決交通工具。
《禹貢》“奠高山大川”。《 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 第三步,測量地形,為山川命名。
這些前期步驟,為古今治水工作所必需,應該是實踐經驗的記錄,既科學,又合理。
《周髀算經》載有遠古數學家商高的話:“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認為中國的數學創自大禹,因為治水才需要這門科學。書中介紹了“用矩之道”,矩是一種簡單而又實用的測量工具:“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大禹所用的矩,現代航海員手上的“六分儀”就根據它的原理制造。《山海經·海外東經》有一段話,說禹命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這位名“亥”的青年測量員右手拿著計算器,左手伸指測平,求得平距。這些說法符合測量技術要求。
漢代《論衡·談天》指出:“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現在《山海經》仍存,但今人往往不承認它是禹益所記,說它是戰國時人的編造。在這里想請教他們一下:時間與禹相隔兩千年的司馬遷,寫《史記》時強調,《山海經》里“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如果那是相隔幾百年的戰國產品,怎會有這樣大的文化理念差距?再者,《山海經》里的地名,晉代地理學家郭璞注解時三分之二弄不清楚,交了白卷。相反《春秋》和諸子書中地名,弄不清的僅不到十分之一。如果《山海經》出自戰國,怎會有這種怪現象?今人所知有限,不應輕率地否定古人的說法。
大禹著手治理長江、黃河這樣的萬里巨流,除了必要的科技準備以外,還有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全局觀念,不能上下游各行其是,左右岸以鄰為壑。為此,必須統一號令,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否則治理不了水土。堯舜時期,《尚書·堯典》講得很清楚,政治上是部落聯盟議事制,普天下氏族部落林立,各方雖有為首的岳長,但邦國之間爭強斗勝,誰也不服誰。因此,大禹治水開始,一定要樹立崇高威信,優先利用當時的原始信仰,采取“天”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即《墨子·非攻下》所謂“禹親把天之瑞令”;然后召開大會,進行動員,遲到者殺。《國語·魯語》上孔子敘述“昔禹致群神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 。《韓非子·飾邪》認為這是“古者先貴如令”。當時肯定會出現許多反對派,大禹則以武力為后盾,加以制服。《墨子·兼愛下》記有古代文告《禹誓》,就是征伐三苗的出兵宣言:“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予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荀子·成相》有禹“辟除民害逐共工”的話,而且《山海經·大荒西經》上也有“禹攻共工國山”。《呂氏春秋·召類》:“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說明那時征伐行動實在不少。
大禹治水有八年、十年、十三年諸說,最后達到《禹貢》所述“九州攸同”,號令完全統一。所劃分的“九州”,全部以自然地理特征為標志,在四千年前真了不起!比如四川所在是“華陽黑水惟梁州”,完全不依部落邦國的行政界線。今人往往說那是戰國時期學者的閉門造車,確實太主觀了。九州之說影響所及,貫穿了整個二十四史地理志、五行志,誰有那么大的能量閉門造出如此威力巨大的太空車?由此只能表明,治水帶來了政權的大一統,才有這樣燦爛的結果。《左傳·宣公三年》言及各地把地理資料送到中央,同時進貢一些金屬;大禹則利用金屬鑄成九鼎,把地理材料刻在上面,供民眾使用。如果全國不統一,缺乏一方的材料,九鼎上面的刻記就無從完整。
一切的一切,都證實了大禹治水事跡的科學合理性,而且大部分并非漢代以后的傳抄,多半是先秦文獻記載。
科學的救災
中國人有歷史學的基因,從上古起就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傳統。大禹當時說的話,幸而《尚書》里有具體記錄;盡管文字特別古奧費解,而且字句過分簡單,但畢竟是這位偉人留下的聲音。
《皋陶謨》是舜、禹、皋陶等一次談話(或許是開會)的全記錄,甚至連“嗯”、“啊”這些語氣詞都錄了下來,使四千年后的我們,有幸體驗到當時他們臉上的表情。司馬遷寫《史記·夏本紀》時,則用西漢時文言體照搬照抄。
《皋陶謨》開頭一大段,由皋陶發表一通政治見解。說完之后,作為主持人的舜帝說:“來,禹,汝亦昌言”——坐過來,禹!你也暢所欲言吧。
禹拜了一拜,說:“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是啦,陛下!我能說些什么?我思想上每天都很緊張。
這時,皋陶插話:“吁,如何?”——哎,這話怎講?
禹開始匯報情況:“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洪水滔天,浩浩蕩蕩地包圍了高山,沖沒了丘陵,住在低處的居民不幸沉陷到水里。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我在干地、水地、山地、泥地用四種不同的運輸工具,沿著山脊砍出的林間小路,和益一起,現殺些鳥獸肉,送給那些救出的災民,讓他們活命。
“予決九河,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我們疏通了九條大河,先把洪水排泄到四海;再一條條地疏通小河和溝渠,把積水排泄到大河里去。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接著又和稷一起,動員大家播種糧食。等到收成時,再分給民眾那些種出的糧食和鳥獸肉,并且讓產量不同的地方互通有無,讓大家儲存些貨物。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普通老百姓都有了飯吃,萬方的部落邦國都安定了下來。
皋陶聽完,深受感動地說:“俞,師汝昌言!”——哦,這些話你講得太好啦!
大禹的匯報極有層次性,完全勾畫出整個救災和治水行動過程和結果。《周易·系辭》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簡簡單單的一席話,講得清清楚楚。
第一段講災情。洪水的嚴重性,在幾句話中歷歷如繪。
第二段講搶救。首先是準備運輸車輛,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工具;其次是砍樹開路,而且沿途打獵,積累食物;同時又救出被水圍困的民眾;最后是給災民送食,維持生命,要點十分突出。今天的救災步驟也不過如此。
第三段講治水。從疏通大河做起,讓蓄積的澇水由大河暢流入海,解決最主要的洪患。然后才治理小河和溪流,把積水通過大河排出去。步驟不能相反。如果大河不通,小河和溪流的積水就無法排盡。今天我們采用的排洪步驟,仍然照這樣辦。
第四段講災后重建。首先恢復農業生產,再以漁獵作為輔助,然后統一收獲,合理分配,調劑余缺,動員民眾進行貿易、交易,積累財富。這種積極的救災方式,今天仍然有借鑒價值。
第五段講穩定民生。民以食為天,解決了糧食問題,分散的邦國都不難穩定。
如此科學合理的言論,封建時代的腐儒絕對是編造不出來的。大禹不但有血有肉,而且有智有慧。
質樸的言論
《皋陶謨》接下去,是大禹對舜帝的建議:“都,帝!慎乃在位”——是啦,陛下!謹慎地坐在大位上吧。
舜虛心地答應:“俞”——噢。
禹接著說:“安汝止,惟幾惟康”——堅守你的職位,隨時想到會發生危機,想到如何才能安定。
“其弼直,惟動丕應”——輔助你有許多正直的人,你想辦什么事,他們會大力響應。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全心全意地接受上天的旨意吧,上天會不斷賜給你美好的機遇。
大禹這番話,反映出他質樸的性格;同時也反映出當時政治體制上的民主特征。從第一段話得知,舜雖然被推舉為天下共主,但他的職位隨時可以被取代,所以大禹請他居安思危。從第二段話得知,舜的周圍是些既有品德又有才干的人,辦事沒有什么阻力。從第三段話得知,大禹雖有科學頭腦,但卻篤信上天,具有巫文化原始信仰,這似乎與他出身于西羌有關。他希望出自東夷的舜,也產生和他一樣的質樸信仰。可是舜只對他那第二段話感興趣,很激動地說:“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哎,大臣喲就是親鄰喲,親鄰喲就是大臣喲!
大禹也滿意地答:“俞”——是啰。
舜帝接著說了一大堆話。禹很贊成:“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對呀,陛下!光天化日之下,直到天涯海角的民眾,萬邦的黎民百姓,一概是你的臣民。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請陛下選拔任用他們;普遍聽取他們意見;再考察他們的工作成效,用車服來獎勵優秀者;這樣一來,誰敢不謙虛、誰敢不恭恭敬敬地響應你的召喚?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如果陛下不這樣辦,卻帶有好壞混同、良莠不分的作風,就是天天選拔人才,也沒有什么好結果。
大禹這番真心話,講得十分耿直,顯示出當時的民主作風。舜帝聽了這種逆耳之言,接著作了一大段解釋,說明他比堯帝的兒子丹朱更儉樸,而且對于堯家敗在丹朱手上感到痛心。這時,大禹就不能不把他自己更加艱苦的作風,補敘一段,告誡舜帝不能吃老本:“娶于涂山,辛、壬、癸、甲”——我和涂山氏結婚,在家只呆了四天。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生下啟兒呱呱地哭,我沒拿他當兒子(沒有盡父親責任),只在野外計劃怎樣完成土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劃分出五道管理帶,直到五千里外;中心區每州建立十二個行政單位;向外一直延伸到靠近海邊,都設立了五級長官,各自領導各類任務。
“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只有三苗老是頑抗,不肯接受任務,陛下要多考慮這事啊。
《皋陶謨》上述大禹親口說的話,正如已故四川大學教授任乃強所評價的那樣:“他那些話,現在鄉村里基層干部也能說得出來,沒有多少高深理論。”對比一下皋陶講的“寬而栗,柔而立”等等辯證言論,顯得比較土俗,可是每句話都比較實在,毫無華麗辭藻,每句話都閃耀著奮斗精神、救民責任。
踏實的思路
《皋陶謨》前段,在皋陶“知人安民”的發言中間,大禹有一段插話:“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哎,都像你講的那樣,即使是堯帝恐怕也難做好。
“知人則哲,能官人”——知人,就達到“哲”的程度了,就能任用所有賢才了。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民,就達到“惠”的程度了,黎民百姓就全都懷念他了。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又是哲,又是惠,如果真正達到這種地步,還害怕什么驩兜?還搬遷什么三苗?還戒備什么花言巧語、吹牛拍馬的奸人?
大禹的意思明擺著,不贊成提漂亮口號,而主張實事求是。在他的治水行動中,依靠的都是益、稷、契這些實干家,而不是什么理論家。
古文《尚書》里有《大禹謨》一篇,也記有大禹的一些言論。盡管清代樸學家曾經條理化地考證過古文《尚書》存在許多偽造,但那些大禹言論皆見于其他古文獻,所以并不妨礙考察研究。比如大禹說過:“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這些話的意思是,君主和臣民都抱著艱苦奮斗的作風,政治上就和諧了。順民意就吉,逆民意就兇,報應來得很快。民生問題,在政治上最關重要,“利用厚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如此等等,反映出他的一貫思想。
《禹貢》末尾,交代了大禹平治水土成績后,以檔案方式確定各地的貢賦標準,給中心區的“中邦”劃分土地,確定姓氏;然后記錄下大禹說的兩句話:“祗臺德先,不距朕行”。意思是請大家尊重以德為先的原則,切勿離開確定的制度或做法。
在治水過程中,大禹曾經鎮壓過敢于抗拒命令的頭人,懲罰過大批懶惰或辦事不力的官吏,可是人們并沒有怨恨他,原因在于他處處以身作則,工作起來比任何人還勞累、還艱苦。《莊子·天下》引墨子的描述:大禹“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漢代武梁祠石刻的大禹像,頭戴斗笠,身穿短衣,手持土鍤,完全不像什么領導人,而很像一位老農。他的真正形象,的確應該如此。
這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凡人大禹。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