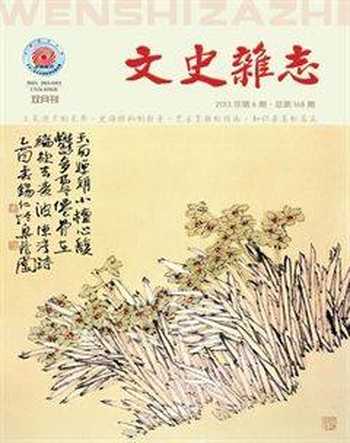漢區孝文化在彝區的適應傳播
徐雷 肖健
中華民族的孝文化源遠流長,發展豐滿,以各種形式對中國民眾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其中,具有傳奇色彩的董永傳說,不僅在漢區廣泛流傳,而且通過翻譯實現跨文化的傳播,在中國相關少數民族中流傳。《彝族傳統孝文化載體<賽特阿育>研究》(羅曲、王俊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一書所展現在讀者眼簾的,就是對董永行孝如何通過翻譯民族化、地域化,在彝區“適應性傳播”的研究。
中國古人皆重視人倫規范,所以孝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從國家政治生活中“以孝治天下”來看,還是從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百善孝為先”或者個人教育啟蒙中的“首孝悌,次見聞”的觀念來看,孝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需要,已滲透進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將之升華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并與“忠”產生聯系,忠孝并提。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孝文化作為中原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被周邊少數民族所民族化、地域化而加以利用乃久已有之。但是孝既是一種思想倫理意識,也是行為表現。這種意識和行為,作為孝文化的兩個方面,如果要加以傳播,并使之在社會產生作用,就不能用抽象的說教方式。所以,孝文化在傳播中,出現了文學欣賞性很強的、以董永為主人公的傳說故事,并通過翻譯而實現跨文化的傳播,在相關少數民族中傳播。
彝文文獻中的《賽特阿育》,是對歷史上董永行孝傳說的翻譯。彝族孝文化長詩《賽特阿育》,加上譯者自序,從勤勞善良的賽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求子,到董伏安時來運轉,一共有一十三個部分。在譯者的自序中說:
彝家有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化,但都成了過去。現在漢文化占了統治地位。我閣尼舒叔,雖然沒有明說,心頭總是在想。現將書上看到的一則故事,改編后用彝文寫一下來,讓后人,尤其是有知識的后輩,從中領悟作者的用心,發揚彝家的固有傳統,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
這里說的“改編”,其實就是翻譯,只不過是這種翻譯表現出一種民族化、地域化的“再創作”特色,是一種“文化”的翻譯。這里所說的“一則故事”,就是董永行孝的傳說。但是作為孝文化的載體,有關董永的傳說版本較多,文體除詩體外,還有散文體的傳奇,劇本等。《彝族傳統孝文化載體<賽特阿育>研究》的作者,對流傳于漢區的孝文化載體董永傳說的各種文體、版本與彝文文獻中的《賽特阿育》進行了比較研究后,鎖定了文本源為評講《大孝記》和寶卷《天仙配》。
彝漢兩族的社會生活是有差異的,社會發展的進程也不同。《大孝記》和寶卷《天仙配》的創作,都是以漢區文化為基礎的,反映的是漢區的社會生活,如果絲絲入扣地將它們直譯介紹到彝區,就會因為文化基礎的原因而達不到傳播的目的,也沒達到譯者關于“從中領悟作者的用心,發揚彝家的固有傳統,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的翻譯目的。所以,翻譯者在將董永行孝傳說的相關文本翻譯成《賽特阿育》時,進行了相應的民族化,以便在彝區有效傳播。《彝族傳統孝文化載體<賽特阿育>研究》一書的作者,對譯者為了董永行孝故事在彝區的有效傳播的民族化手法進行了認真研究。首先在作品主人公的姓名上,就漢文文本中的《天仙配寶卷》而言,依次出現的人物有:1.董善,他是后來董永的父親;2.馮氏,董善之妻,即董永的母親;3.董永,乳名永生子,是董善夫妻之子;4. 教書先生尤文顯,是董永仕途的重要人物;5.富豪尤華,是解決董永葬母費用的關鍵人物;6. 老婦人,尤華之妻;7.玉皇大帝,天上、人間的最高統治者;8.日月游神,其職責為受玉帝之命察看人間事象;9.因偷王母胭脂而等待發落的七神姑,即其他異文所說七仙女;10.王母,玉皇大帝之妻;11.尤家的老管家;12.尤大公子;13.賽金,尤華之女;14.尤二公子;15.鄧天君,玉皇大帝的使臣;16.店主李梅及妻姚氏;17.宰相趙京善;18.趙金定,趙京善之女,董永之妻;19.御史;20.皇帝唐太宗;21.董仲書,董永與仙女之子;22.董仲義,董永與賽金之子;23.陶貴生,與董仲書一同讀書的同學;24.袁天罡,算卦先生;25.五個冤魂;26.閻王。
在《賽特阿育》中,依次出場的是:1.賽特董哲安,他是董永的父親;2.賽特懂哲安之妻釜史妮妮,她是董永的母親。3.舉祖,他是相當于玉皇大帝的最高統治者,在文本中表現出仁慈正義;4.天神微察魯特汝、杜那沓、恒諾布,其中的微察魯特汝為賽特阿育的投生者;5.賽特阿參,賽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的兒子,后來讀書時老師更名為賽特阿育。6.教書先生,他是賽特阿育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人物。7.色特阿治,當地富豪,文本所述不是為富不仁者;8.仙女倫霓,她是天君舉祖的愛女即七仙女;9.阿治汝額,賽特阿治的大兒子;10.天臣諾婁則;11.阿治嫩念,賽特阿治的愛女;12.阿治汝鳩,賽特阿治的二兒子;13.阿育董伏,董永和仙女之子;14.皇帝;15.武帖呷,與董伏一同讀書的同學;16.鬼谷子,算卦先生;17.五個冤魂,皇帝錯殺的五人;18.翁祖,管理陰間的最高權威即漢語中所說的閻王。
姓名雖然是一個符號,但這種符號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之中的,是確認文化主體民族身份,從而決定自己是否和這些文化主體認同,進而是否認同這些文化主體所負載的文化。所以,譯者將漢文文本中的相關人名彝化為彝族人姓名,其作用顯而易見。
《彝族傳統孝文化載體<賽特阿育>研究》的作者,在對作品主人公姓名民族化的比較后,還對情節內容的民族化進行了比較研究。翻譯其實就是一種文化的傳播,所以這種研究,向我們展示了歷史上彝漢兩族文化傳播中的翻譯技巧。它同時告訴我們,跨文化傳播,必須進行必要的民族化,才能適應受傳者的社會生活文化,所要傳播的文化信息才會為受傳者所接受。其最終所實現的將一種文化信息從這一民族傳播到另一民族,從大的方面說,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從小的方面說,達到了翻譯者的目的。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成都)歷史文獻學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