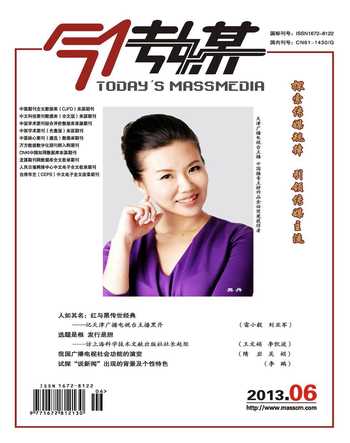從“五W”模式看網絡輿論監督的變化
賀立凱


摘 要:當前,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網絡輿論監督發揮了傳統媒體無法發揮的作用,并在實際監督過程中解決了許多問題。因此,學術界對網絡輿論監督的研究予以了高度重視。本文擬從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五W”模式入手,結合當前國內的網絡輿論的熱點問題,研究探討網絡輿論監督所引起的傳統輿論監督各要素的變化。
關鍵詞:網絡輿論監督;“五W”模式;無眾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6-0023-02
輿論,在我國古代又稱為“輿誦”,是指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里,公眾對于特定的社會公共事務公開表達的基本一致的意見或態度[1]。網絡輿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網絡輿論,就是通過互聯網表達的社會輿論,幾乎包含了所有的社會輿論形式。而狹義的網絡輿論,則僅僅是指網民作為輿論主體,在網上表達的輿論。
何為“網絡輿論監督”?有學者提出,網絡輿論監督是指廣大公眾利用網絡空間發表言論、表達意見、實現監督[2]。另有學者認為,網絡輿論監督指社會公眾利用互聯網的輿論表達方式,對國家事務、社會現象和事件、個人行為發表自己的觀點、意見和看法[3]。還有學者指出,網絡輿論監督指的是以互聯網為平臺,通過網絡技術和各種網絡形式了解國家社會事務,廣泛、充分地交流和發表意見、建議,對掌握一定社會公共權力者行使權力的行為進行監督的過程[4]。
通過以上對概念的厘定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對“網絡輿論監督”定義的表述不同,但是都含有幾個基本要素。即網絡輿論監督的主體是社會公眾,監督的對象是國家事務、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等公共事務,監督的途徑是通過互聯網絡,受眾從傳統的信息被動接受者變為主動的信息發布參與者,而眾多學者也一致認為,網絡輿論監督能夠帶動其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對現實社會起到監督、檢查和評定的功效。這正構成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五W模式”,即控制分析、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分析。下面,本文將從這五個方面具體展現網絡輿論監督相對于傳統的輿論監督模式帶來的新變化。
一、輿論監督主體的平民化
網絡作為新興的第四媒體,由于其較低的門檻限制以及較大的自由度,甫一出現便受到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熱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2011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見圖1[5]:另據《人民日報》“社會觀察”版與人民網的聯合調查,在所有參與調查者中,有87.9%的網友非常關注網絡監督;93.3%的人在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選擇網絡曝光。有50.6%的網友認為網絡監督非常必要,是對傳統輿論監督的有力補充[6]。
圖1 中國網民規模與普及率
以上調查結果說明,相對于傳統的輿論監督而言,網絡輿論監督的主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少數的掌握司法、媒體等資源的精英階層轉變為人數眾多、社會階層更為廣泛和多元的普通百姓。開放的網絡使普通百姓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打破了精英階層對媒體話語權的壟斷。曾經沸沸揚揚的黑龍江方正縣為開拓團立碑的事件,正是因為經微博披露后網民形成的一邊倒的網絡輿論給當事方造成的巨大壓力,最終才被迫將其拆除。此外,近幾年不斷活躍在各個熱點事件中的“網友調查團”,也悉數由生活在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構成,這體現了輿論監督的主體出現的顯著變化。
二、輿論監督對象的針對性
如果說輿論監督主體的變化是質的改變的話,那么網絡輿論監督帶來的監督對象的變化更多的表現在形式上。這種形式的變化主要是指從之前的針對“有關部門”輿論監督的泛泛而談,轉變為由某個人或者某群體而引起、進而針對特定部門或制度的輿論監督。
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就是其中的鮮明代表。當時,原籍湖北黃岡的孫志剛被廣州市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后雖經官方聲稱為收容所員工犯罪的個案,但是經廣大網友的持續關注和追問,引發了中國國內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中國政府之后頒發新法規將此制度廢除。
2011年6月20日,新浪微博名叫“郭美美Baby”的郭美玲在網上公然炫耀其奢華生活,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其認證身份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這一舉動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有網友稱她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女兒,由此引發很多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的非議。雖然隨后中國紅十字會稱“郭美美”與紅十字會無關,但是已經引起了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以及整個慈善行業運作模式的強烈質疑,最終迫使其撤銷商紅會。
與此類似的還有甬溫線事故、陜西省安監局楊達才“微笑表叔”事件等等,這些轟動一時的網絡事件都是由于某個人或某些人引發,在網上曝光后迅速發酵的,網友強烈的輿論監督指向其背后的相關政府部門,暴露出不為人知的內部問題,并迫使其改革,是輿論監督對象在網絡時代發生的新的變化。
三、輿論監督形式的多樣化
傳播途徑和方式是網絡輿論傳播相對于傳統的輿論傳播最大的變化,其輿論監督的途徑無疑都是借用了在中國迅猛發展、至今方興未艾的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技術在中國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一日千里。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國IPv4地址數量為3.30億,擁有IPv6地址9398塊/32,域名總數為775萬個,中國網站數量為230萬,國網頁數量達到866億個。[7]
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無眾傳播”的概念。無眾傳播是一種傳受雙方互動性強、以使用者自我為中心、淡化傳受者觀念的信息傳播方式。它與大眾傳播、分眾傳播的不同特點見表1[4]:
表1 三種不同概念的傳播對比
通過表1可以看出,互聯網的應用使得輿論監督的受眾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無眾傳播從傳統“點對多”單線的傳受方式轉變為“點對點”、“多對點”的互動交叉的網格狀,其受眾處于中心地位而非之前單純的被動接受者。博客尤其是微博的興起是這一變化的最直觀的體現。以往在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下,受眾只能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輿論監督意見的反饋和表達既沒有形式的可行,又不被重視。而現在,受眾已經逐漸上升為整個信息傳播活動的核心地位,信息接受者不但擁有多種信息接收的選擇權,而且不再滿足于簡單的信息接收活動,而是嘗試使用媒體發布自己掌握的內容,因而成為輿論監督活動的“傳者”。
四、輿論監督效果的顯著性
網絡輿論監督具有傳統輿論監督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其效果令傳統媒體監督難以望其項背。比如上文提到的孫志剛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都起到了傳統輿論監督形式無法達到的社會效果。有學者認為,相較于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網絡輿論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程度與水平不僅代表著國家的民主化與法制化的程度與水平,也是人民實現民主權利的重要途徑。同時它實現了社會公眾作為監督主體的本位回歸,并在具體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8]。同時,不少學者也高度評價網絡輿論監督的作用,比如為民意的表達開辟了新的道路、更具有過程監督的意味、增強了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互動等。
但是,網絡的運用對于輿論監督是雙刃劍。由于監督者身份的隱匿性、速度迅捷性等特點,其導致的負面影響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深入探討。由于網絡輿論監督缺乏嚴格意義上的信息“把關人”,導致信息的發布與傳播上過于隨意,極大地影響了網絡輿論監督的效力。網絡輿論監督過程中帶有情緒色彩的言論較為突出,容易產生“網絡暴力”現象。網絡輿論監督還可能通過各種爭辯說理之外的行為如“人肉搜索”、曝光隱私等其他非正常的方式對監督對象進行報復或打壓,讓所謂的“被監督人”失去反擊之力[9],從而造成對當事人的人身權利的侵犯,這些都是我們今后在研究過程中不得不重視的問題。
綜上所述,相對于傳統的輿論監督形式,網絡輿論監督的主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少數掌握話語權力的知識精英轉變為社會階層更為廣泛的網民,打破了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過程中的話語壟斷。監督的客體在形式上更為靈活,由之前的泛泛而談轉變為針對性更強的社會制度或者機構。依托方興未艾的互聯網技術,網絡輿論監督深入到網民的日常生活,出現了“無眾傳播”的新趨勢。同時,網絡輿論監督具有傳統輿論監督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監督效果令傳統媒體難以望其項背,當然也不能忽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網絡暴力”等問題。這些變化不斷促使網絡這一新媒體在新的社會輿論格局中占有愈加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1] 李良榮.新聞學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王曉陽,李昕燃.淺析網絡輿論監督的影響力——以“杭州富家子弟飆車案”為例[J].新聞知識,2009(9).
[3] 曹維康.2008年中國網絡輿論監督的光榮與夢想、問題與挑戰[J].新聞愛好者,2009(3).
[4] 李偉征.網絡的輿論監督[J].新聞愛好者,2009(9).
[5]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1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R].2012.
[6] 網絡輿論監督倍受關注[N].人民日報,2009-02-03.
[7]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1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R].2012.
[8] 雷建軍.視頻互動媒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9] 關梅.我國網絡輿論監督的意義、問題與出路分析[J].新聞界,2009(3).
[10] 牟雯琪.從網絡熱點事件看網絡輿論監督[J].青年記者,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