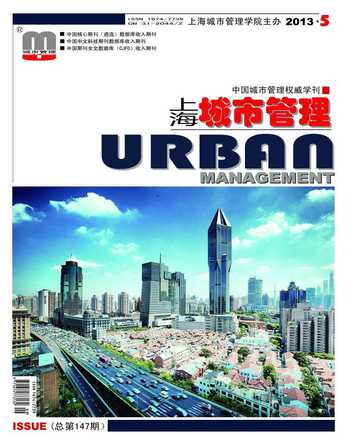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戰略中的發展規模與承載閾限

導讀:世界范圍內,城市化進程愈演愈烈,中國則提出新型城鎮化的戰略,其中不可逾越的一個問題是:城市究竟可以有多大?從“承載力”的角度出發,論證城市發展終將以生態環境的可能邊界為約束,只不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更佳交通條件以及貿易能力的城市將從“承載力”的貿易中獲益,從其他地區輸入“承載力”,從而擴大其城市發展可能的界限。就此而言,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盡最大可能避免城市規模向其承載力極限靠攏將是未來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決定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城市規模;承載力;生態環境;新型城鎮化
引言
自2012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新一屆政府領導人的就位,有關城鎮化的戰略與政策陸續擺上了議事日程①,相關的論述及報告也日益增多,各地也逐漸燃起新一輪的“造城”熱情,鄉鎮地區想著升格為縣城,縣城想著升格為地市,地市想著升格為單列市或大城市,大城市則想著升格為都市,而都市則想著升格為“國際城市”,在計劃造城的年代里,這樣的一種熱情和理想其實無可厚非,歷史上的很多例子告訴我們,只要中央政策允許,在資源累積的效應下,即便原本是一個小漁村,也可以扶搖直上,變為大都市。不過,計劃造城的模式走到今天,似乎已不可持續,因為地可以“圈”,級別可以“升”,人口也可以“遷”,甚至“公平”也可在計劃下指日可待,這些過程計劃之手都可以實現,但有一樣東西計劃似乎無能為力,那就是“承載力”,更具體一點,就是基于生態環境基礎上的人口承載力②。如果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文明的發展足以讓我們克服所有前進中的障礙,那么,唯一的例外便是承載力。同樣是歷史,各種文明的消失、多處古城的湮滅告訴我們,即便你曾經擁有過多少的輝煌和業績,但面對大漠風沙、氣候驟變、海水入侵等等觸及“承載力”底線的生態環境災難,再堅固的城市也會頃刻間灰飛煙滅。由此,一方面,我們有必要繼續沿用各種計劃和市場的手段來推進城鎮化進程,而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必要探索“承載力”對城市規模的客觀影響,使得我們的新型城鎮化盡可能地在承載力邊界的范圍內運行。
一、“承載力”挑戰下的經濟學范式
就城市規模與承載力的既有關系而言,我們可以直觀地觀察到的是,各種城市生態環境災難的發生及其災難性影響,在此之前,人們甚至對承載力的存在知之甚少。盡管有關生態環境災難及其后果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經濟學所需研究的命題,但實質上這正是各種經濟發展理念長期侵蝕下的一種結果。
(一)農耕時代:小農經濟思想下的承載力極限
譬如,農耕社會里,只有水土肥沃的地區才能繁衍出人種與人口,但隨著“馬爾薩斯”現象③的出現,在自發的小農經濟思想指導下,精耕細作成為最后的選擇,土地肥力被不斷透支,同時還不斷通過生育來增加“勞動力”,結果是總人口在不知不覺中接近并突破以土地為代表的承載力極限。要知道,通過增加勞動力來提高農業產出,這樣的一種經濟發展理念或思想在承載力極限的范圍內并沒有錯,事實上也與后來出現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強調要素稟賦的思想相契合。但無論是強調靜態的小農經濟思想,還是后來強調動態的現代經濟學(從古典到新古典),都將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劃定在行為主體的個體范圍內,也就是從一國/地區,或企業或個人所擁有的要素規模及結構出發,來計算各種技術條件下的最大可能性邊界(如圖1)。
圖1中,X、Y分別代表所需的不同生產要素,曲線上的各個點代表不同的要素組合,同時也代表社會產出和福利最優的點。理論上而言,兩種要素間存在完全替代的可能性,這也就是我們用一種廉價要素替代另一種昂貴要素后,產出水平不變的簡單道理所在。
表面上看,圖1似乎也包含了“承載力”的意思,也就是個體不能越過所擁有要素的承載邊界來生產,但事實上,這樣的計算只是表達了可能性,社會經濟發展所需承載力要素(主要體現為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土地、食物、水資源、礦產、能源等等)并非沒有上限,直觀地看,這個上限便體現為人口數量意義上的生態環境“承載力”。
以圖2為例,在圖1的基礎上,我們添加了兩條直線,分別代表決定生態環境承載力的因素C1和C2,它們的大小無疑約束著生產可能性邊界的范圍,并使得生產出現了上限。實際上,這個上限正是生產所有這些承載力要素的“生態環境系統”,而這樣的一個系統不僅在局部地區范圍內其內部組成相互間的交叉性,進行往復循環,更重要的是,它的構成成分還在頻繁地進行著跨地區交互,也就是全球范圍內進行往復循環。
(二)工業時代:經濟體系交互下的承載力轉移
在歷史上的前工業化時代,繁榮的地區在短期內受上述經濟思想指導而快速地突破本地生態環境發展的約束,但同時,它又無法通過經濟體系的交互性來有效地轉移其承載力約束,結果是文明與城市的衰敗。而到了工業化時代,這樣的興衰周期似乎被拉長了,我們在某些區域的范圍內往往已經在較長時間里觀測不到承載力的約束性,譬如發達國家,又譬如聚集了大量人口的都市,即便如此,這并不能表明我們的發展能力已經完全解除了承載力方面的后顧之憂。只不過,鑒于上述生態環境系統的交互性可能,全球化的貿易條件讓我們將承載力的約束及后果從一地轉移到另外一地,即經濟體系的交互性增強了地區的承載力水平。但要知道,從全球范圍內來看,承載力并沒有實際的提高,只不過是進行了結構上的轉移,發達國家和地區承載力名義提高的代價其實便是落后國家和地區承載力的急速下滑,甚至是掉入深淵(譬如受氣候變化影響,某些島國已經因為海平面上升而被迫遷移)。
由此可見,就承載力而言,某些國家和地區的確可以通過技術條件或貿易條件來修正本地的界限,從而繼續沿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指導經濟發展,但對于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這樣做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一方面,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承載力約束本身就很強,生態環境基礎比較脆弱;另一方面,不僅無法輸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承載力”,而且還要輸出本地的承載力,兩相作用下,最后的結果便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承載力水平逐漸被侵蝕。當然,如果從全球生態環境交互的角度來看,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載力水平的下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為最終必定會逐步蔓延開來,波及那些先發或者承載力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因此,“承載力”的約束對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啟示在于,在現有的方法下,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生態環境系統在生產函數及發展決策中的重要性。否則的話,經濟體系便會受到生態環境的拖累:先從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然后到生態環境基礎較好的地區,各種與承載力相關的病癥會逐步蔓延出來,并最終損害社會整體福利。而如果我們把代表生態環境的“自然資本”視為“美麗”的話④,那么還原“自然資本”與其他資本的比價關系,并有所提高“自然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就成其為重視“美麗”的“美麗主義”經濟學研究范式及體系(李志青,2013)。[1]
二、“承載力”挑戰下的城市化規模
“美麗主義”的經濟學研究范式對于城市發展有何借鑒意義呢?事實上,在城鄉的結構中,城市就好比是“先發”的地區,在其發展之初,根據同樣的道理,城市所代表的地區也擁有著較高的承載力水平,而城市也就在較高的承載力基礎上得以生存并發展,問題是,從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來看,不同的城市,其規模(人口密度意義上的城市規模)有大有小,而同樣一個城市,它的規模也不是一成不變,有的是從小變大,而有的則卻在萎縮(UN Habitat,2008)。[2]怎么解釋其中的區別呢?在聯合國的一份世界城市發展報告中,城市規模變大的可能原因有“城市優先性(Urban Primacy)、經濟及產業政策、生活質量變化、行政推動”等幾大因素⑤,此外,城市由大變小的成因則是生態環境質量等方面的自然選擇結果(UN Habitat,2008)。[2]這里面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示,如果把城市比喻為一個木桶,那么承載力會不會是木桶中最短的那根木板,并最終決定了城市規模的極限值?其中有必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體現為生態環境質量的承載力對于城市的發展有何影響?二是城市的發展又如何反作用于生態環境質量?
(一)城市起源與環境承載
1.城市起源于優質生態環境
上述第一個問題其實關涉城市的起源,如前所述,在歷史上,可以發現,最早的定居點(城市的前身)往往地處水土肥沃之所,就生態環境質量的角度來看,相比其他地區,這樣的地方首先是氣候比較適合人類聚集居住和繁衍,同時,因為物產豐富,可以支撐各種消費需求。此外,還有一個條件非常重要,那就是交通便利,尤其是水路交通便利。這些特點意味著,在工業化之前,城市的確正是因為有著較高的自然承載力而逐步成長起來的。拋開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就業、價格、貨幣等概念,可以發現,能夠滿足人的生存需要是人類選擇定居并擴大規模的最原始出發點。就此而言,承載力在絕對意義上決定了城市的產出邊界,并間接地決定了城市的規模。當然,即便如此,也存在某種外溢的可能,那就是通過便利的水路交通,工業化之前的城市也可以與外界建立進行一定程度的經濟交互,即貿易。在中國的宋代,大都市的規模可以達到100萬的“天文數字”,其必備的條件便是逐步開挖、并貫通南北的京杭運河,大量的南方物產通過運河源源不斷地被輸入,從而支撐起超過本地承載力的城市規模。如果從生態環境的視角進行思考,實際上,運河的開通本身也是城市承載力的一種體現,即城市的生態環境條件在新的科技水平上支撐起了更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這一點還將在后面部分詳細論述)。這是工業化之前城市發展的緣起,那么工業化之后呢?
2.城市發展于經濟集聚效應
自1776年開始,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現代經濟學也應運而生,對現代城市起源的解釋也開始系統化,即主要從提高效率的角度來論證城市發展后帶來的集聚效應,同時將邊際分析的方法作為城市發展的約束條件。簡單而言,城市通過創造就業以及福利來增強其吸引力,并提高其經濟意義上的吸納能力,從而推動城市一步一步地擴張,然后在其邊際規模效應不斷遞減的情況下,當規模的增加再也無法提升邊際產出時,城市的規模增長運動便戛然而止。
在這樣的理論下,就業及價格等經濟變量就至關重要。一則城市依靠產業來帶動就業并創造產出,二則城市靠產出來穩定價格水平維持福利。由此,工業化與城市化兩大進程并相依相隨,為什么呢?因為,只有工業化才足以創造規模龐大的就業,并支持城市發展。而恰恰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人口呈現出大爆炸的增長趨勢,按照人口規模與工業化創新發展關系的研究(Kremer,1993),[3]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人口規模基數是決定創新水平的重要因素⑥。因此,人類也便擁有了一條迥異于“馬爾薩斯陷阱”的發展道路,那就是在人口規模上升的持續壓力下,通過工業化來推進城市化,繼而突破產出的約束,提高福利水平。
3.城市蓬勃于工業推動程度
在這樣的分析路徑中,承載力似乎已經不再重要,抑或是工業化城市的發展已無承載力的約束可言,但事實上,即便是工業化帶動下的城市化,我們依然可以發現不同地區的城市規模大小不一,如果從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城市規模的不一致所體現的是工業化程度的差異,那么,工業化程度又為何不一樣呢?或者工業化的條件有哪些呢?就地理經濟的角度看,全球范圍內,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城市或地區其分布基本與農耕時代的主要城市的分布相比,起碼在其中一個特征上沒有太大的區別,也就是同樣具有便利的交通。當然,現代城市的主要對外交通已經不限于水路一種了,還包括了公路、鐵路、航空等主要交通方式,作為工業化主要成果,各種現代交通運輸方式蓬勃興起意味著貿易范圍的全球擴張,城市間的經濟交互能力大大增強。這意味著,工業化不同于農耕產業的地方在于,它的生產能力和規模可以借助于現代交通方式而高度依賴于外部世界,這樣一來,交通或貿易條件便成為解釋工業化程度差別的主要成因。
4.城市培育于生態環境建設
為何有的工業化地區或城市的交通運輸能力高,而有的則比較低呢?決定高低的關鍵因素依然是生態環境質量代表的承載力,從系統交互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水路、陸路還是航空等交通方式,它們的有效性與所處的生態環境質量都緊密相連,很難想象,在一個環境惡劣的地區,即便修建了各種交通設施,會有多高的利用頻率。抑或是在一個生態脆弱的地區,盡管山清水秀,但卻僅能承載較小容量的人口規模,也無法支撐起龐大的工業化體系,進而也就不能發展成為一個大規模的城市。就以上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部分地回答“城市可以有多大”這個承載力的問題,那就是原則上必須在生態環境的承載力范圍內來規劃城市發展的規模,這個承載力既包括支撐本地直接產出的生態環境條件,譬如大氣、水體、土壤等環境要素的質量,同時,也包括能夠支持城市對外經濟交互能力的各種自然條件或基礎。
(二)城市環境與承載邊界
一般而言,傳統的理論往往將承載力木桶中最短的那塊木板界定為水或食品(Cohen, 1995[4];李志青,2013[5])。但基于城市的獨特性,事實上,在支撐城市發展的承載力中,最薄弱的環節是支撐對外交通的生態環境條件。由此出發,我們繼續回答上述第二個問題,即城市又如何影響生態環境質量呢?或者,城市的發展會否擴展其承載力的邊界呢?
1.城市提升環境質量的兩重悖逆
基于效率的原因,主流理論強調城市發展在各個領域所表現的積極性(UN Habitat,2012[6]),其中包括城市發展對于提升生態環境質量的價值。主要的原由在于,一方面,因為城市有集聚功能,在提高人口密度的同時,可以減少人均的生態環境消耗,相比于人口分散的鄉村地區,相同人口總規模下,城市規模的擴大相當于提高了城市人口占總人口中的比例,進而降低總人口規模對生態環境的消耗程度。在經濟學中,這一點可以用規模經濟效應來概括,相當多的文獻對此進行過詳盡的論證(陸銘等,2012[7])。另一方面,在諸多文獻中,尤其是有關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研究報告中(UN Habitat,2012[6];The World Bank,2010[8]),都認為城市作為人口載體,與其他的人口定居方式相比有著更強的學習能力,包括城市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保障人們的生活質量,城市內生有利的組織和制度促進技術改進和創新等等。這些都意味著,城市天然地擁有著提高利用生態環境資源效率的制度稟賦,同時更加重要的是,正是由于這樣的制度稟賦提高了城市生態環境資源的利用效率,進而對周邊及外部的生態環境資源產生了較強的“漩渦”效應,即城市好比是一個巨大的漩渦,強大的吸力將周邊的流水都吸了進來,并不斷地加強自身的能量(承載力)。
2.城市提升環境質量的承載短板
城市不斷像漩渦一樣增強了自身的承載力,這實際上恰恰解釋了上一小節所提為何傳統意義上的生態環境要素不再是城市發展的承載力短板的原因,在城市基礎設施支持及有利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下,城市不僅通過交通與貿易與外界發生經濟上的交互,而且還可以借助現代化的技術手段來從外部世界引入所必需的生態環境資源。譬如新加坡、我國的香港等城市就屬于典型的生態環境資源輸入型城市(Newman,2006[9]),如果僅以它們自身的承載力而論,它們是不可能擁有到現今如此龐大的人口規模。城市發展的過程等于是通過借用外部資源擴大了這些生態環境要素的邊界,反而讓其他的承載力短板(譬如區位等)更加凸顯出來。
(三)城市美化與歷史困惑
以上兩點便是城市化通常備受贊譽的主要原因,就承載力的約束性而言,長期以來,城市化的進程也并沒有加劇城市所處生態環境的惡化,相反,在一系列造城運動的推動下,部分城市內部的人居環境還在逐步改善,甚至得到美化。這樣的結果也往往給人以錯覺,以為城市真的不僅可以不斷擴大其邊界和規模,還可以緩解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的矛盾。然而,效率至上甚或是規劃/計劃指導下的城市發展是否真的走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困境?是否便屬于本文第二節所描述的“美麗主義”?事實上,上述有關城市發展積極性的論證至少忽略了兩點。
1.傳統城市理論強調規模的邊際效應
一方面,就總規模而言,在一定范圍內,城市發展后所增加的規模增量的確存在規模效應,也就是可以逐步以更低的代價來獲得相同的規模增量。但即便城市增長的邊際成本在遞減,如果就總規模而言,其總成本還是在增加的,從區域生態環境的視角看,其實邊際遞減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總規模是否在逐步向承載力水平靠攏,就此而言,城市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絕對影響無疑是在不斷遞增的(Newman,2006[9])。另一方面,就人均的生態環境資源消耗而言,城市發展后帶來的集聚效應會降低人均水平,也就是人均的承載力消耗在下滑。不過鑒于人口密度是度量城市規模的重要指標,在人口密度增速超過人均承載力消耗水平減速時,城市實則在不斷逼近承載力的最大容量。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誤區,即忽視城市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資源消耗的反彈效應。當城市發展被認為是有利于資源環境保護時,城市的發展反而可能會因此而加大資源環境的消耗。譬如,城市化(或城市群)被論證為有利于節能減排(陸銘,2012[7]),那么會推動更多的地區進入這個行列,從而加大城市在資源能源上的負擔,最后的結果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城市的資源環境消耗反而高于初始狀態。由此,城市規模層級的每一個增加都意味著對生態環境質量或承載力的侵蝕,在承載力有限的情況下,使得城市發展過程本身就在不斷逼近其承載約束的邊界。譬如,以城市的空氣質量為例,雖然有證據表明,城市人均的PM2.5濃度遠遠低于鄉村或者其他地區,但城市仍然不得不陷入霧霾圍城的尷尬境地里。單就這一項,我們便再無法自信滿滿地面對那些肯定城市發展積極一面的說詞。
2.有關城市發展積極性的論證還忽略了價格因素
如上所述,在一些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其規模擴張程度往往突破了自身的承載力邊界,為什么呢?因為它可以從外部世界的鄉村或者其他城市來輸入承載力,這就類似于發達國家通過全球化的貿易條件從發展中國家輸入“承載力”。在此,體現為生態環境綜合質量的“承載力”成為了可貿易品,其中固然有城市在技術、制度上“先發”優勢之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城市實際上是通過不對等的制度安排來獲得低廉的“生態環境”商品,從而為其規模擴張創造了低成本的有利發展條件。尤其是在城鄉二元結構明顯的地區,“工業品”貴于“環境品”的價格剪刀差極為普遍,城市正是利用這樣的剪刀差進行長期的原始積累,使其規模在“效率”的名義下得以快速增加。那么,為何在市場制度如此普及、公平觀念深入人心的情況下仍會存在這樣的“逆市場化”現象呢?究其原因,是因為“市場被選擇性地失靈”,也就是說,基于外部性的市場失靈眾所周知,但有的市場失靈被“計劃者”意識到,并迅速糾正了,比如衛生醫療、教育、交通、國防等,但有的則被故意忽略了,譬如生態環境的破壞。正是在此效應的作用下,作為可貿易的生態環境資源,其貿易條件被扭曲:一則“計劃”的市場定價過低,二則得不到法律保護。
由此,城市得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大量吸納外部世界的生態環境資源,其結果是,城市的承載力邊界得到了較大的提升,但其周邊以及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卻在不斷下滑,逐步逼近受到約束的邊界。這一點其實有目共睹,譬如以氣候變化為例,城市的規模擴張在以加速度吸納全球的石化能源,而城市自身也基本實現了更低的人均碳排放目標(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均碳排放都低于其國家人均水平,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人均碳排放仍高于國家人均水平(The World Bank,2010[8])),但那些氣候環境較為脆弱的國家和地區卻因此而飽受氣候變化的煎熬,氣候環境的變遷極有可能突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承載力極限。這便是承載力進行直接或間接轉移后的結果。不過,最后的結局還不僅于此,在全球生態環境與經濟的交互體系中,不同地區的承載力水平下降或突破最終都會波及城市自身,造成城市的萎縮。到目前為止,我們至少已經發現了城市萎縮的部分證據,一是城市原有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UN Habitat,2008[2]),另一個則是城市人口的郊區化(UN Habitat,2008[2];朱茜,2013[10])。
三、結論
城市究竟會有多大呢?究竟具有怎樣的適應生態環境及人口規模的合適承載力呢?通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一則,城市必須按照其自身的生態環境創造力約束條件來進行合理規劃其可行的規模水平;二則,城市還有必要對可貿易的生態環境資源凈流入量進行測算,按照不高于城鄉人均資源環境消耗量的水平來限制城市自身的發展規模。其中的關鍵在于是否糾正了生態環境資源在市場中的不利地位,是否消除了選擇性的失靈,以及是否更加地注重生態環境“之美”。否則,城市即便在短期內實現了“大躍進”式的發展,但假以時日,人為造出來的那部分規模終究是要通過不同形式“歸還回去”的,甚至于要還得更多。
說明:本文為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2013)、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3)以及上海市教委科創項目(201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2年12月17日。
②有關“承載力”的定義,可以見Dennis J. Mahar, 1982[1]; William E. Rees, 1992[2]; Joel E. Cohen, 1995[3]; Peter Newman, 2006[4]等。
③即人口增速超過耕地等物質增速,造成絕對貧困,從而抑制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的現象。
④基于審美的角度。
⑤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8.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2009.Harmonious Cities,London, Sterling, VA.
⑥Michael Kremer. 1993.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8, No. 3:681~716.
參考文獻:
[1]李志青.“美麗主義”與新型城鎮化[N].文匯報,2013-05-06.
[2]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2009: Harmonious Cities[M]. London:Sterling VA,2008.
[3]Michael Krem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681~716.
[4]Joel E. Coh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arths Human Carrying Capacity[J]. Science,1995(269):341~346.
[5]李志青.城市“水力”與新型城鎮化[N].東方早報,2013-07-01.
[6]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 Prosperity of Cities[M]. London:Sterling VA,2012.
[7]陸銘,等.集聚與減排: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C].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2012年會資料匯編,2012.
[8]The World Bank.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An Urgent Agenda[R]. Washington:Washington DC,2010.
[9]Peter Newma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ities[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2006(18):275.
[10]朱茜.中國城市人口居住郊區化的微觀動力機制研究[D].復旦大學,2013.
責任編輯:張 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