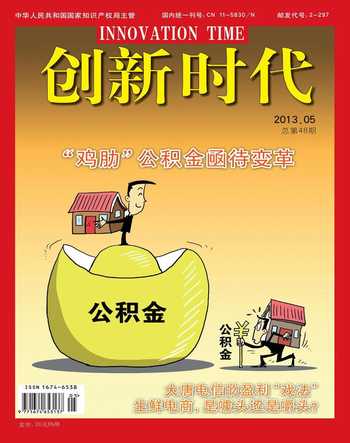不死的傳統,新舊文字的融合之路
王昆
移動互聯網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技術要素,它一手導演的大變革正轟轟烈烈地開展,簡單、粗暴、刺激、顛覆,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每天要花25個小時黏在這張網上,快樂至死或者抑郁而終。“動起來”是未來十年的大趨勢,簡單粗暴的趨勢毫不留情地帶走了傳統事物的固有優勢,科技、經濟、體育、娛樂、人民的監督力量和政治表達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還有用來傳承文明的一行行文字,也在這波洪流中幾經洗禮......
現在,提起文字人們腦海里首先浮現的可能不是散發墨香的紙質書稿,而是三星和CMI的高清顯示屏,或者亞馬遜的Kindle和蘋果的iPhone4S,姑且,先讓圖書和Kindle作為傳統和新興文字的代表,它們最直接的不同點就是傳播渠道,然而,這卻不是新舊文字真正意義上的分別,那些在內容、時效、權威性、受眾人群上的差異才是新舊文字本質區別,也正是這些區別才讓人挑起傳統與新興文字的戰爭,但事實上,它們根本不是博弈的關系。
雖然有此消彼長的趨勢,這個可以從報紙發行量和iPhone的銷量上窺見一些端倪,但新舊文字從來不是博弈關系,更沒有“誰要干掉誰的”劍拔弩張。新舊文字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只能共存,而且會相互融合,事實上,這種融合已經開始,包括媒體、小說和它們的從業人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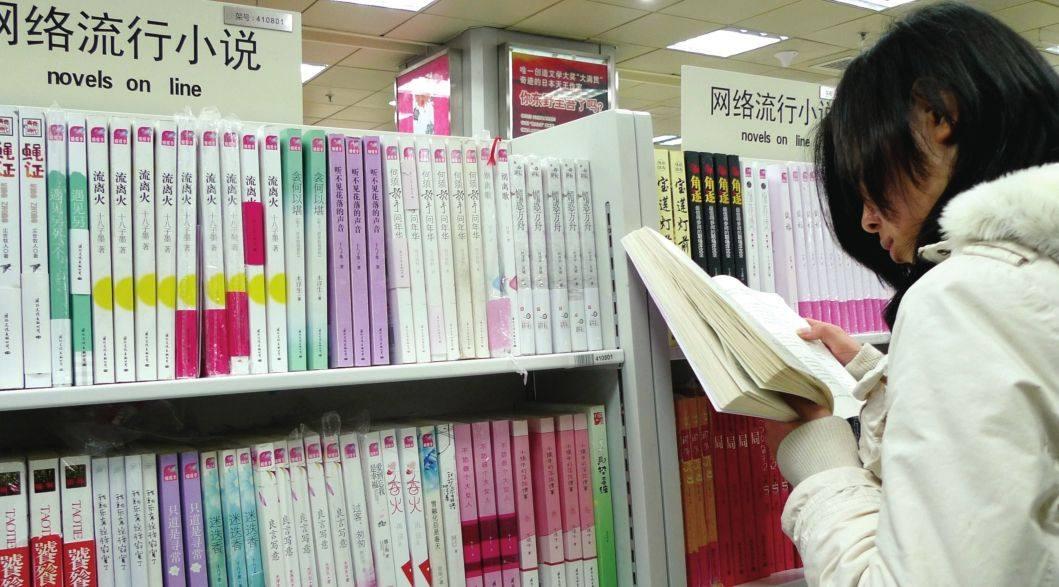
怒放的生命,傳統媒體沒有2012
每個新時代稍有雛形后,總會有大躍進的簇擁們盼望著大批的傳統事物可以慌忙猝死,現代史上,這些“被猝死”的傳統事物包括電影院、收音機、自行車和諾基亞,但如你所見,老家伙們的存在感雖然被削弱,但依舊能影響著一些有影響力的人,這讓他們生生不息,怡然自樂。
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也難免遭遇“被猝死”的尷尬,一場有關“紙媒數字化死不死的大討論”如火如荼,曠日持久,但如前文所述,新舊文字會共存,并且要相互融合,媒體自然也不例外。有網友調侃:互聯網時代,讀報是老年人的專利,顯然,這是膚淺的印象流結論。據一項權威機構調查,仍有大量的用戶選擇報紙作為重要的新聞和資訊的獲取渠道,這個“大量”并不比iPhone手機的銷量少太多,尤其是28-45歲社會中堅力量,讀報率要遠高于其他年齡段用戶,而受過高等教育和年收入6萬元以上的群體,則更有興致跑到圖書館而不是藏在被窩里閱讀時政新聞和商業觀點......
雖然受到數字化媒體的極大沖擊,但傳統媒體的固有特性,專業、權威、深度注定了其不可能無人問津,而且數字化媒體在急速狂奔之后,同樣會遇到自己的瓶頸,而這個瓶頸正是傳統媒體賴以生存的命脈。前不久,太原富士康爆發大規模暴動,倘若放到十年前,我們可能只會在《人民日報》上得知武警們如何英勇果敢,如今通過微博幾乎是現場直播,各大門戶網站更是第一時間貼出評論,沒錯,數字化媒體滿足了消費者追求速度的需求,但當消費者想要得到一些更深層次的內幕報道時,網站們就只能把《南方周末》或者《中國經濟網》等權威媒體的文章放到頭條上,這就是最簡單的新舊媒體之融合。
數字化媒體猶如攻城拔寨,來勢洶洶,走時匆匆,讓人暢快淋漓;傳統媒體則是好似蜘蛛結網、蜜蜂釀蜜,潤物無聲又經年累月,新浪也別嚷嚷著干掉《人民日報》,《南方周末》自然也不能取代網易新聞,二者各有優勢,新舊互補可能是最和諧的媒體發展之路!
網絡小說:失去了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
文人相輕,是中國文學界乃至世界文學的特色,偉大的友誼可能存在于牛頓和法拉第之間,愛因斯坦和霍金也可能會一起研究時間和光速的秘密,但倘若雨果、托爾斯泰或者馬克吐溫生活在一起,絕對鮮有機會湊早一起把酒言歡,觥籌交錯的,因為他們總會覺得身邊的人是弱智。
在網絡文學野蠻生長的時候,就有傳統文人跑出來大吐酸水,嘲諷到:網絡文學失去的東西正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但同樣如你所見,網絡文學火了,已經火到不能再火,據某項數據調查,燃文小說網每日訪問量上億,這個數字可能比自清朝開始累計的《紅樓夢》讀者還要多一些,而紅袖添香每天的訪問量同樣高達6500萬,那些寓意深刻、富有教育性、猶如史詩般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或者《駱駝祥子》等越來越多地敗給了玄幻、穿越、宮斗等快餐小說。由穿越小說改編的《宮》風靡2012,主演楊冪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了朱自清和賈平凹,有些藝術學院的考生竟言之鑿鑿地向考官說曾經讀過“魯迅漂流記”這部原著,即便是當下最火傳統作家莫言也是因諾貝爾的光環才被人熟知,否則,人們只知道《紅高粱》是由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就更不要提什么《豐乳肥臀》、《蛙》等作品了,越來越多的事情證明,當下的快餐時代,網絡小說更讓普通消費者受用,傳統文學家泛酸也于事無補。
其實,傳統作品和網絡小說根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讀物,前者是文學家們為自己而寫,闡述的是自己對當時社會的看法、見解和具有深度的思考,他們甚至不知道未來讀者是誰;網絡小說的特點則是更照顧讀者的情緒,寫出來的東西第一使命是迎合讀者的需求,這也注定了其不能成為影響一代人的經典作品。一本經典的世界名著可能流傳千年,而一部網絡作品的壽命可能短到只有幾個小時,但后者的存在價值在于短時間內緩解讀者現實生活中的壓力,穿越小說的男主人公往往戰無不勝,項少龍突然成了西楚霸王的老子,女主人公則收獲愛情,晴川不也順利地成為康熙爺的兒媳婦嗎?這樣的橋段讓飽受生活壓力折磨的屌絲們沉醉其中,無法自拔,大有春秋大夢不愿醒來的貪戀,傳統文學里的哲思、感悟等則不免被拋之腦后,這也是特定時代最無奈的悲哀。
相比于媒體,傳統文學和網絡小說更顯得涇渭分明,融合之路顯得更加充滿荊棘,但同樣它們會長期共存,而且遲早會相互融合,典型的代表如寫傳統文學的叛逆代表韓寒的發跡,正是借助網絡的推動力。
新舊文字,工作者的相互轉化
或許僅從傳播渠道上看,我們無法分辨韓寒這樣的作家該屬于哪一派,早在上世界90年代,《三重門》的火爆就讓這個叛逆少年擁有50萬的身價,這些錢可以在普通城市全額購買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然而,現在大多數人會通過網絡閱讀韓少的作品,點擊近6億的新浪博客本身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而作家維權聯盟假聲討百度文庫,發布首款Android閱讀APP《一個》,都已經注定了韓寒早就找不回傳統的文學創作者的身份了!
事實上,韓寒的故事代表著未來的趨勢,也即新舊文字工作者的轉化。
如前文所述,新舊文字本來就不是博弈關系,而是相互融合,這在文字工作者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毫不夸張地講,互聯網改變了時代的一切,傳統文字工作者自然不能獨善其身,而渠道的優勢更是讓傳統文學望塵莫及,有時候精心準備三個月的雜志產生的影響力還不如三分鐘編寫的一條微博,這種赤裸裸的利益和影響正誘導著越來越多的傳統文字工作者走向網絡,而他們的到來,又把長期積累的嚴謹作風帶到網絡文字上來,使之更具深度。
速度與質量如同魚與熊掌,新舊文字都不能兼得,倘若能夠很好地融合,讀者在吃魚的時候很可能產生舔一口熊掌的沖動,到時候不會再有新舊文字之分,也不會有渠道之爭,而只是剩下好文字與壞文字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