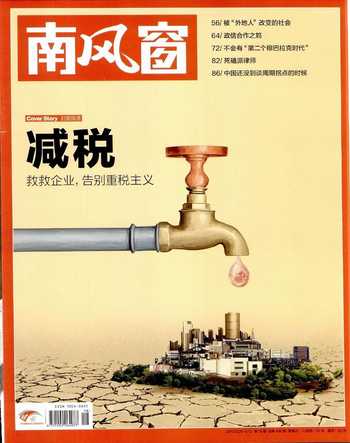國是2
國務院辦公廳
使政府把精力放在日常行政管理上
8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四個一律”,要求減少評比達標表彰評估:“沒有法律法規依據和中央文件規定的,一律不得開展;與政府職能無關、對推動工作沒有實際意義的,一律不得進行;已取消的,一律不得變相保留或恢復;已轉交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承擔的,一律不得使用財政資金和向企業或社會攤派費用。”
政法委
不能因輿論炒作而作出違法裁決

中央政法委出臺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應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人及其親屬鬧訪和“限時破案”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指標。
財政部
推動省以下預決算的公開工作
財政部近日發布通知,要求在全面公開省級預決算及“三公”經費的基礎上,2013年進一步推動省以下預決算公開工作。2013年,各省應至少選擇20%的地市級和縣級地區開展“三公”經費預決算公開工作,2014年所選地區應至少達到省內同級政府數量的50%。原則上,應優先選取縣級地區。
輿論天然是權力
若對“權力在民”沒有異議,輿論權力與政府權力就可進行多番并提:都需要一個“民眾賦權”的過程,都關涉大小具體事務的處理,都具有不小的“強制力”,以及維護自我權力運行的排他機制。
權力本身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它其實一直在流動。常規媒體機構或曾暫時掌控輿論權力,但新技術已經讓輿論權力向新的輿論載體轉移。其間,舊有輿論權力由國家機關直接賦予,新的輿論權力則由民眾“直選”;權力的新舊代理人必然產生激烈的沖突;輿論權力的轉移是悄然發生、非正式操作的,并不存在制度設計和公平保障,輿論權力也難以逃脫權力的陰暗面。
決定由誰來充當輿論權力代理人的“賦權”斗爭非常慘烈,而且在權力最初轉移時,法律懲戒和道德規范一般不會及時跟進。買粉絲、造謠、炒作、相互攻擊等,就發生在這一通過“博眼球”、“受關注”來獲得“輿論賦權”的階段。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都足以對任何人產生毀滅性的誘惑。
近日被刑拘的網絡推手楊秀宇自白稱:“我變本加厲地策劃了許多虛假新聞,看到傳統媒體跟進報道的時候,我甚至會有快感……我最初的目的是進一步打造真善美,干一些正能量的事情,但后來我在金錢和真相面前選擇了前者……”權力帶給人滿足感和利益—或許一個變質了的權力行使者,最初也曾抱著善意的目的。
我們要想清楚,對舊有體制和行權人的不滿,是否讓我們過于簡單地將權力重新賦予給了我們并不真正了解的個人、我們并不真正看透的輿論。政治領域的戲劇表演傾向、操縱技巧以及暗箱操作的潛規則,在輿論場同樣存在,甚至可能更甚。
網絡輿論逐漸取代整體輿論,就注定了“輿論”的技術壁壘;有錢、有閑、有團隊的占據了大部分輿論領袖的位置,就代表了社會精英階層已經在瓜分輿論權力;國家權力對互聯網的“凈化”,就暗示著輿論權力斗爭的多力量角逐;最可能的是,輿論權力的新舊代理人相互妥協,完成權力的內部再分配,結成共同體。
輿論,并不一定就在民眾手中。在有限的幾個候選人里,民眾進行著仿若自主的選擇。而輿論權力,僅僅是眾多權力的其中一個戰場—還是民眾顯得最可掌控的一個。平穩、合理的賦權之后,還存在如何行權的問題,如何保證輿論權力的正常流動而不致于讓原有的輿論領袖壟斷或者“世襲”權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民眾如今的唯一要求似乎只是“不要投給那個最差的選項”,而不是選擇最好的那一個。 (戴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