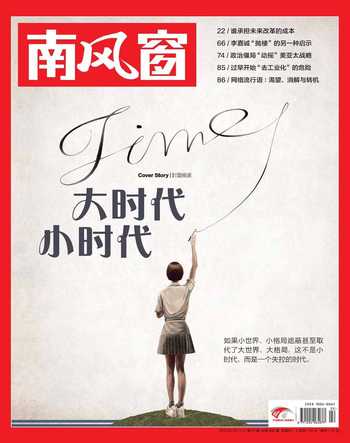誰是壞律師?
葉竹盛

近日多省律協接到上級通知,認為當前律師隊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極個別律師串聯、抱團、死磕、惡意炒作、觸碰政治法律底線……等行為”,要求各地進行調研,分析這些問題的危害性,以及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通知還要求各地律協形成書面材料,對這些突出問題提出對策和建議,尤其是對“個別問題嚴重的律師”如何加強“有針對性的措施”。
某省律協一位要求匿名的領導向《南風窗》證實了這份文件的上述內容,并據稱這份文件在他所在律協引起了強烈關注,而一些已經獲悉情況的律師則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認為這意味著律師隊伍將面臨整頓。
近年來,“死磕派律師”興起,律師經常超越案件本身,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最近的兩起案件更是將律師推到了輿論漩渦的中心,一起是“李某某強奸案”,一起是“夏俊峰案”。前者更被稱作刑辯律師的“滑鐵盧”,藉此,一些律師的公眾形象從“李莊案”時期的“崛起的法治力量”,迅速墜落成了名利場上的跳梁小丑。
律師職業面臨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前所未有地進入了同步狀態。
好律師,壞律師?
在進入自媒體時代之前,律師群體的形象,從未在中國公眾面前有過如此清晰而復雜的展現。當律師通過微博、博客等渠道,將案件暴露在公眾面前,訴諸公議之時,自身的種種表現也成為輿論檢視的對象。
如果說“李莊律師團”時代的律師尚能獲得一致的好評,到了“死磕派”群體涌現,針對律師形象的評價開始出現分化,而“李某某強奸案”中一些律師的表現,按北京律師劉洋的說法,則是“讓全國律師丟夠了臉”。
其中對律師形象最具有殺傷力的,無疑是李在珂律師為了當上李某某的辯護人而發給李某某母親夢鴿的幾條“雷人”短信:“一直想找一個大的案子辦成功擴大在全國的知名度,為將來當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加分”;“你可能失去了一個唯一有能力把這個案子翻過來的律師”;“我在外面名氣不大,可我在公檢法內部知名度是高得很,80年代官至處長的律師恐怕在全國找不出幾個”。
李案審理期間,夢鴿的法律顧問蘭和律師在微博上也批評了李在珂。李在珂進行自辯,并將蘭和“貶損同行”的行為舉報到了司法局和律協,同時舉報的內容還包括夢鴿一方提前公布律師辯護詞,暴露了部分當事人的隱私。
被李在珂舉報的蘭和也是備受質疑的對象。有過豐富媒體從業經歷的蘭和,以李家法律顧問的身份針對李案發表了諸多成功吸引眼球的言論。深圳律師肖海峰譴責蘭和使“案件辯護從庭上發展到庭外,辯論的對象竟然從公訴人發展到其他辯護人”,這“不僅超出了律師行業底線,恐怕也超出了老百姓的底線”。
同樣成為指摘對象的還有“夏俊峰案”的辯護律師。殺死兩名城管的小販夏俊峰一度以“平民英雄”的形象出現在媒體報道和律師辯護中。近日他最終被執行死刑后,法律界開始質疑夏案律師的辯護策略。
夏俊峰案的二審的辯護詞中有大段篇幅抨擊了目前不甚合理的城管體制,并結合有關證據和推測,得出夏俊峰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的辯護結論。將個人放到不合理的體制背景下進行辯護,業界有人批評稱,采用這種策略的律師不顧當事人的利益,目的是實現個人的抱負,畢竟“當事人不是花錢請你來推動法治進步的”。
但是在其他一些同樣影響力巨大的案件中,公議的標準似乎又悄然變化了。“劉志軍案”僅3個小時就結束了庭審,辯護律師錢列陽因此被批評為“不死磕”,配合表演了一場審判。
前不久,著名投資人王功權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代理律師陳有西一改往常一些案件中的高調,沒有披露該案的細節,也沒有組建聲勢浩大的“律師團”,此舉遭到多方批評,有人甚至譏諷道,陳有西已經被“收編”了。
陳有西向《南風窗》表達了遭受誤解的無奈,“有人想把王功權包裝成反體制的英雄,要我拉上幾十個律師死磕,這樣做雖然我的律師名氣會很大,但就等于把我的當事人犧牲掉了。”
業界除了對李在珂的言論呈一片倒的批評態勢外,在其他爭議方面,并未達成共識。種種爭議之下的本質問題是,業界尚未在“好律師、壞律師”的衡量標準上達成共識。
尷尬的律師定位
長期擔任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委員的欒少湖律師向《南風窗》分析,辯護律師應當明確自己的崗位在法庭上,“除了合理收取的代理費外,應當避免謀取哪怕一丁點利益,不可以再摻雜上自己的利益、想法和企圖”。
欒少湖認為,李案等案件中引起爭議的辯護律師,“都沒有很好地領會和理解辯護律師的全部職能和職責”。他分析道,脫離案件本身,試圖通過輿論辯護,來影響案件的法律適用,扭曲法律要求的做法,還有將水攪渾,使案件永遠無法達到真相的種種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據媒體報道,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協已就李案中律師的不當行為開展調查。盡管在欒少湖看來,辯護律師的角色和定位是明確無疑的,但他不贊成處分蘭和。蘭和以李家法律顧問的身份發表言論,這是一種新的現象,是一種沒有法定規范的新的法律服務形式。欒少湖認為,法律顧問應當盡謹慎義務,只對委托人發表法律意見,是否對外發布,則是委托人的權利。
此次蘭和的行為引起爭議,欒少湖將主要責任攬到律協身上,他認為在自媒體時代,律師協會應該及時細化研究新時代和新平臺上的律師行為,出臺行業規則,“行業規則也應該適用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就不應該處罰”。
行業規則不甚明了的背后,是中國律師的角色在復雜的多方認知中,一直未取得統一認識的現狀。改革開放初期,律師制度剛恢復時,《律師暫行條例》將律師定位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1996年制定的《律師法》中定義的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2007年修訂后的《律師法》中,律師則被界定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欒少湖對刑辯律師定位的解讀正是建立在新《律師法》提出的新理念之上。
定位表述從國家到社會再到服務具體的當事人,中國律師的法定“身份”越來越接近現代法治社會對律師的定位。然而這并不代表律師的定位因此就明晰了。
新《律師法》在提出新定義的同時,也規定律師要發揮三種職能,即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正義,以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作為具有公共性的一種職業,這也無可非議。但這項規定卻為各方從不同角度解讀律師定位埋下了伏筆。
2010年,“李莊案”第一季二審判決不久,司法部下發了《關于李莊違法違紀案件的通報》要求各地律師協會以李莊案為例,在律師隊伍中開展“警示教育”,加強對律師隊伍的教育、監督和管理。通報還稱,律師要“協助司法機關準確打擊犯罪”。
以往司法行政部門根據新《律師法》中律師的第三項職能“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所做出的解讀,也不過是“協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實”。既然犯罪嫌疑人不愿意出錢請律師來推動法治,那么他們更不愿意花錢請律師來幫忙司法機關“準確打擊”自己。聲勢浩大的律師“警示教育”活動隨著“李莊案”第二季的展開,也偃旗息鼓,漸漸淡出視野。
但是在律師群體中,對于律師的第一項和第二項職能的認識仍然存在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就體現在對自身職業定位的認識之上。“死磕派律師”中的大多數認為,他們應當以當事人利益為上,死磕法律程序,確保當事人的合法利益。而另外一些律師則可能更看重這個職業“維護社會正義”的屬性,力圖推進制度進步,超越個案,實現更大的公義。
這種認知上的差別,直接導致了衡量“好律師、壞律師”的不同標準。欒少湖還是堅持律師的專業主義立場,“律師可以為各種人辯護,但是律師必須清楚認識到,自己是代理人,不能用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者用委托人的政治主張,來影響依法辯護和依法死磕”。
律師治理的邏輯
上述某省律協領導向《南風窗》分析道,律師的職業準則模糊和定位混亂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律師個人,根本還在于缺少有效的律師治理機制。
律師制度雖然在“文革”結束后迅速得到恢復,但直到1993年國務院批準了《司法部關于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之后,律協才在律師治理中占據一席之地,該方案規定了“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與律師協會管理相結合”的治理體制。
但是這種“兩結合”的體制并沒能彌合業界爭議,據上述律協人士分析,機制欠缺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正在向自由化的方向蔓延”。
實際上,多項規范律師職業的機制和制度隨著運動的展開已經逐漸建立起來了。2004年,司法部出臺了律師懲戒規定,并在各地律協建立律師和律師事務所不良行為投訴制度,設立專門的律師懲戒委員會。2010年,司法部又發布了《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辦法》以及修訂后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但受制于目前體制下各方行動的隱秘邏輯,這些規則并沒有充分落實。
“兩結合”的治理體制下,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協共享對律師的處罰權,但是律協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只有進行訓誡、通報批評等軟性處罰,而涉及吊銷執業資格或其他行政處罰等真正有威懾力的處罰,只能交給司法行政部門來處理。某律師業發達城市的一名律協工作人員告訴《南風窗》,律協的地位其實非常尷尬,沒有脫離行政機關的控制。
各地律協的會長基本上都由執業律師擔任。上述市律協工作人員認為,司法行政部門在政府序列中權力較小,但是在維穩有關的問題上,經常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因此司法行政部門在這方面對律師的控制相對較嚴。例如,2006年3月,《關于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出臺,將土地征用征收、房屋拆遷、庫區移民、企業改制、環境污染以及農民工權益保障等領域定義為群體性案件高發地帶,要求代理群體性案件的律師,及時向律協及有關司法行政部門匯報。
對律協來說,一方面缺少行業充分自治的權力,另一方面在意愿上也不太愿意過多處罰律師。據上述某市律協工作人員透露,該市律協平均一年收到150到200件針對律師的投訴,最終正式受理的大概有10幾宗,而受到行業處分的則只有幾宗。他分析,律師目前在整個體制下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律協更趨向于替律師出面維權。
“兩結合”體制下的各方主體的隱秘邏輯,導致律師職業內部缺少足夠的監督和治理。上述某省律協人士評論稱:“諸多不當行為沒有制止者,沒有官方和協會的聲音,這是導致一些律師行為混亂的最大原因。”
一場官方針對部分律師群體的摸底活動正在展開,而輿論場上,中國律師的公眾形象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矛盾態勢,在這關口,律師將走向“分而治之”,進入更激烈的紛爭狀態,還是樹立行業共識,建立有效的行業自凈機制?這將取決于多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