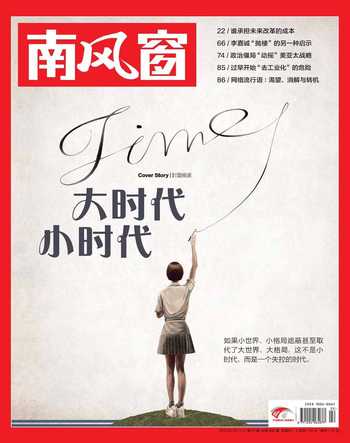被“過度消費”的阿拉法特
歐陽晨雨

多年來,對于阿拉法特之死,盡管“死因”判斷并不一致,人們還是普遍接受了阿翁“血液系統紊亂而死”的現實。然而,2012年7月,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公布了與之合作的瑞士洛桑大學輻射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出根據從阿拉法特遺孀蘇哈那里獲得的阿翁隨身衣物的取樣結果,在阿拉法特私人用品上的釙的含量要比普通狀況高得多,大約有60%至80%并非來自自然。此舉讓本已沉寂的阿拉法特 “死因”之爭驟然升級。當年11月, 阿拉法特靈柩被打開,俄羅斯、法國和瑞士三國專家取出阿拉法特大約60個遺骨樣本,并提取樣品以備調查死因。
一年之后,尸檢結果尚未公布,部分媒體卻先躁動不安,有一種要將陰謀論進行到底的勢頭。的確,9年前阿翁入院急救不到兩周即駕鶴西去,給人一種事發突然的感覺(可對比其對手沙龍昏迷7年后,仍能靠營養液維持生命)。但存在矛盾的事實本身也許并不能僅僅靠科學得到澄清,政治考量和操作仍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巴以特定的對抗格局下,尸骨早寒的阿翁被有關方面抬出來“過度消費”,不僅是其個人命運的凄涼寫照,也是地區僵局懸而待解的諷刺性象征。
“烏龍報道”
今年8月有消息傳出,瑞士方面可能在9月中旬將阿拉法特的尸檢結果移交巴方,但逾期一個月,阿翁尸檢報告仍沒動靜。10月12日,半島電視臺網站轉載了英國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網站當日刊登的一篇論文。該論文并未提及任何“尸檢”可能提出的新證據,只是針對去年2月由洛桑大學輻射物理研究所對阿拉法特遺物首次分析后的病理報告做了一次同行驗證評估,其結論也并非認定阿翁死于中毒,而是說取樣結果支持遭釙輻射致死的“可能性”,而阿翁之所以未出現被輻射后的典型癥狀,如骨髓抑制、頭發大量掉落,可能也與個人體質有關。
但在中東和中國一些媒體的報道中,瑞士科學家去年初從阿拉法特“衣物和牙刷上”殘留的血液、尿液、唾液痕跡中檢出大量釙210,被“錯會”成從后來的尸檢中發現了這些高放射性元素。而一些媒體在引用《柳葉刀》論文時,將“代表可能性的表達”轉變成了肯定的語氣。于是,所謂“《柳葉刀》證實阿拉法特被毒殺”的新聞滿天飛。
10月13日,巴勒斯坦官員對新華社記者否認阿翁被證實死于中毒的說法,稱巴方尚未接到正式的尸檢結果。而阿翁死因調查委員會主席陶菲克·提拉維也表示,正式的尸檢結果目前處于保密階段,還沒有遞交給巴方。提拉維也否認巴方受到內部或者國際壓力推遲公布消息。洛桑大學新聞發言人14日表示,目前尚不知何時會得出結論,報告若出爐,會首先遞交給阿拉法特遺孀蘇哈。
可以說,這是一起因媒體不熟悉內情而斷章取義的“報道烏龍”事件。不過其背后也存在值得關注的政治動因。對于阿翁尸檢結果推遲公布(部分因素在于法國醫生調查研究尚未結束,三方會審尚未啟動),就有巴勒斯坦官員說,可能是為了防止尸檢結果對巴以和談重啟造成沖擊。此外,考慮到半島臺的背景及立場,雖說炒冷飯,不難看出其對于“被毒殺”結論的渴望。盡管就算阿翁“被毒殺”,人們也無法在短期內獲知誰是下毒者,就像敘利亞沙林毒氣事件搞不清幕后黑手一樣,但在這樣的模糊語境中,以色列必將更多地遭受國際輿論的壓力。
“國際驗尸”
2004年10月29日,羸弱不堪的阿拉法特終于獲準,離開了被以軍重兵圍困的拉姆安拉官邸。被軟禁近3年后,罹患重病的他由一架約旦直升機緊急護送到法國貝爾西軍醫院接受治療。當年11月11日,阿翁搶救無效去世,享年70歲。
對此,以色列否認有任何過錯,請求巴勒斯坦領導層公布阿翁所有病歷。而2005年對阿翁病歷進行的首次獨立評估顯示,他死于出血失調導致的中風,而出血失調則是由一未知感染引起的。
去年7月,卡塔爾王室背景的半島電視臺在經過9個月暗中運作后,突然公布瑞士洛桑大學輻射物理研究所有關阿翁可能死于釙中毒的分析報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法國法院等聞訊后迅速介入。隨后,在阿拉法特遺孀蘇哈的請求下,位于拉姆安拉市的阿拉法特墓穴被打開。
從伊斯蘭習俗來看,將死者從地下挖出“驗尸”,是一種不夠恭敬的行為。是以,直到最后時刻,阿拉法特的妹妹仍在極力反對 “開棺驗尸”。然而,公開 “驗尸”不僅是確認阿拉法特是否非正常死亡的唯一途徑,還可以微妙地利用國際輿論的壓力和時間差,實現巴勒斯坦當局的階段性目標。
2012年11月29日,亦即阿拉法特“被開棺”兩天后,第67屆聯合國大會以138票贊成、9票反對、41票棄權通過決議,把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地位由“觀察員實體”提升為“觀察員國”。雖然這種國際地位還達不到安理會討論正式成員國地位的要求,但已經可以憑借日后的尸檢結果,請求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介入阿翁之死一案。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事件確實可以對巴勒斯坦的“入聯”事業做出“貢獻”。
由于處于輿論下風,美國和以色列對阿翁被開棺驗尸一事不動聲色。真正積極參與其中的,是法國、俄羅斯和瑞士。法國因為阿翁在貝爾西軍醫院去世時并未查出其具體死因,所以在“投毒論”驟起后,有責任對巴方做個交代。2012年8月,蘇哈和女兒扎赫娃向法國楠泰爾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對阿翁死因展開司法調查。法方迅速反應,派出3名法官介入調查。
俄羅斯積極參與,是因為與巴勒斯坦主流派有著特殊關系,阿巴斯曾多次訪俄尋求支持。而作為最先拿出阿翁衣物檢測報告的第三方,瑞士方面的介入,更讓尸檢活動給世界留下一個“客觀”的印象。
當然,最不可忽略的國際力量,還是半島電視臺的東家—卡塔爾。在敘利亞政府因哈馬斯支持“倒阿薩德”而與之決裂后,2012年10月卡塔爾元首歷史性地訪問加沙,并給予哈馬斯大量援助。有分析人士認為,卡塔爾是開棺驗尸的幕后指使者,其出發點是在中東地區證明其強國地位,同時向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發出警告。
“燙手山芋”
2012年7月,巴勒斯坦阿拉法特死因調查委員會就曾公開表示,根據已有材料和臨床癥狀推斷,阿翁系中毒身亡。不過,也有質疑之聲,在一些生化核專家眼中,“釙中毒”之說從理論上并不可行。
由于釙元素的半衰期僅138天,大約2年半后其放射性含量就基本消失了。可離奇的是,現在居然還能在他的遺物中發現如此高劑量。再者,半島臺介紹說釙210毒性為同劑量氰化物的2.5億倍,那么,曾多次探望阿翁并保留其遺物的蘇哈,又是如何避免受到傷害的?所以,人們不無懷疑,這些“新鮮”的釙可能是在阿翁逝世多年后重新放置的。
即便是《柳葉刀》從頗為權威的角度論證,阿翁很可能系釙中毒身亡,也只是去年洛桑大學分析報告的衍生物,且存在諸多疑點。例如阿翁臨終癥狀(骨髓良好,并未脫發),與釙中毒患者的一般癥狀并不完全相符。
對于許多致力推動“驗尸”的力量來說,目的是將矛頭對準以色列這個“兇手”。然而,以方主導“謀殺”的可能性的確不高。一頭早已褪去尖牙利爪不再風光的衰老雄獅,是不會激發獵手多大興趣的。
1990年代初,當阿拉法特表達了對薩達姆侵略科威特的支持后,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就逐漸邊緣化。2004年時的阿拉法特,被以軍重重圍困在拉姆安拉,與外界基本隔絕,已無法發揮政治作用。盡管時任以色列總理沙龍不太情愿,畢竟也向時任美國總統布什承諾過,不殺害阿拉法特。
就算阿拉法特死于他人毒殺,也不能一舉鎖定以色列。阿翁領導下的巴解組織,其他有野心者未必不會劍走偏鋒;哈馬斯則和他關系不睦,未必不會有激進者使出辣手。況且,以色列即便被“判定”為“兇手”,對于巴以局勢也只是火上添油。
長期以來,巴勒斯坦經濟嚴重依賴對以色列出口,巴方的失業率徘徊在26%左右,財政赤字日趨嚴重。去年,對于巴方謀求“聯合國席位”之舉,美國和以色列采取了有力的制裁舉措,如以方暫停向巴方移交重要的代征稅款。
今年7月,在美國斡旋下,巴以開始恢復對話,為重啟巴以和談做準備。中東問題四方委員會呼吁巴以在9個月內達成和平協議。一旦巴以因阿翁之死撕破臉面,這些工作將前功盡棄,歷盡戰火劫波、正在艱難爬升的巴勒斯坦經濟將不堪重負,只不過是便宜了那些希望海牙國際刑庭介入此事的區外勢力。所以,巴勒斯坦當局現在不愿為風言風語所動,免得為別的勢力火中取栗。
“翻開新頁”
阿拉法特之死,留下了一個難以彌合的真空地帶,在巴勒斯坦政權內部,權力爭斗一度非常激烈。遺老派與新領導層之間的斗爭結果,是遺老派中巴前安全高官穆罕默德·達赫蘭和阿拉法特經濟顧問穆罕默德·拉希德等被驅逐出權力中心。
2006年,法塔赫與哈馬斯曾組建聯合政府,但最終以哈馬斯在2007年武力奪取加沙地帶控制權告終。作為巴勒斯坦的領導人,阿巴斯近年來努力推動巴內部團結,宣布改組內閣后多次呼吁新政府要包括哈馬斯成員,并于2011年實現了法塔赫與哈馬斯的初步和解。而主持“尸檢”、尋找“真兇”,也讓法塔赫與哈馬斯再度走到一起。但顯然,在哈馬斯看來,無論是之前的庫賴,還是今天的阿巴斯,都無法再現昔日阿拉法特的權威和力量。
其實,就算阿拉法特得以重生,也不復當年威望。2002年8月,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阿海羅估計,阿拉法特個人財產超過13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審計報告指出,阿拉法特曾在1995到2002年間,將9億美元公共基金轉移到本人賬戶內。2003年美國雜志《福布斯》估計阿翁個人財產至少3億美元,排名為國家領導人中第六位。
之前,有媒體報道,阿拉法特遺孀蘇哈拿到法國公民身份,長期在巴黎過著奢靡的定居生活。她在巴黎五星級飯店住了一年多,整層樓每晚租金高達8700英鎊。由于面臨逃稅等指控,蘇哈在突尼斯的生活也陷入了窘境,甚至公民權都被剝奪。因此,有人指出,當初在法國強烈反對“驗毒”的蘇哈,而今強烈要求“尸檢”,其真實目的不過是借阿拉法特的殘存聲譽,為自己謀取額外的好處。
正因如此,盡管在一些巴勒斯坦人眼中,阿拉法特仍是民族靈魂和象征,每年11月11日,巴勒斯坦民眾都會自發組織集會,向這位老戰士致敬,但作為一個事實,屬于阿拉法特的時代早已遠去。
眼下,圍繞“釙中毒”風波,在鐵與血交織的巴以沖突中,一場集體“消費”阿拉法特的國際角斗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