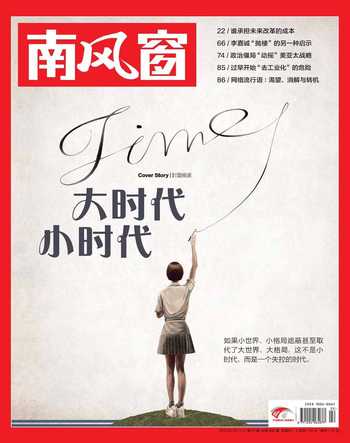過早開始“去工業化”的危險
丹尼·羅德里克
老生常談的工業化是多數發達經濟體取得今天成就的必由之路。從傳統手工業及公會系統的灰燼中浴火重生的紡織、鋼鐵、汽車等制造業的長足進步,推動了農業社會向著城市社會的轉型。農民轉變為工廠工人,這個過程不僅伴隨著前所未有的生產力進步,同時也造就了社會及政治組織的大規模革命。工人運動造就了大眾政治,并最終帶來了政治民主制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服務取代了制造的地位。在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制造業的就業比率在一戰前約為45%,之后下降到只有30%多,這種狀況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之后制造業的就業率開始急劇降低。制造業目前僅占英國就業總量不到10%的份額。其他富裕經濟體也都經歷了類似的工業化和去工業化進程。美國制造業在19世紀初就業率不到3%。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25%~27%后,開始去工業化進程,近年來制造業就業率不到10%。
瑞典的制造業就業率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33%的頂峰,之后下降到略高于10%。即使在被視為發達世界制造業最強國的德國,制造業就業率在1970年左右達到近40%的峰值,之后就一直穩步下降。正如哈佛大學羅伯特·勞倫斯所說的那樣,去工業化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且早于不久前的經濟全球化浪潮。
只有東亞地區的少數發展中國家效仿這種模式取得了成功。多虧有了出口市場,韓國經歷了異常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其制造業的就業份額從20世紀50年代的一位數上升到1989年的28%(之后就下降了10個百分點左右),韓國在30年時間里完成了早期工業化國家一個世紀或者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轉型。
不過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模式已經有很大不同。不僅工業化本身進展緩慢,而且去工業化的開始也比發達國家早得多。
比如過去10年來發展勢頭較好的兩大新興經濟體巴西和印度。巴西的制造業就業比率從1950年到1980年幾乎沒有變化,僅僅從12%上升到15%。20世紀80年代后期,巴西開始去工業化,該國近來的經濟增長幾乎沒怎么阻止或逆轉去工業化進程。印度的情況更令人意想不到:制造業就業于2002年僅僅達到微不足道的13%,之后開始進入下降通道。
發展中國家為何提早出現去工業化發展軌跡,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一個明顯的因素或許是全球化和經濟開放,因此導致巴西印度等國很難與東亞超級制造巨星展開競爭。但全球競爭并不能成為主要原因。事實上,出人意料的是就連東亞國家也提早進入到去工業化進程。以中國為例。身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人們意外地發現其制造業就業率不僅明顯偏低,而且一段時間來一直在下降。雖然中國的統計數據并不可靠,但事實是制造業就業率于20世紀90年代達到峰值的15%,之后就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
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當然絕大部分勞動力依然留在農村。但絕大多數農民工現在是在服務業而不是制造業工作。同樣,越南和柬埔寨等新一代制造出口國根本不可能達到英、德等早期工業化國家曾經達到過的工業化水平。
這種現象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在低得多的收入水平開始向服務經濟轉型。當美國、英國、德國和瑞典開始去工業化時,它們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9000到1.1萬美元(按1990年的價格計算)。而反觀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只達到其中一小部分的時候,它們的制造業就開始萎縮:巴西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開始出現去工業化進程,中國的去工業化開始于3000美元,印度則是2000美元。
過早去工業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后果還有待全面論證。在經濟領域,很顯然,過早去工業化會阻礙經濟增長,導致發展中國家遲遲無法與發達經濟體會合。制造業是我所謂的“電梯行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有向前沿逼近的趨向,哪怕該經濟體的政策、制度和地理狀況共同遏制了其他領域的進步。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除極少數自然資源豐富的小國之外,歷史上的快速增長大都與工業化脫不了干系。工業化空間收窄無疑將影響到未來的增長。
社會政治后果不那么容易預測,但卻可能同樣重要。持續民主政體是持續工業化的產物: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紀律嚴明的政黨和圍繞左右中軸展開的政治競爭。
勞資雙方的斗爭史造就了妥協與節制的習慣—制造車間是上述斗爭的主要場所。鑒于去工業化進程的提早出現,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在實現民主和善政的過程中另外開辟一條未知的、也可能更加崎嶇的道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作者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社會科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