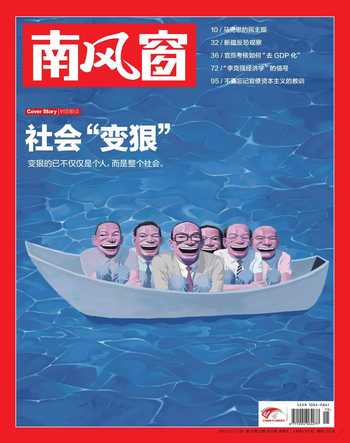民間劇場(chǎng)的草臺(tái)精神
莊稼昀



自2005年創(chuàng)建以來(lái),草臺(tái)班,這個(gè)以上海作為大本營(yíng)的民間劇場(chǎng)團(tuán)體已經(jīng)集體創(chuàng)作并演出了《38線游戲》(2005年)、《狂人故事》(2006年)、《蹲》(2008年)、《魯迅二零零八》(2008年)、《小社會(huì)》(第一、二卷)(2009~2010年)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今年上半年,又接連推出《翹臀時(shí)代》(集體創(chuàng)作/導(dǎo)演:侯晴暉)、《不安的石頭》(編劇/導(dǎo)演:趙川)、《變形花園》(編劇/導(dǎo)演:吳夢(mèng))、《我把春天喜歡過(guò)了》 (編劇/導(dǎo)演:庾凱、瘋子)等幾部更加鼓勵(lì)從個(gè)人創(chuàng)作出發(fā)的新劇。
草臺(tái)班由趙川主持創(chuàng)作,吸收了如瘋子、庾凱、侯晴暉、劉念、吳夢(mèng)等一批所謂的“非科班”出身,把大部分業(yè)余時(shí)間投入劇場(chǎng)(特別是社會(huì)劇場(chǎng)),且不計(jì)報(bào)酬的骨干成員。除了劇場(chǎng)部分,草臺(tái)班也舉辦表演工作坊、討論會(huì)、文化站、巡回演出或外出拉練等活動(dòng),將這個(gè)“自謙”僅僅做非盈利、平民戲劇的業(yè)余草臺(tái)班子逐漸發(fā)展為中國(guó)民間劇場(chǎng)中一塊精彩且難得的公共平臺(tái)。
初識(shí)趙川很偶然。2007年夏,我們都在北京九劇場(chǎng)門口跟著櫻井大造的團(tuán)隊(duì)為即將上演的《變幻痂殼城》搭帳篷。2012年再見(jiàn)時(shí),我說(shuō)怎么依稀記得當(dāng)年你和草臺(tái)班開(kāi)了輛大公共來(lái)北京“串聯(lián)”的,他說(shuō)這就是草臺(tái)班給人的質(zhì)感吧:流動(dòng)的、臨時(shí)的、簡(jiǎn)樸的,還時(shí)不時(shí)自?shī)首詷?lè)一把。今年初夏再見(jiàn),他又笑道,“如果你跟我討論專業(yè) (劇場(chǎng)),我不懂;如果你跟我討論業(yè)余,我在搞業(yè)余上比任何人都專業(yè)。”
逼 問(wèn)
趙川說(shuō),“草臺(tái)班堅(jiān)持做的事情實(shí)在不是件日常的事情。我們?cè)谫Y本驅(qū)動(dòng)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里好像不是一個(gè)自然的實(shí)體。”趙川曾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逼問(wèn)劇場(chǎng)》一文,倡導(dǎo)以“逼問(wèn)”的方式創(chuàng)作民間劇場(chǎng),進(jìn)而創(chuàng)造民間空間。或許我們可從這“逼問(wèn)”二字略窺“不日常、不自然”的草臺(tái)精神之一二。
首先,逼問(wèn)劇場(chǎng)產(chǎn)生并發(fā)展于既非職業(yè)(如國(guó)有院團(tuán))也非商業(yè)的社會(huì)空間中。它向社會(huì)全體成員開(kāi)放,就草臺(tái)班而言則吸收了“三六九等”上海學(xué)生白領(lǐng)準(zhǔn)白領(lǐng),也吸納了(有限的)社會(huì)資源—比如王景國(guó)老師常年為上海非職業(yè)劇社免費(fèi)提供的下河迷倉(cāng)劇場(chǎng)空間。就這個(gè)無(wú)固定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無(wú)固定排演地點(diǎn)、在村臺(tái)閭弄中尋摸容身之地、知音之交的草臺(tái)班子而言,也許“不自然”的反而是它的那個(gè)正規(guī)的、占據(jù)大量資源卻無(wú)所作為的對(duì)立面。或者說(shuō),草臺(tái)班之存在及其主體性也正是在逼問(wèn)中國(guó)當(dāng)代民間劇場(chǎng)和民間戲劇不健全也不健康的當(dāng)下生態(tài),更不必說(shuō)它以逼問(wèn)立場(chǎng)所做出的社會(huì)批判和文化改造上的種種努力。
其次,正如《小社會(huì)》演出前那段開(kāi)場(chǎng)白—“看戲過(guò)程中,歡迎您打開(kāi)各種通訊工具,歡迎您小聲或大聲與外界通話,在我們的社會(huì)劇場(chǎng)中,歡迎您與生活保持密切聯(lián)系”—草臺(tái)班有意強(qiáng)化“劇”(戲劇)之小環(huán)境與“場(chǎng)”(狹義到演出場(chǎng)地、廣義到社會(huì)場(chǎng)域)之大環(huán)境間的互動(dòng)與摩擦,將轉(zhuǎn)型期國(guó)家與市場(chǎng)既依存又對(duì)立卻將社會(huì)浸泡、壓制于(政治和資本)權(quán)力之中所出現(xiàn)的 “不日常、不自然”置于草臺(tái)之上,解剖分析。或許草臺(tái)班處理的某些社會(huì)問(wèn)題過(guò)于龐大抽象,嫁接在舶來(lái)理論之上,或如同《小社會(huì)》中時(shí)而挺身而出、炫技般地用幾種語(yǔ)言朗讀《共產(chǎn)黨宣言》片斷的那位來(lái)自加州大學(xué)的教授 “老康”一樣“隔空喊話”。然而,草臺(tái)班執(zhí)著于縫合歷史、現(xiàn)實(shí)與再現(xiàn)間的斷裂,在劇場(chǎng)時(shí)空間中建立演員和觀眾對(duì)現(xiàn)實(shí)處境的同步思考,也用它那粗糙、簡(jiǎn)陋、“不夠漂亮”的劇場(chǎng)去逼問(wèn)那些由搞笑懸疑穿越多媒體的商業(yè)劇“培養(yǎng)”起來(lái)的年輕都市劇場(chǎng)觀眾,也逼問(wèn)他們的娛樂(lè)消費(fèi)、情感消費(fèi)和文化消費(fèi)習(xí)慣。
再次,“逼問(wèn)”在趙川的論述中是自省與自我挖掘,是摘下假面和逼近真相,是建立在布萊希特反叛亞里士多德模仿觀和敘事論基礎(chǔ)之上進(jìn)一步揭露再現(xiàn)幻象、下放劇場(chǎng)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實(shí)驗(yàn)。草臺(tái)班的團(tuán)隊(duì)內(nèi)部有諸多差異:如多元的身份(年齡、職業(yè)、性別、出生地、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等),加入團(tuán)隊(duì)的不同初衷(進(jìn)入社會(huì)批評(píng)的場(chǎng)域、沿襲校園戲劇的傳統(tǒng)、尋找滬上社交平臺(tái)等等),以及這種種差異所引發(fā)的成員們觀察事物、思考問(wèn)題的角度和方法上的區(qū)別。趙川和草臺(tái)班堅(jiān)持劇場(chǎng)方式,正是因?yàn)榕c其他媒體不同,劇場(chǎng)不僅為參與者提供了多樣化并多變化的交流方式,充分釋放觀/演者的生活能量和生存體驗(yàn),也常常期待不可預(yù)測(cè)的“游戲”結(jié)果。無(wú)論從實(shí)際操作層面還是美學(xué)層面,逼問(wèn)劇場(chǎng)的對(duì)象是將社會(huì)規(guī)則和倫理秩序內(nèi)在化后的“自我”,它暴露了普通人“日常的、自然的”規(guī)范展演(performance),也賦予他們?cè)趧?chǎng)中創(chuàng)造“非日常、非自然”的機(jī)會(huì)。
尋 找
我問(wèn)趙川,現(xiàn)在草臺(tái)班所面對(duì)最大的問(wèn)題是什么。“我們?nèi)鄙偻悾彼摽诙觯拔覀兒孟癯闪斯伦C。”
交談中,趙川簡(jiǎn)單梳理了對(duì)草臺(tái)班早期發(fā)展頗為重要的亞洲民眾劇場(chǎng):菲律賓教育劇場(chǎng)、在香港推行民眾戲劇的莫昭如、鐘喬的臺(tái)灣差事劇團(tuán)、“東亞民眾戲劇網(wǎng)絡(luò)”(EAPTN)、“亞洲的吶喊”和“大風(fēng)吹”等跨亞洲幾個(gè)地區(qū)的劇場(chǎng)集結(jié)匯演。而草臺(tái)班的前身也正是受韓國(guó)民眾戲劇工作者張笑翼邀請(qǐng),為韓國(guó)2005年光州亞洲廣場(chǎng)戲劇節(jié) (the 2005 Gwangju Asian Madang)創(chuàng)作演出《38線游戲》的那個(gè)團(tuán)隊(duì)。
亞洲民眾劇場(chǎng)產(chǎn)生于上世紀(jì)60年代,源于第三世界革命想象,曾以巴西戲劇工作者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的《被壓迫者的劇場(chǎng)》作為最主要的理論基礎(chǔ)和操作范本。隨著80年代末期世界社會(huì)主義運(yùn)動(dòng)進(jìn)入低潮,一部分民眾劇場(chǎng)人將訴諸意識(shí)形態(tài)變革的革命劇場(chǎng)轉(zhuǎn)向更具公益性服務(wù)性并貼近市民生活的社區(qū)劇場(chǎng),也引進(jìn)美國(guó)戲劇人喬納森·福克斯(Jonathan Fox)“一人一故事” (Playback Theatre)的互動(dòng)即興表演方式。(可以說(shuō),國(guó)內(nèi)如廣州木棉劇團(tuán)、同聲同戲劇團(tuán)和深圳牙牙劇社等幾個(gè)民間戲劇團(tuán)體的發(fā)展都和“一人一故事”的引進(jìn)密不可分。)沿著這個(gè)脈絡(luò)發(fā)展了一段,草臺(tái)班卻意識(shí)到了自身與東亞民眾劇場(chǎng)無(wú)論在歷史經(jīng)驗(yàn)還是操作層面上的脫節(jié):一則這些在中國(guó)大陸周邊國(guó)家與地區(qū)懷著左翼理想和擔(dān)當(dāng)?shù)拿癖妱?chǎng)人所反抗的“壓迫”和大陸民間劇場(chǎng)人面對(duì)的實(shí)際“壓迫”大相徑庭;二則每次戲劇工作坊部分完成后,東亞民眾劇場(chǎng)“導(dǎo)師”們的技術(shù)傳授和輔導(dǎo)活動(dòng)也隨即結(jié)束,這意味著東亞民眾劇場(chǎng)運(yùn)動(dòng)與大陸民間劇場(chǎng)本土資源和在地經(jīng)驗(yàn)的整合相當(dāng)有限。
另一個(gè)對(duì)草臺(tái)班有重要影響的則是自1997年發(fā)起的致力于通過(guò)劇場(chǎng)展演和討論推動(dòng)亞洲文化交流的非贏利性項(xiàng)目—“亞洲相遇”(Asia meets Asia)。在幾次小型戲劇展演后,“亞洲相遇”曾在2005年暫停,又于2008年卷土重來(lái),而這里就需要提到《魯迅二零零八》。2008年,在水泥毛坯倉(cāng)庫(kù)式的上海東大名創(chuàng)庫(kù)中,趙川與來(lái)自日本的大橋宏、臺(tái)灣的王墨林、香港的湯時(shí)康共同創(chuàng)作的《魯迅二零零八》,探討魯迅作品對(duì)東亞社會(huì)和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影響。魯迅先生在《社戲》中描述的“最惹眼的屹立在莊外臨河的”草臺(tái)鄉(xiāng)土意象全然消失;在廢墟般的空間中,盲人、瘋子、小兒麻痹癥患者和那些《狂人日記》中隨時(shí)要吃人又要警惕吃人之人的人,在建筑垃圾揚(yáng)起的嗆鼻塵土中掙扎與嘶咬,在翻滾中發(fā)出狂笑與悲泣,在穿過(guò)滑輪的繩子兩端捆綁與拉扯。魯迅的文本就支離破碎地夾雜在劇場(chǎng)的聲嘶力竭中,無(wú)論是《希望》中的“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沒(méi)有真的暗夜”,來(lái)自《新的世故》中那句耳熟能詳?shù)摹跋闰?qū)者本是容易變成絆腳石的”, 《墓碣文》中“于一切眼中看見(jiàn)無(wú)所有;于無(wú)所希望中得救”,還是那些用各種語(yǔ)言和方式表達(dá)出來(lái)的字句,都在作品中轉(zhuǎn)換為東亞劇場(chǎng)人對(duì)魯迅文本充滿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觸覺(jué)、甚至痛覺(jué)的經(jīng)驗(yàn)和體驗(yàn)。通過(guò) 《魯迅二零零八》,“亞洲相遇”也摸索著在同一主題下,跨地區(qū)、跨語(yǔ)言、跨語(yǔ)境的集體工作方法。在接下來(lái)幾年中,這個(gè)團(tuán)隊(duì)繼續(xù)“夢(mèng)難承”系列的實(shí)踐,先后創(chuàng)作《夢(mèng)難承4:失家園》(2009年)、《夢(mèng)難承5:回歸》 (2010年)、 《夢(mèng)難承6:希望》(2011年)。
也就是在與“亞洲相遇”劇場(chǎng)人的碰撞中,趙川進(jìn)一步確定了身體在劇場(chǎng)中表達(dá)的重要性。除了剛才提到的 《魯迅二零零八》中充滿暴力的身體意象,在作品《蹲》中,主人公“蹲”與“半蹲”在支在舞臺(tái)中央的腳手架上支撐著一個(gè)精力被耗費(fèi)、尊嚴(yán)被挑釁的“蹲姿”,尷尬而倔強(qiáng)地用不識(shí)時(shí)務(wù)的身體與現(xiàn)實(shí)對(duì)話和交鋒。《小社會(huì)》中則展現(xiàn)了一個(gè)個(gè)在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買進(jìn)賣出的卑微的身體:有裹在麻袋中被越揀越多的廢品擠壓得彎不下腰的拾荒者的身體、有站在小拉桿箱上感嘆著要在這個(gè)最好的時(shí)代中積累資本的打工者那顫悠慌張的身體,也有在強(qiáng)光照射下支吾著“我愿罰”并倉(cāng)皇地向角落滾爬去的性工作者的身體。草臺(tái)班的劇場(chǎng)中正要挖掘和呈現(xiàn)這些反映著社會(huì)權(quán)力關(guān)系、也嵌刻著生命經(jīng)驗(yàn)的身體,也相信只有這種身體所占有的物理空間和所作出的社會(huì)表達(dá)才能構(gòu)建劇場(chǎng)這樣的公共空間,并把這個(gè)空間延伸開(kāi)去。相信,草臺(tái)班通過(guò)或拉練或巡演的方式,為的正是把他們具有劇場(chǎng)能量的身體帶向四方,由此尋求同道中人—所有那些具有身體能量的劇場(chǎng)和劇場(chǎng)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