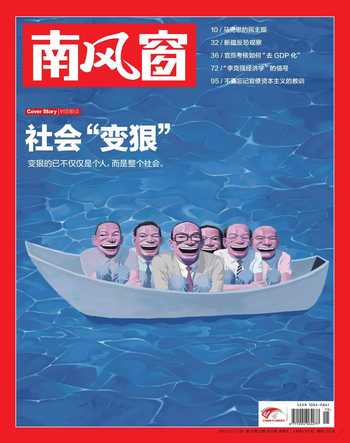思想改造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的社會地位,一直呈現出一種“邊緣化”的趨勢。傳統中國是由士農工商組成的四民社會,讀書人通過科舉制度參與政治,成為國家官僚體制的核心力量。士大夫在國家層面代表道統,與君主共治天下,在社會層面成為官府和百姓之間的聯絡紐帶。然而,晚清以降科舉制度廢除,讀書人與國家失去了建制性的聯系,士大夫轉變成現代的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上自由流動的資源。尤其是四民社會瓦解,工商階層和軍人集團的崛起,知識分子更是失去了社會中心的地位。他們懷著傳統士大夫的夢想,力圖通過言論和知識的力量,重返社會中心。這一努力在國共內戰之際達到頂峰。但是好景不長,在此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知識分子被徹底邊緣化。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最能說明問題的例證便是思想改造運動。在政治上,這些黨外人士被打入另冊,成為暫時有地位但毫無實際權力的一群人。后來更是既無地位又無權力,成為黨政官員和學生眼中一無是處的“老九”。在學術上,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專業和學術,被當成過時的無用知識遭到徹底的清算。總之,在時代的語境之下,他們是被主流政治體制排斥的另類,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言人。正如陳徒手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中所揭示的那樣,知識分子必須徹底否定自己,進行脫胎換骨式的靈魂改造。
思想改造首先是對知識分子地位的挑戰。比如史學泰斗陳垣,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享受著政治光環,卻處于被邊緣化的真空地帶,是沒有任何實權的光桿司令。甚至學生慕名請他題詞,他也要考慮再三,請校黨委書記看題詞是否妥當后再題寫。傅鷹作為石油學院的非黨系主任,沒有過問系里人事的權力,甚至名下研究生的研究題目也是由系里確定,對導師保密。馮友蘭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經常在課后被學生圍堵在教室里進行自我檢討。他為指導學生開辟一個教研室,學生嫌麻煩,要求他親自到宿舍指導。馮友蘭到學生宿舍后,卻又遭到學生的反問和訓斥。
其次是對主流知識和學術的挑戰。馬寅初是中國經濟學的權威,卻被組織上評價道:“馬寅初過去是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真才實學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后來經過一番摸底,黨組織認為馬寅初原來并不可怕,只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知識少得可憐的人。康生對游國恩、王瑤的評價是:“那些人沒什么實學,都是搞版本的,實際不過是文字游戲。”對馮友蘭、張岱年的評價是:“馮友蘭的哲學,說什么抽象的意義,實際上他的哲學并不是哲學,說好一點是語言學,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張岱年去年寫荀子的哲學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是一個社會學的范疇,但從思想的角度講,似乎是反智主義發展到極點的表現。中國古代思想中,道家法家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反智論,儒家被法家化以后,三家思想匯流,反智成為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近代以后,激進主義思潮狂飆突進,一切舊的東西都受到質疑,過去的優秀文化成果多半被當成 “封建殘余”打翻在地。尤其是邊緣人和工農階層崛起之后,相信“知識越多越反動”,將矛頭對準智力,對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其后的“文革”將知識分子徹底打倒,其結果便是一個國家民族元氣的喪失,創造力被徹底扼殺,智慧被斷送。正如本書題目《故國人民有所思》所揭示的那樣,這種反智主義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