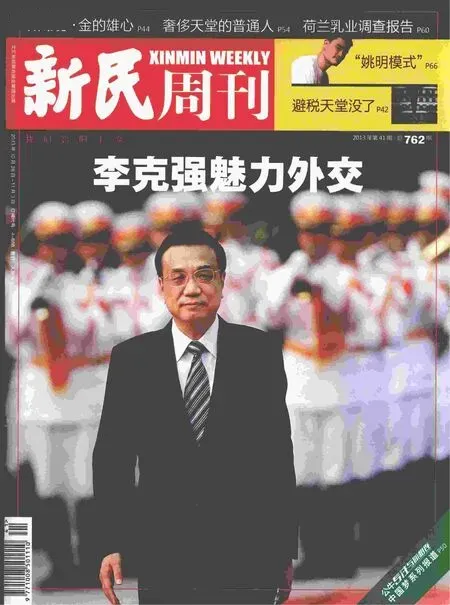編與讀
《教育真能快樂嗎》
(2013年第40期)
對于我們的應試教育,特別是高考制度,我們總是有著一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因為高考制度,讓孩子很累,讓家長很累,所以對其抱怨;另一方面我們又怕沒有了這種制度,那些普通孩子相對于“官二代”、“富二代”可能會失去更多公平的機會。
究其原因,我個人覺得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壓力太大了。我們的教育就是要你不斷進步,一天比一天好,超過同齡人,尤其超過爸爸媽媽朋友的孩子,為滿足自己的一些滿足欲,而讓孩子辛苦地學習,有的時候甚至感覺有點罪惡。 上海讀者 陸建國
《誰來填補養老金缺口》
(2013年第38期)
說到養老就繞不開農民養老問題,數量龐大的農民養老同樣面臨養老金缺口的問題。如何填補農民養老金缺口,當引起高度重視。對于這一問題,我的建議是,在農村推行“以田養老”。近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其中有關“以房養老”內容引發輿論關注。然而,即便“以房養老”得以推行,也與農民無關。由于缺乏清晰的產權界定,農民的房子哪怕建造得再豪華,也很難作為“以房養老”的“抵押物”。
中國面臨的最大養老問題,是農民養老(包括農民工)。雖然實行了新農保政策,但有限的養老金近乎無。就說我自己,繳費滿15年后,每月能拿的養老金只有200多元,與公務員等真是天壤之別。考慮到生活成本,按照多繳多得的原則,城市人養老金比農民高一些無可厚非,但這個差距應該控制在合理范疇內。
相比“以房養老”,“以田養老”對于農民來說,更具現實意義。當農民年老不能耕種后,可以將土地轉給他人繼續利用,通過租金來獲取收益,作為養老錢;農民也可以將承包地質押給銀行,從而獲得養老資金。推行“以田養老”,基于三點現實:一是只要田地不被征收,農民對其便擁有足夠的財產權;二是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農民人數的減少速度快于農地的減少速度,農民人均占有田地的面積增加,從而使土地收益增加;三是“以田養老”是最大程度配置市場資源,并不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
“以田養老”需要頂層制度設計和創新,需要完善法律予以保障。實際上,“以田養老”的雛形已經在農村出現,譬如我的田地就流轉給了種田大戶,我每年能夠拿到4000元。如果我的田地面積再多一些,租金標準再高一些,“以田養老”就不是夢。
安徽 孫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