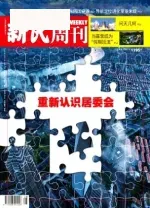新加坡是面鏡子
江迅
早些日子,就看過《到了新加坡才知道》的微博,據說流傳頗廣,筆者略摘一二:
到了新加坡才知道——8加3是要用計算器的;嚼口香糖是會被罰款的;年薪20萬(折算成人民幣)是算底層的;公交、地鐵上是不準喝水的;說話是很小聲的,大聲說話是要被投訴的;這里的人最少會用三種語言,但沒有一種語言是說得好的;說一句話,是沒辦法用一種語言講完的;他們干什么事情都要說謝謝的;路邊的椰子芒果是沒有人敢摘的;家庭瑣事政府要管的,鹽吃多少是政府規定的;新加坡人沒有紅綠燈是不會過馬路的……
這些說法,準確與否,暫不評說。在中國大陸,普通百姓對新加坡大多是顯得好奇而知之不多的。盡管早就有聞,中國不少學者傾向于新加坡的改革模式。與新加坡相距2600公里的香港,卻時不時會掀起新一陣“新加坡話題”,最新的一次,起因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上談新施政方略,其中有一重點就是要協助低收入家庭置業買樓,確保每個有工作的家庭都買得起一間組屋。
簡約而言,與香港一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政府拋出新政:改革資助房屋政策,令國民只需以4年工資便可擁有物業,以家庭為單位,月入1000坡元(約6000港元),可通過津貼計劃,買到新建1房1廳組屋;月入2000坡元,可買2房1廳組屋。買家只需動用公積金,在25年內付清所有房貸,其后部分月收入再存作退休養老。其實,新加坡置業率高達95%,這次提高置業津貼,就是要讓5%的低收入家庭能盡早置業。
人們往往把新加坡與香港比作“雙城”,這對互不相讓的競爭對手,始終處于心照不宣的競爭態勢。在過往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競逐中,香港明顯居于上風,不過近年來,在許多方面新加坡卻趕上了香港。“雙城記”越演下去,港人越感覺不是味兒。
新加坡是面鏡子,香港人照得不自在了。香港樓價高,低收入者望樓興嘆,同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卻人人有樓住,新加坡可以,為什么香港不可以?新加坡6000元收入的家庭也能置業,等同香港拿政府綜援的家庭也可置業。反觀香港,年輕人完全買不起房子,有香港網民說,“在香港月收入12000元的,要買下半個洗手間都難”。目前香港公屋輪候在冊的有23萬人,政府承諾每年提供1.5萬個公屋單位,月入8880港元以下的單身人士可申請公屋,2人家庭則要1.37萬港元以下。另外,2016年起4年供應共1.7萬個居屋單位。
香港與新加坡的差距緣何如此之大?可以找出十條八條理由,這里只說一條,新加坡的發展,是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下的精英主義管治完成的,變相的一黨專政,卻是通過選舉機制而獲得的權力結構,確保了執政黨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實,新加坡側重社會福利主義,政府決定權大。這些香港人能接受嗎?
要實現改善人均居住面積、人人有屋住的愿景,需要大量土地建屋。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同樣面對土地不足的發展問題,李顯龍提出遷移空軍基地和港口,騰出大片土地發展住宅和寫字樓,顯示新加坡政府銳意拓展土地以興建足夠組屋的目標,新加坡政府為鼓勵置業,可將七成地價降低,令購買組屋變相成為福利。香港政府表示要不遺余力增加房屋和土地供應,提出了未來具體的規劃藍圖和建屋量,但香港政府依賴土地收入,不會拿出大批土地興建公屋,再說,香港政府計劃開拓新界東北,填海及發展新市鎮,每一項都深陷社會和不同政治團體的紛爭中,面對不少激進勢力的阻礙,政治化干擾令政府拓展規劃寸步難行,香港社會如果不排除政治干擾,港人的住屋夢是無法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