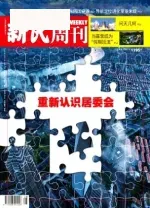傷痕之后又傷魂
何映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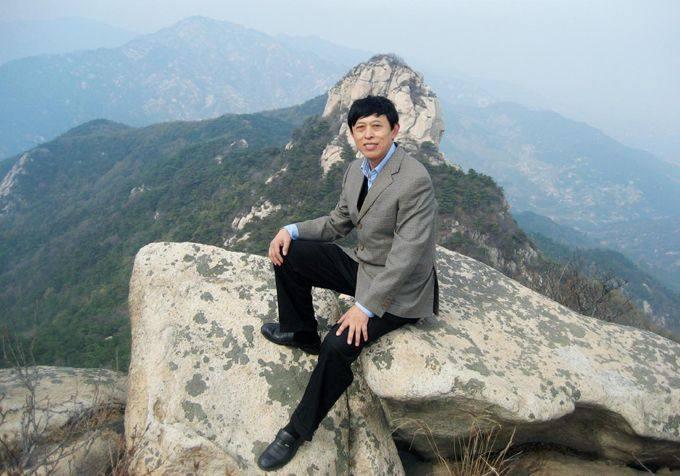
傷痕之后更傷魂。
2010年的《財富如水》之后,“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家盧新華又推出了他的新作《傷魂》。
《財富如水》以隨筆的形式,《傷魂》以小說的形式,形式不同,思考的內容卻是一致的,就是人性的沉淪。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傷痕之后,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卻沒有讓我們的靈魂獲得安寧,用盧新華的話說就是:“大道流失。”
大道流失之后怎么辦?精神價值的重建,需要知識分子的反思和啟蒙,需要一代人的反省,重建大道,任重而道遠。
“文革”前與“文革”后
《新民周刊》:寫作這樣一部長篇小說的初衷是批判當今社會的物欲橫流?
盧新華:對,對于當今中國人性扭曲的狀況,我思考得很多。
中國是個快速發展的國家,經過過去的窮苦歲月,很多人都窮怕了、餓怕了,一旦有機會賺錢,就會不擇手段不知滿足。我打個比方,就像一個非常饑渴的人,拿到一瓶水,他一定會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下;食物也一樣,餓極了,也是餓狼撲食,一副暴發戶的嘴臉。你看我們現在環境的破壞、各種有毒食物的泛濫,也可以說是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
我們這個時代,是大道流失的時代,就傳統文化來說,儒釋道三家所說的天道,都已經失去了。只留下了什么?孔子學院,教教漢語而已。道家,本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批判他們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現在也沒有進入主流社會,只是比較小眾的知識分子對道家思想感興趣。佛教呢,在廟堂里,大家求官求財,對于真正的佛教精神,并不關心。現在最盛行的,是權謀文化。你去哪個書攤,賣得最好的,還就是這種關于權謀的書,怎么對付員工對付老板,這是他們可以學的,就是這種文化在盛行。
《新民周刊》:你覺得這僅僅是經濟發展過快造成的問題,還是制度性的問題?
盧新華: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制度性的問題肯定是知識分子比較關心的問題,制度性的問題其實也是個文化問題,一種地域文化才能催生出一種地域性的制度,根源在于文化。這種文化或制度,在另一種土壤中,必然是無法生存的。在我們看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些顯然不合理的制度,在我們的土壤中能夠生存,必然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性因素在,才能長時間生存。
《新民周刊》:你覺得這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斷裂有沒有直接的關系?
盧新華:這當然有!我曾經將中國問題以“文化大革命”為分水嶺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文革”中和“文革”前,一是“文革”后。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整個意識形態和權力機構在做的,就是激發全民的仇恨。本來人類因為物質利益的分歧就會發生矛盾,我們的意識形態、權力機構不是努力去化解這些仇恨,反而是激發仇恨。我們這一代人在當時天天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是綱,綱舉目張!”這就是把人群以抽象的階級來區分,并讓他們互相斗爭,那一代人的心靈傷痕就是這種斗爭造成的。小說《傷痕》中的王曉華和她的母親劃清界限,那就是因為她把她母親作為一個對立的階級來看待的,那不再是母親,而是階級敵人,是仇恨的對象。我參過軍,在軍隊里,每次抗險救災前,先要憶苦思甜,增加對于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仇恨。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后,又進入另一個階段,有了“新傷痕”的概念。新傷痕和舊傷痕的區別在于,舊傷痕是階級仇恨這把刀子造成的,而新傷痕則主要由于貪婪,為物質的貪婪。佛教講“三毒”——貪、嗔、癡,貪是“三毒”之首。佛教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就是要放下“貪、嗔、癡”這“三毒”。人類文明總是在和貪嗔癡作斗爭,在我的《傷魂》這部小說中,龔合國這個人物身上,就有時代的特征,他也貪財、也戀權、也好色,他的身上,也有權謀文化的特征。他對權謀文化特別有心得,這些心得體會運用于實際生活中,也常常能創造實際的效果。
先亂其神,再奪其魂
《新民周刊》:《傷魂》的這個主人公叫龔合國,是共和國的諧音,就是將其作為共和國寫照出現的?
盧新華:對,龔合國的人生故事發生在共和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龔合國也就是共和國,或者說,前者就是后者的縮影。“先亂其神,再奪其魂”的是龔合國,但同時也是共和國的真實寫照。這種傷不僅傷在個體上,更傷在國體上,傷在民族之魂魄上。所以,揭示這種“時代之傷”,為的也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是每一個身體中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的人們的責任,更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以“悲天憫人”作為自己情懷的作家們的責任。為了揭示“時代之傷”,就必須用一種心理學家或精神病學家的眼光來對現實做持久的解剖和批判,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新民周刊》:你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怎么樣來審視“文化大革命”?
盧新華:這個時代對“文革”的反省常常采取一種淡化處理的方式,忽略掉它,好像這世界上從來沒有“文革”這回事似的。還有許多歷史重大事件,在媒體報道中,變成了一縷縷青煙,幾乎不見蹤影,這當然是不正常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個政黨一個人,都應該經常反省自己的歷史,如果我們缺乏了反省的力量,得到了,也很可能會失去。這世界上那么多的繁華,可是要毀滅的話,非常非常快,就像現在的底特律,曾經多么繁華的大都會,現在政府破產,成了一座鬼城,完全蕭條了,一幢房子就是一雙皮鞋錢了。以前經濟好的時候根本沒有人會預料到美國這么大的城市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如果我們對文化對財富沒有特別的警惕和反省,那是很可怕的。
關鍵是我們看歷史規律,所有的繁華總有沒落的一天,而且這一天來的速度之快,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我記得有本書中說過:如一條船航行水上,又快又穩,但是在臨到碼頭時翻了船。我們很多貪官不就是這樣嗎?他們在仕途上,就像龔合國一樣,一開始都是順風順水,家庭、事業、孩子、方方面面,都很春風得意,可是他們認為可以全身而退的時候,翻船了,要在牢獄之中度過下半生。國家也是如此。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人的疾病和國家、民族的疾病是一樣的。從這方面來說,我可能還是有點憂國憂民的,在這部小說中龔合國就多少有點這個時代的影子。我當然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和諧、健康、美滿的人生,但這要建立在我們對文化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之上。就如我在《財富如水》中所說的,我們要契合天道!
《新民周刊》:如果要為這個“大道流失”的時代開出藥方,你覺得我們應該怎么應對?
盧新華:從整個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著想,我能開出的藥方必定是:契合天道,平衡人欲。因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生存的環境已經變得傷痕累累,不堪入目。但我們既然已經經歷了“存天理、去人欲”和“存人欲、去天理”的兩個畸形發展的歷史階段,知道都不可取,那么,我們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去肯定一個比較理想的改革和發展方向,那就是 “合天道、衡人欲”。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唯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