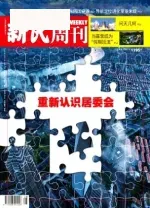蓋茨比的了不起
闕政


8月剛開頭的那幾天,走進電影院,會有這么一種感覺:拍電影真容易——隨便寫個劇本,來幾個帥哥美女,穿插些慢鏡頭、特寫、分屏,再加上一點對上流社會生活的貧瘠想象,就成了!
等到8月底,再進電影院,感覺又好像完全變了:有些電影浩大繁復得需要重構一個不小的時代,每個環節都可以無止境地做精做細,了解越多,就越覺出它的深不可測……
了不起的重逢
很多美國人都是從他們的高中課本里,第一次知道有“蓋茨比”這么個人物。菲茨杰拉德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它初版的1925年只售出了4000余本,影響卻綿延將近100年,家喻戶曉到幾乎被漠視的程度。導演巴茲·魯赫曼(Baz Luhrmann)找到男主角小李子的時候,后者感嘆:“這就像美國的莎士比亞故事。”但,“我對它的印象還是停留在高中時,那時讀后也沒什么感覺。”
其實導演本人早在12歲那年就看過羅伯特·雷德福主演的1974年版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兒時的記憶也僅僅是“雖然畫面漂亮但又有些空洞”。
然而,西伯利亞火車上的一次重逢改變了一切。
2004年,拍完《紅磨坊》的巴茲從北京搭乘西伯利亞火車快線,打算穿越俄羅斯北部,到巴黎去見他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當我發現這不是我所期待的托爾斯泰式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派的浪漫之旅,而是被困在一個小小的車廂里時,我想起我有一本有聲讀物和幾瓶澳洲產的葡萄酒。”于是他喝著紅酒,打開了有聲讀物……“6個小時過去后,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第二天再一次回到車廂做同樣的事情。”就在那時,巴茲意識到,蓋茨比的故事“具有電影的架構”,并且暗暗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我要把它拍成電影”。
事實上,小說吸引他的遠不止是“電影的架構”。蓋茨比故事里那個極度奢靡的世界、破碎的愛情之夢,歷來都是導演的心頭之好,要不然,他就不會因為拍出《羅密歐與朱麗葉》、《紅磨坊》而名噪一時了。
這幾乎是一次注定會成功的翻拍。有人說,《蓋茨比》完全就像是昨天寫的故事,影射當下時代。紐約的夜晚和當年一樣熱鬧,摩肩接踵的紅男綠女依舊讓人目不暇接。奢靡和愛情的吸引力只增不減。更妙的是,對觀眾而言,《蓋茨比》不僅是雞尾酒,也是醒酒茶。紙醉金迷的微醺與悲劇性的頹廢交相輝映,飄飄然與自省的感覺交織而來,殺傷力絕對是二次方的。
唯一的問題是,版權凍結在曾經拍過電視劇版《蓋茨比》的A&E電視網絡公司手上,巴茲耗費了將近十年時間去爭取。
了不起的考據癖
不過,新版電影的成功也不是必然。畢竟,考慮到小說的情節,假如碰上三流導演,還是有被拍成瓊瑤式婚外戀故事的可能性。而菲氏原著的《本杰明·巴頓奇事》2008年被大衛·芬奇搬上銀幕后一舉拿下13項奧斯卡提名,也讓后來者感到了沉沉的壓力。更何況,《蓋茨比》還早有三版電影在前,不乏珠玉。
“要怎么來拍攝這個電影才能讓廣大現代觀眾接受呢?”巴茲再三自問。和許多知名導演一樣,他對待任何工程,起點總是“先從搜集做起”。
讓人佩服的是,他的考據不僅是普遍意義上的了解時代背景、搜集影像資料,以至于知道1920年代的游泳池里常常會出現橡膠斑馬……他的考據是連小說版本都沒有放過。
好朋友、知名導演科波拉告訴巴茲,他當年做1974年版《蓋茨比》編劇的時候,很多靈感來源于菲氏的其他創作。于是巴茲讀了《最后的大亨》、菲氏的自傳體小說,甚至菲氏最喜歡的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兩者的故事架構有很多相似之處:天真無邪的人在旅途中遇到了偶像人物。”
當年菲氏輾轉長島、紐約和法國的圣·拉斐爾,于三地完成了《蓋茨比》的創作。如今巴茲故地重游,任何細節都不放過:“菲氏在圣·拉斐爾郊外的一個別墅里寫作《蓋茨比》。就在20分鐘路程外的戛納海灘邊,他的妻子和一個帥氣的軍官發生了婚外戀。”最終,電影的首映禮所在地,距離菲氏當年寫作的長島,也只有20分鐘路程。
那段時間里,巴茲、小李子,還有飾演蓋茨比好友“尼克·卡拉韋”的托比·馬奎爾,三個人常常在房間里一圈圈地走著“尋找著更多的東西、更多的細節……就像鯊魚在水里追著血腥味一樣”。
了不起的蓋茨比
找個什么樣的人來演蓋茨比?巴茲的心里充滿了形容詞——復雜、浪漫、黑暗、有魅力、一個偉大的演員……他若笑起來,“就像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那種笑容,那種笑容讓人安心”,然后轉瞬間,表情看上去“就像他殺了一個人”。
這些形容詞最終不出意料地把他引向了小李子——22歲上,后者就出演過他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而他說服的方式也極其簡單——把一本舊版小說拍在桌子上,告訴后者:“我已經爭取到了拍攝權,我想和你一起拍。”
如今,我們甚至不需要再追問導演,他心目中的蓋茨比是什么人,是浪漫主義者還是徹頭徹尾的瘋子,是不是符合我們讀小說時的想象。聽聽小李子的理解,已經足夠放心——
“15歲上初中那時候讀的蓋茨比和我成人后讀的蓋茨比是大不相同的。我在初中時對故事的理解是:這是講述一個男人單戀一個女人,為了能和她在一起而創造了大筆財富——這是個悲劇的浪漫愛情故事。
“成年之后重讀此書,卻讓我深深著迷。主人公是如此地空虛。他在尋找一些對他的生命有意義的東西,并且為他的舊愛黛西深深著迷——她就是他的海市蜃樓。蓋茨比所舉辦的派對,以及經營使他暴富的地下酒吧生意,都是為了讓他愛的人、也讓美國貴族們重新接受他。從中西部的貧民小伙兒打拼成‘了不起的蓋茨比,他想成為那個時代的洛克菲勒,這是他的美國夢。
“蓋茨比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打造他的府邸,為了把黛西吸引進來。但即使他牽著她的手,他還是在凝視那盞綠燈。他仍然在尋找可以讓他生命完整的東西……
“即使經過了80多年仍然一樣。在這個摩登時代我們已經重復經歷過同樣的事情,而且還在重復做同樣的事情。菲茨杰拉德評價了社會的本質、人的本質和不斷追求財富的人性。”
——如果說演技是基于對角色的體認,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小李子即將呈現的蓋茨比,一定不會只有迷人的外表。
了不起的大海撈針
相比小李子的一錘定音,女主角的人選就沒那么容易了。任誰都知道“黛西”對于整出戲的意義,更何況對手還是小李子這樣的偶像實力派。
“毫不夸張地說,每個你能想到名字的女演員,都很想出演這個角色。”巴茲說,“這是那種大師級、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角色。所以我們發現自己好像就處在《飄》那樣的境地,我們探索所有的可能性。”
《飄》一般的尋找。幸好,《蓋茨比》最終也找到了他的“費雯麗”:凱瑞·穆里根。
巴茲在好萊塢知名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的奧斯卡派對上,見到了這位出道不久的年輕女演員。“我還記得她當時穿著V&A的復古裙子,氣質優雅獨特。我走上前,和她打了招呼,發現她是個聰明伶俐的人。”
在凱瑞參加試鏡的整個過程中,巴茲和小李子一直在交換意見。
導演要找的“黛西”必須具備美貌的外表、年輕的氣息和天真的氣質。而小李子眼中的“黛西”不光天真,還得有一種“因為貴族出身而擺脫不了的追求享樂的個性”,“即使她愛著蓋茨比,但最終更重要的是別人怎么看她。就像她說的:‘我希望我的女兒將來是一個快樂的小傻瓜,在這個世界上女孩最好的就是當美麗的小傻瓜。”
最終,還是小李子的一句話說服了導演——他告訴巴茲,臺詞里有句話是這么說的:“蓋茨比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了解了女人。”“那意味著蓋茨比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很多美麗的女人對他投懷送抱。如果黛西只是聰明美貌,他不會想要和她有任何關系。”小李子說,“但你看凱瑞的詮釋,她就是溫室中的花朵。于是你就會明白他想把她放在玻璃盒里保護起來的欲望。那是他執念的起源,也埋下了瘋狂的因子。”
聽完這番話,兩人互望一眼,異口同聲道:“就是她了。”
了不起的澳大利亞長島
電影就是造夢,而蓋茨比的夢,更比其他電影難造得多。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當大部分觀眾都以為這是對1920年代的懷舊旅行時,導演卻并不是這么打算的。根據攝影師回憶,巴茲讓他把一切都拍出“嶄新”的氣息,“他希望拍出來的效果,是我們就置身于1920年代那個令人迷惑的時期,而不是我們在回頭記錄那個時代。”
造夢師的秘笈,首先就是打造一個令人信服的場景。曼哈頓中區的“王牌酒店”很理想,從套房的凸窗里看出去就是紐約城,周圍還有很多菲茨杰拉德時期的建筑物。但迫于預算,電影的大部分場景仍然只能在澳大利亞完成,而不是紐約。
“湯姆·布坎南”的豪宅其實是在悉尼福克斯工作室的大舞臺里搭建出來的。相比蓋茨比,布坎南的家象征著世代相傳的名門望族,劇組沿襲了美國富豪典型的建筑風格,用白柱、紅磚去堆砌,40英畝精心修剪過的草坪直通海邊。
而蓋茨比,他卻是一個“不知從哪兒冷不丁冒出來的在長島上買了座宮殿”的新貴。為了表現蓋茨比的野心、浪漫和孤獨,他的城堡被打造成哥特式巨型豪宅,還高聳著閃亮的炮塔。
為此,巴茲在悉尼的一座山上打造了一個長島。而那座城堡,原先是一所天主教男生學校,巴茲的高中時代就在那里度過(他是澳大利亞人)。
有人問小李子,是否就住在城堡中。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導演甚至常常在早晨跑進來說:“請去叫醒蓋茨比先生,巴茲先生準備給他個近景。”然后一幫傭人跑去敲他的門,小李子就會穿著長袍下來說:“我準備好了。”
從影片中看,蓋茨比的城堡像極了“迪士尼”的城堡。在巴茲看來,蓋茨比先生的假日派對就是一場夢境般的狂歡,所以他的城堡,也就是一座“成人迪士尼”游樂場。
了不起的夫妻檔
凱瑟琳·馬丁也是澳大利亞人。20年前就開始和巴茲·魯赫曼合作,一直合作到與他戀愛結婚、生兒育女。
盡管此前已經榮獲兩座奧斯卡獎(美術指導、服裝設計),但《蓋茨比》還是讓凱瑟琳感嘆:“我從沒參與過一部電影,在戲服細節設計上如此大量、如此復雜。”
按照導演設定的歷史發展概念,小說的時代背景是1922年,而它的故事又暗示了1929年的金融危機。對凱瑟琳來說,“規則是我們可以引用任何1922年至1929年的事物。”
凱瑟琳對原著中的每一句描寫都作了詳細研究——1920年代流行的西裝,配搭向后折的袖口;黛西的三角帽子;蓋茨比司機的制服是知更鳥蛋的那種藍色……
美國傳統服飾品牌布魯克斯為劇組提供了2000套服裝供選擇,燕尾服就有200套之多。與布魯克斯合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曾經賣過衣服給菲茨杰拉德,至今還存有大量菲茨杰拉德要求定制衣服的來信。”
對凱瑟琳來說,服裝不只是演員的一部分,服裝就是演員。“蓋茨比那種從容優雅、湯姆·布坎南那種天生的粗魯氣質,還有尼克·卡拉韋那種來自中西部、受過良好教育的農家孩子,整體服裝造型要能體現出他進入上流社會后的蛻變……這些都要通過細節來體現,而我就是要細致再細致。”
她那種細致,是細致到可以隨時準備好和別人打筆墨官司——“我總是擔心,假如我不像歷史中所記載那樣精確地去設計,會被人逮捕。人們會說:‘那個針織衫的衣服重量和1922年那時穿的不一樣。然后我會說:‘等一下,我肯定我可以找到那個時候人們穿著那件套頭衫的照片。然后就去找來說:‘看!”
令“湯姆·布坎南”的扮演者喬爾·埃哲頓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片中,“湯姆·布坎南”和“尼克·卡拉韋”畢業于耶魯大學,并曾是某神秘組織的一員。劇組經過調查,發現那個組織很可能是“骷髏會”。“于是凱瑟琳在我的西裝上縫了個骷髏和骷髏腿的圖案。”埃哲頓說,“她本不需要那樣做,而且你可能根本看不見,但我知道衣服上有。”
——不知道看IMAX的同學,你們看到了骷髏腿沒有?
了不起的爵士時代
“爵士時代”這個詞,幾乎就來源于菲茨杰拉德的小說。在《了不起的蓋茨比》里,他引入了當時美國黑人的新興音樂——爵士樂,包括1922年最熱門的曲子《凌晨三點》,還在手稿中記錄了70多首流行歌曲。
巴茲也喜歡爵士。但他不能再選用當年的抒情爵士——“我不要鏡頭里有那種漂亮的、朦朧的薄紗,配著暗淡的色調,像是在回憶往昔。同樣,我也不要會激起人們思鄉之情的音樂。”巴茲說,“因為當你讀了小說,你就會發現,那不是一種回憶往事的感覺,而是當下,就在當下的感覺。”
這一次,巴茲要的絕對不是懷舊,而是直接帶領觀眾搭乘時光機,回到1920年代當下。他問自己:“什么音樂是立竿見影讓人感覺活在當下的?”聽聽爵士,再比較一下現今美國黑人的街頭音樂——“那就是嘻哈了!”
于是制作團隊里多了說唱音樂界的統帥人物、17次捧得格萊美獎的——Jay Z。嘻哈樂的根源里有爵士樂,而它又是爵士樂的新時態表達。“嘻哈和爵士都是很純粹的自我表達方式。”巴茲說,“我們一定要讓觀眾感覺到在蓋茨比派對上第一次聽到爵士樂的感覺……新世界正在形成,每個人是如此年輕,如此美麗,如此富有,又是如此醉醺醺和瘋狂。我們希望能讓觀眾有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要去世界上最棒的夜店,就好像我們在開世上最快的汽車……”
對巴茲來說,電影配樂不是單純地還原那個時代,而是為那個時代的音樂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進行解碼。
去年,阿黛爾的一曲《Skyfall》就為“007”大電影加分不少。如今,Jay Z也攜妻(碧昂斯)上陣。巴茲果然如傳說中的那樣:對待電影音樂就像對待電影明星一樣。
了不起的3D
3D最青睞的電影類型莫過于:災難片、奇幻片、動作片、驚悚片、動畫片……一部電影選擇以3D形式制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種:突出視效、場面火爆、賣更貴的票……以往,觀眾面對3D多少有點“圈錢”的質疑。然而有趣的是,這一次,既非奇幻亦非災難,《蓋茨比》首開了劇情片3D化的先河,卻沒有招致非議,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認同:這樣一部電影,無論3D還是3D+IMAX都是相得益彰的。
說它開先河,事實上并不很準確——畢竟希區柯克的《電話謀殺案》最近也被改制成了3D版本。也正是這個版本,讓巴茲“靈光乍現”:“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沖我而來的那些東西——而是格蕾絲·凱麗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我真想伸出手碰碰她——拍攝鏡頭并沒有動,是她在移動和表演著。于是我想到,在3D電影里,讓一個演員走向鏡頭,而不是把鏡頭移近演員,這是一項多么強大的改革啊!”
巴茲說他喜歡原著小說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它的描述讓人感覺身臨其境,就像你在現場一樣。”所以,他現在要所有電影觀眾也和劇中人一樣“置身派對之中”,“和他們一起狂歡”。在技術方面,他采用了比較寬的廣角鏡,“這樣的鏡頭比較接近人類的眼睛看出去的視覺”。
或許,蓋茨比窮其一生都未曾如愿。但這一次,至少巴茲·魯赫曼是找到了他自己的“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