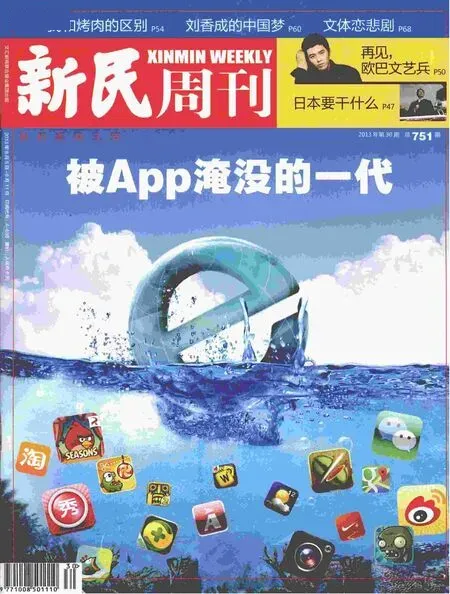App嵌入柴米油鹽
任蕙蘭
前不久,北京交通委的一紙新政給了草根打車軟件“轉正”的希望,但規定App將和電調同樣收費,不得插入商業廣告。官方對App的態度從叫停到收編,因為不得不正視平臺上的龐大用戶量。從打車軟件到新崛起的家政服務軟件、代駕軟件,生活應用類App的瘋長給線下行業帶來了危機感,這也表明它們正在嵌入人們的生活。
“接地氣”是王道
7月的某一天下午,琳達在辦公室用打車App發出了用車需求,45秒后,收到了一位出租車司機的回應。經過電話確認位置和目的地后,琳達吹著冷氣等待司機“接駕”,5分鐘后她就坐在車里繼續吹冷氣。
炎炎夏日等候在路邊打車是很多人經歷過的“苦役”,尤其是公認打車難的一線城市,情況正在因為打車App而改變。
活躍在市面上打車App有大大小小幾十家,其中“快的打車”和“嘀嘀打車”規模最大,瓜分了大部分市場份額,領土基本以“南快的、北嘀嘀”分配。“上海有5萬多輛出租車,我們App覆蓋的有3萬多輛,一般一輛車配有兩班司機,所以覆蓋的司機人數在4萬-5萬。”“快的打車”COO趙冬說。
經過最初瘋草般的野蠻生長,打車App的擴張腳步緩了下來,由于磨合中暴露出來失信、短途難約等各種問題,有一些參與者被擠出了市場,另一些忙著進化。
琳達的打車路線很近,這樣的“短差”在App平臺上并不吃香,搶單的司機很少。揚招的乘客上車以后再指示目的地,遇上“短差”司機也只能自認晦氣,不會冒投訴風險拒載,但在App平臺上司機不會搶路線太近的單子。
打車App的推送模式是先向乘客位置最近的一圈司機推送,如果沒有人搶單,一定時間間隔以后再向外圈推,每一圈的距離和間隔時間是每家打車App的技術機密,根據時段和區域不同也會有差異。對于“短差”,如果近距離的司機不感興趣,遠距離的司機更不會千里迢迢趕來接這檔不上算的生意。
所以,看著自己的“短差”在1分鐘內被搶,琳達很出乎意外。
司機解答了琳達的疑惑:這和新的游戲規則有關。以上海地區活躍的“大黃蜂”為例,它根據每一單的路程距離給司機一定的積分,“短差”積分高于“長差”,司機累積40分以上有資格搶去機場的長單。此舉提升了司機接“短差”的興趣,短途乘客自然也容易打到車。
這只是打車App進化中的一步。
“在App上搶單也有風險。比如接了你這單,過來的路上我就放棄了好幾個揚招。”司機告訴琳達。同樣,乘客在等待過程中也會錯過幾輛空車。這些錯過的揚招和空車在經濟學上叫做機會成本,根據大數原則,一般乘客和司機對使用App造成的沉沒成本是有心理預期的,但總有例外,因此就會有一定比例的乘客和司機被“放鴿子”。
琳達有過一次被“放鴿子”的經歷,她在計算好時間預約了一輛車后,氣定神閑地在GPS地圖上觀測司機的動向。琳達看著司機慢慢靠近自己的位置,卻突然折向另一個方向,越走越遠,再打電話司機已經拒聽。她只好手忙腳亂沖下樓去揚招,對毫無誠信的司機給出一個差評。
各家公司對于失信的處罰不同。失信的乘客也會被封號,不過相比司機,重新注冊的成本更小。各種解決失信現象的辦法浮出水面,比如打車App綁定支付寶。現在乘客已經可以通過支付寶手機客戶端付打車費,趙冬表示,已有幾千個司機綁定了支付寶,數字還在增長。“快的打車”會和支付寶有深化合作,“能將放鴿子現象徹底消除”。阿里正是“快的打車”的投資人。
從打發地鐵時間的小游戲,到嵌入用戶生活的實用工具,App變得越來越“好用”。不管是打車、代駕還是家政App,都在打通線上和線下生活服務的資源。但是找準用戶的穴位,讓他們乖乖付錢,并沒有這么容易。
沒有盈利模式的創業是耍流氓
在第一輪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整合線下服務資源)試水中,先驅是打車App,關鍵詞是燒錢。
運營商對新注冊的用戶進行話費補貼,搶單排行榜上靠前的司機獎勵油卡、OK卡等,司機成功游說乘客下載軟件,也會受到獎勵,加上廣告推廣,支出非常龐大。而在收入這一塊,平臺向用戶收費就意味著找死,所以各家都在努力做大蛋糕,賺錢是下一步。
之前傳出打車App可能會根據用戶的上下班打車軌跡,推送附近的美食健身等信息,但新出臺的官方招安公告里有一條,不得插入廣告。所以很難說打車App有明顯的盈利模式。
第二輪進入O2O的玩家則想要找到更有賺錢希望的領域。有人坦率地說,沒有盈利模式的創業是耍流氓。
以用戶發布需求,阿姨(保姆)搶單為游戲規則的“e家潔”幾乎是打車模式的翻版,它是云濤和孫磊切入App市場的第二個產品。在前一個產品“嘟嘟打車”的失敗嘗試中,他們對新一次創業定下兩條軍規:第一選開放的市場,第二要有盈利模式。
“做O2O我們扮演的角色是信息中轉,相當于中介,所以要做市場大、使用頻次高的產品。最先考慮的有兩個,一個是房產中介,一個是家政,但房產中介除了信息傳遞的功能以外,還有推銷性質,需要業務人員和買賣雙方溝通,不適合O2O模式,所以最后選擇了家政。”孫磊說。
這個時候他們看到了希望,美國家政服務App 公司Homejoy完成了170萬美元的融資。“這是個千億級的市場。” 兩人找了很多阿姨聊天,了解家政市場價格體系。經過兩周左右的調研,第一個試水產品“快保潔”在微信平臺上啟動。“發了200多份傳單,當天有100多個用戶注冊,在平臺上成交了十幾單。”
6月初,“e家潔”正式上線。和做免費平臺的打車軟件不同,e家潔一開始就有清晰的收入來源:向阿姨收取年費。傳統家政中介每小時收費在20-30元,其中15-20元給阿姨,e家潔價格在20元/小時,平臺不抽成,但向阿姨收300-600元年費。“阿姨花了錢就會重視這個平臺,珍惜每個工作機會,如果平臺是完全免費的,她們就會覺得無所謂,搶來的單不去做。”孫磊說。
當做到1000單以后,兩人開始考慮融資,會見一輪又一輪的投資人。投資人的問題雖然不像TV秀里魔鬼導師那么麻辣,但也直指要害。
最常被提到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家政不像打車有標準化的服務,每個阿姨打掃的干凈程度、打掃方式不同,如何制定統一標準?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跑單。阿姨和用戶聯系上了以后,經常會跳開平臺直接交易。
經過實踐,孫磊發現解決第一個問題的關鍵是篩選,雖然每個人的服務有個性化,但有經驗的阿姨總是會讓用戶滿意。“北京有30萬阿姨,是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可以通過篩選專業的阿姨來提高服務品質。”“e家潔”招聘門檻是從業3年以上,50歲以下的阿姨。另外還有處罰機制,對于磨洋工的阿姨,一次給機會,二次剔除。
平臺還引入好評制度。完成100單,好評在85%以上的阿姨會被評為四星級,時薪漲1元,500單以上評五星級。這樣做既為了激勵阿姨提高工作質量,也為抑制跑單。“因為阿姨和用戶直接交易,可能做幾年對方也不會價錢,但在平臺做有機會漲薪,雖然只漲幾元時薪,阿姨是很在乎的。”
“市場上70%的單子可能會跑,北京地區每天就有10萬單跑單。”孫磊發現,完全杜絕跑單是不可能的。他們轉換思路,為什么一定要杜絕?這個市場那么大,即使容忍一定程度的跑單也可以生存。那下一個問題就是,對跑單容忍到什么程度?就要制定規則去盡量避免。
團隊對系統做了更新,用戶不用每次都在平臺上發布家政需要,等阿姨搶單,可以直接查看“我的訂單”歷史記錄,聯系使用過的阿姨,這一單還是被留在了平臺上,既方便了使用者,也增加了平臺黏性。
打車軟件的經驗也被移植到e家潔,20%的打車單子會加價5-10元,e家潔也引入加價模式,晚上6:30以后和周末叫家政服務的用戶集中,這時候提出加價對阿姨的激勵作用很明顯。
孫磊介紹,目前平臺投訴率只有1%-2%,說明服務已經非常標準化。不過“e家潔”的商業愿景還不止于此,將來會推出自己的認證,把在App平臺上注冊的家政服務員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收費標準不同,“當e家潔一級阿姨成為市場上認可的品牌,我們就有了排他性,不怕其他人的競爭了。”
另一方面,O2O切入的小時工市場在家政細分市場中標準化程度高,但附加值相對低,利潤也比較薄。孫磊說,“e家潔”會先通過做好小時工市場打品牌,再切入附加值更高的月嫂、保姆和家政培訓市場。
如果再繼續定位App開發者為“技術宅”,似乎已難以對應于他們豐滿的商業藍圖。
別再叫我“技術宅”
在細分化程度高的市場,需要App產品有很多創新。而創新更多建立在對使用者行為模式和需求偏好的研究上。這些商業邏輯不是一堆代碼能說清道明的,要求開發團隊更多元化。
云濤和孫磊就是一對互補的搭檔。他們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同學,云濤是市場營銷專業出身,在奇虎工作一段時間后,去美國西北大學進修了8個月,回國投入創業。孫磊學的是計算機,在互聯網企業工作了4年。從一開始兩個人的分工很明確,孫磊負責技術,云濤負責市場。
智能手機最初興起的時候,第一波搶占市場的是娛樂類App,有很多是技術宅閉門造車的產物,但要將App嵌入生活,成為使用者不可或缺的工具,純技術宅不那么能hold住了。一個開發團隊的構成比以前更“雜燴”,除了技術人才之外,還要有了解市場營銷、精通行業背景的商業人才。
“微代駕”創始人顏瑩也是一位復合型CEO。他從武漢大學本科畢業后,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之后又獲得了杜克大學的MBA。在投身創業之前,曾做過幾年風投。
他做的第一款App是“地省”,是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導購軟件,商家可以在平臺上自助發布團購信息。當時團購網站風頭正勁,移動互聯網支持的導購App也遍地開花,競爭很激烈,地省湮沒在了其中。所以顏瑩的第二次嘗試獨辟蹊徑,瞄準的是一個尚未飽和的市場——代駕。
“現在國家法律對酒駕零容忍,代駕需求增長很快,相比去年增長將近200%,現在北京每天有2萬單代駕需求,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開發了代駕App。找代駕的人會越來越多,如果有好的平臺,把品牌做起來,很多人會選擇。”顏瑩說。他看中這個領域一是因為市場夠大,二是馬上能賺錢,司機愿意為代駕平臺付費,因為他有收入。
“微代駕”平臺上一單代駕的起步價是39元,平臺抽10元信息費。6月3日上線以來,20多天下載量達到2萬多個,擠進了蘋果中國區旅行類App前20名。現在北京有司機800多個,上海有500-600個,成都有200多個,一般同時在線的有20%-30%。“在北京,用戶打開手機搜索,5公里內一般就會有司機。”
但顏瑩說,做一款App,線下比線上更難。
根據對代駕使用者的調查,人們對代駕服務的諸多要求里,排第一的是安全,遠遠超過服務和便捷方面的需求。那如何保證代駕安全?
顏瑩說,最重要是找靠譜的司機。公司在前程無憂等招聘網站發布招募信息,也會找在58同城、趕集網上發布求職意向的司機,要求應聘者駕齡在5年以上,擁有派出所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本地戶口優先(或有本地戶口擔保或本地有房產)。司機的選拔是通過面試、培訓、在線考試和路考幾個環節,通過所有考試的司機才能上崗。
經過嚴格的入職關后,司機表現不佳也會被“一陣出局”。“司機受到一次用戶投訴,如果核實屬實,就直接解除合作,而不是罰款了事。比方我們代駕起步價是39元,乘客給40元,他說沒零錢不找了,就可能因為這一塊錢被解除合作。因為培訓時就講過出車必須帶零錢。”
“我們平臺的代駕司機有白領,也有單親母親,大部分是老實本分的普通人,家庭負擔比較重才做兼職,所以會珍惜這個平臺的工作機會,遵守規矩。”
其實相比司機,更難以約束的是平臺的用戶,因為找代駕的人一般都喝過酒,容易情緒不穩。“我們在培訓時會講,如果發現乘客是醉酒狀態就不能接,微醉的話先和家人聯系安排,如果發生沖突,司機要安撫乘客情緒,或把車停在路邊,先不開。”若乘客無理取鬧,核實情況也會直接封號,因為惡劣乘客的存在是平臺的不穩定因素。
在實踐里還會遇到很多問題,考驗團隊的情商。比如代駕司機自身夜歸難題,北京有夜班車,司機可以步行到夜班車點坐車,車上的夜歸人一般也都是代駕司機;或者通過App查看周圍代駕司機,大家一起拼車回去。但總有司機送客到偏僻地區,最新的辦法是司機輪流值班,當天不做代駕,開自己的面包車接送其他司機,收對方代駕費的15%。“晚上代駕費在79-99元,一車坐好幾個司機,值班司機一晚上掙100多元,收入也不錯。”
顏瑩說,現在平臺的收入主要來自收取信息費,未來會推出增值服務,“比如VIP會員可以獲得金牌司機服務,會員的單次價格會更便宜。對于應酬多的公司,辦一張會員卡會很劃算,可以供很多人使用。”“微代駕”上線之后,已經有5家風投和團隊見過面。
攪局者
O2O的興起不可避免對傳統行業造成沖擊。這些好用的App被視為“攪局者”。
“微代駕”的收費比傳統代駕公司低60%,一般線下公司收費150元到200元,App平臺收費一般在39-99元。
但司機的收入并不因為價格低廉受影響,因為傳統代駕公司一般和司機四六分賬,也有給司機20%,但有底薪,App平臺上向司機抽傭較低,79元以下的單子收10元,99元及以上的單子都是收20元。比如司機做79元一單,拿到手69元,收入超過為傳統代駕拉了一個150元的單。
除了靠經濟利益來吸引司機和用戶,App平臺也在積極拉攏為傳統代駕公司提供大量業務的酒吧、餐館,從中分一杯羹。“我們在和一些高端的酒吧餐廳談合作,為顧客提供代駕服務。高端酒吧更注重代駕的服務品質,酒吧可以在我們的系統上查到代駕路線,更能保障客戶安全。我們和酒廠也在談,爭取把代駕這部分納入企業社會責任開發的一部分。另一個渠道是和銀行信用卡合作,承接VIP客戶代駕服務的外包。”
家政App也在“攪局”。“用戶最看重的是安全和干凈。他打電話給家政中介,對方翻一下電話本,告訴你一個有空阿姨的電話,沒有起到需求匹配的作用,用戶要試錯2-4次才能找到滿意的。用戶從App上發布需求,可以看到搶單阿姨的信息,她是幾星級,搶過多少次單,滿意率怎么樣。”越來越多阿姨會用使用智能手機,當這個群體完全習慣用App接生意,傳統中介就會顯得很雞肋。
線上的“攪局者”也遭到了線下的抵制。
打車App風行后,出租車公司電調平臺生意大減。在上海地區,司機用大眾或強生公司的電調平臺每個月要花120元,乘客為每次電調支付的費用是4元,雙方都要為信息傳遞付出額外的成本。打車軟件的出現將雙方的成本都降為零。
叫停打車軟件的呼聲一直沒有斷絕,交通部門曾提出打車軟件的加價功能有擾亂市場定價之嫌。“嘟嘟打車”就是與傳統行業競爭下的犧牲品,當時“嘟嘟打車”采取的模式是租車和招募司機,和出租車差異化競爭,方便乘客在難打車的位置用App叫車。但很快管理部門發來通知,稱“嘟嘟打車”這項業務沒有獲得出租車運營執照。“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是交50萬罰款,二是停止業務。我們交不起罰款,只好退出市場。”孫磊說。
好用的App結局似乎注定是接受大佬們的招安,然后逐步提高收費。不管未來怎么樣,用戶還是抓緊時間再多吃幾頓免費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