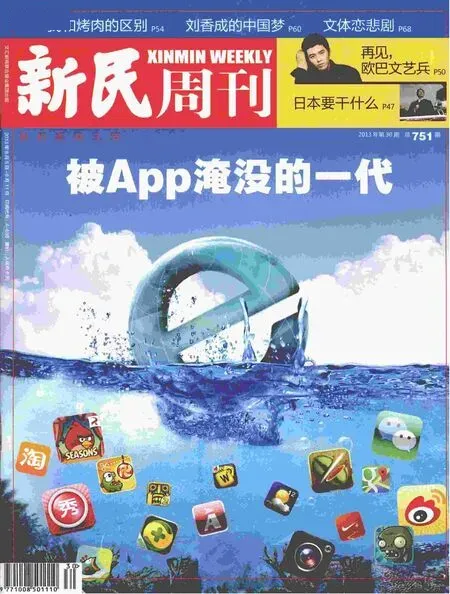火車上的牛仔
崔驥
按照烏拉圭歷史學家加萊亞諾的說法,美國西部片是好萊塢編織的神話,一個風靡全球、違背事實的傳說。在西部片里,所謂牛仔,并非沉默寡言的紳士、腰板筆挺的俠客,抑或常常英雄救美的騎手,而多半是饑腸轆轆的短工,為了可憐巴巴的工錢勞碌,西部史的主角絕非加里·庫伯、約翰·韋恩、伊斯特伍德之輩,并且要么是黃皮膚、黑皮膚,或者是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也從沒有化妝師關照過他們。
當然,史家之言也僅是一家之言。電影是藝術,它不是現實與歷史的奴仆。縱然西部片的主角們并不吻合歷史上真正的西進英雄,但是作為傳播文明的代表,也是鞏固文明、建設文明的先鋒者,理應享有藝術的眷顧。但有一方面加萊亞諾是認同的,就是故事發生的舞臺永遠是一個破敗凋敝的小鎮,小鎮上有一座火車站。
影片《西部往事》,賽爾喬·萊翁導演,開場便是西部偏僻的火車站蕭索地立著,繼而火車到站,汽笛聲響徹耳際之后,琴聲響起,音樂名很詩意,Man With A Harmonica(帶口琴的人),襯托無名氏出場,樂曲蒼涼、凄厲、嗚咽,訴說時事維艱。一陣槍戰,隔著鐵路,三名牛仔斃命在無名氏槍下。
牛仔文化和西部精神是美國精神的原點,如同美國歷史學家威廉·薩維奇所說:“人們很難想象,假如沒有牛仔這個形象,美國的文化,不管是粗俗的還是高雅的,會成什么樣子。要找其他形象來取代他,簡直太難了。什么猿人,太空人,槍手,還有超人,都曾名噪一時,可哪一個也不曾把牛仔的形象給壓下去。”美國人從東向西鋪設第一條鐵路時,目標不單是進行一次西部拓荒,而是野心勃勃地要建立一項“偉大的事業”。
鐵路決定了城鎮的大小范圍和性質。拍攝于1952年的經典西部片《正午》,三個罪犯來找當年送他們入獄的警長復仇,三人初出場背景正是一個小火車站,第一句對白是問售票員“正午的火車還有嗎?”鐵道兩側相對的木屋便是車站,車站建筑符合愛默生《生命行為》中關于“美”的規范,“我們在建筑的品鑒中拒絕涂料,以及所有虛假變幻的東西,表現出木料原始的紋理;拒絕那些什么也沒有支撐的柱子和壁柱,只允許真正的結構物支撐著房屋,使房屋能夠誠實地表現自己。每一件必需的或有機的組成部分,使得觀察者們感到了愉悅。”
《阿帕魯薩鎮》里充滿蒙塵的光線,飽經歲月侵蝕的面部肖像,廣闊的背景空間,這個很有立體感的故事是對該類型傳統的致敬。而當維格·蒙坦森飾演的阿弗雷德站在冒著黑煙的火車上,我們又看到這幫家伙的兇狠與果敢,這個畫面似曾相識,早在西部片《鐵騎》里,以美國修筑橫貫東西大鐵路為背景,跟隨火車的移動,美國西部的蠻荒景致讓觀眾應接不暇。這條連通紐約與舊金山的太平洋鐵路,橫貫美國東西海岸,全長4850千米,1869年建成通車,被稱為“19世紀世界最偉大的建筑”。
鐵路移動了美國的邊界。《殺人三部曲》中的插曲《薩特的磨坊》唱道:“有人倒在了印第安人箭下,有人魂斷落基山中……他們打開了西部大門,鐵路順著他們的足跡延伸……” 1903年,由愛迪生電影公司出品的《火車大劫案》在美國上映,影片根據1900年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搶劫事件改編,講述了強盜搶劫火車上的旅客的錢財最終被警察追擊而受到懲罰的故事。全片共有14組鏡頭, 片長只有十幾分鐘,卻把對火車施暴的全過程展示得驚心動魄。 美國鐵路穿越東西寬廣的大草原、大荒漠,像一頭猛獸,充當美國領土西進的先鋒,因這無界無拘的綿延,催生了難以掌控的事故,在熱衷于大場面的好萊塢電影人手下,火車成了排兵布陣的棋子,自由騰挪,也會產生無謂的自由傷害,可謂入戲之難。